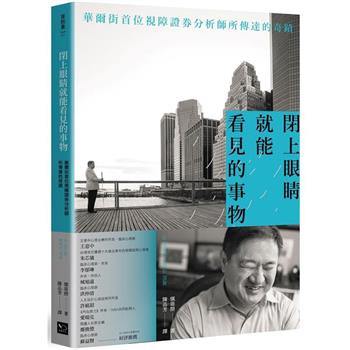不知不覺來到這裡……走進前所未有的奇蹟。
振奮人心的壯麗史詩,想像馳騁的神話之旅。
女性文學獎得主——《老虎的妻子》作者暌違八年長篇小說新作。
歐巴馬年度選書。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榜
童偉格 專文推薦
人生的快樂永遠是一場飢荒。
一無所有的孤獨靈魂,終將在此地相遇。
一八九三年,乾旱肆虐的美國西部亞利桑那領地。諾拉的丈夫出門去找水,至今未歸;兩個兒子與她大吵一架後突然失去蹤影;小兒子托比則堅稱在家附近看見了神秘的怪獸。面對家中窘境,諾拉束手無策,只能苦等丈夫回來。盧里是亡命之徒,也被鬼魂糾纏,跟著他要東西,意外邂逅的一場奇幻友誼,讓他從鬼魂的渴望中得到喘息,卻也激發他展開一場穿越西部的壯麗探險。諾拉與盧里的故事,將會以最懸疑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交會。
只有時間裡的事會改變,
你會相信的事,還有你不會相信的事。
改編自鮮為人知的史實,出現在荒野裡的駱駝,揭開一段美國西部沙漠的神秘過去。
十九世紀美國陸軍為了拓展廣大西南部荒地,展開一椿異想天開的軍事實驗——從中東地區引進「駱駝」,直到一九三四年最後一名駱駝兵死於動物園。書中出現的駱駝騎師哈吉阿里,他的紀念碑至今仍矗立在亞利桑那州。這是西部拓荒史中的一頁黑暗篇章,卻在作者筆下化作不可思議的奇幻冒險,在書中與讀者一同串起並見證迷路人、盜匪、騎警、鬼魂出沒的內陸地帶,不管是活著還是死了,來到這裡的每個人,都隨身帶著巨大而不變的欲望。作者繼處女作《老虎的妻子》後,再度交織鄉野奇譚和歷史傳說,打造一部具有魔幻寫實風格、令人難以置信的文學傑作。
「不凡的人被自己的煩惱侵蝕,而沒用的人則被自己的妄想拉著前進。」
人們永遠為了追尋「看不到」的某種東西而焦慮、逃避、前進。
一群在異域中見證異象的異鄉人,一部奇異又魔幻的文學傑作。
作者以意想不到的旅程,帶領讀者走出為焦慮所苦的心的內陸。
以一回回令人不敢相信的宿命的相遇,
將埋葬諸多死者的瘠地,翻泅為生者自領的幻鄉。
唯有相信,才能啟動命運。
上市即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娛樂週刊》A級書評
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娛樂週刊、圖書館雜誌、科克斯、書單雜誌年度選書
「歐布萊特的書寫,總帶有魔幻寫實的美學印記,因為魔幻敘事所抗逆的,原就是牢固的史實自身—— 然而,在主觀化的私「我」見歷中,一切皆還有可能改寫。這是說:當史實席捲了人盡皆知的死滅,造成了絕對終局,歐布萊特小說裡的私「我」,卻反身凝視絕境中,生機的一再複現,並收納為外公式的深信。彷彿「時間裡的事」,還在無限裡流變。……《夢土》的兩線敘事各自深涉與獨走,不負讀者期待地,將一片埋葬諸多死者的瘠地,翻泅為生者自領的幻鄉。」――童偉格,全文收錄書中
時代周刊 2019 年必讀書籍
Esquire 2019 年最佳圖書
衛報 2019 年最佳小說
柯克斯 2019 年最佳圖書
華盛頓郵報 2019 年著名小說
Good Housekeeping 2019 年最佳書籍
Real Simple Best Books of 2019
圖書館雜誌 2019 年最佳圖書
BookPage 2019 年最佳圖書
NYPL 2019 年最佳圖書
2019年歐巴馬總統夏季閱讀選書
作者簡介:
蒂亞•歐布萊特
1985年出生於前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勒,十二歲以後就一直住在美國。她的文章曾發表在《紐約客》、《大西洋月刊》、《哈潑雜誌》,及《衛報》,並曾被選入《美國最佳短篇小說》。她也被《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美國小說家最好的二十人之一,並且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老虎的妻子》為其第一部作品,她寫作此書時年僅26歲,但旋即以此書獲得英國柑橘獎,並入圍「美國國家書卷獎」文學類決選五強,及入選亞馬遜書店十大好書、和《紐約時報》十大好書。2019年,時隔8年推出長篇新作《夢土》,更被時代周刊評為2019年必讀書籍,並同時斬獲當年度各大報、書評媒體強力推薦。
譯者簡介:
鄭淑芬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肄業(修畢學分),主修國貿、英文、翻譯。具備教育部中英翻譯能力英譯中證書,目前專職翻譯。最新譯作《完美家庭》《我們的天空》《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餘詳csf1970.blogspot.com/。譯文賜教:ajanejane@gmail.com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歐布萊特的文字簡潔卻又極其豐富,充分展現了西部的美以及令人猝不及防的威脅。在這樣一部角色眾多的小說中,歐布萊特仍以充滿詩意的文字細細描繪出複雜的人物特色,令人驚嘆。
——Chanelle Benz,《紐約時報》書評
一場引人發噱又驚心動魄的冒險……這不僅僅是因為歐布萊特華麗的文字帶來的文學效果,更是因為它奇妙地呈現了在那樣荒蕪嚴酷的地理環境中,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生命。
——Ron Charles,《華盛頓郵報》
二〇一一年,歐布萊特以《老虎的妻子》嶄露頭角,轟動一時,八年後,她再度回歸,獻上一本寫實與魔幻兼具、足以讓馬奎斯會心一笑的小說……六頁長的最後一章非常精彩,讓人看得屏息凝神。
——《科克斯書評》星級評論
在當下書界崇尚自我反省、字字句句講求華麗的時刻,能夠看到歐布萊特寫出如此宏大而富有想像力的故事,不僅是一種解脫,也是一種榮幸。
——Sally Franson,《舊金山紀事報》
歐布萊特得天獨厚,光憑描述能力就能夠改變你對於一件事物的看法。
——Elizabeth McCracken,《歐普拉雜誌》
歐布萊特的文字展現了純粹的詩意。這已經不像是寫作,而是從心靈中提煉出的最純淨、最清晰也最真實的東西。
——David Canfield,《娛樂周刊》
歐布萊特以不可見的手帶著讀者前進,直到故事在最後完整串在一起,我們才恍然大悟。即使故事有缺口(也確實有),讀者也會自然地填補這些缺口。而那些一開始看似不重要的情節,像是兩家小報之間的宿怨,或是盧里順手牽羊的後果,也超越了書中的主要角色,最終融合到故事之中,融入時間的洪流裡,為讀者帶來意外的驚喜。
——Sophie Madeline Dess,《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這是西部,但不是我們熟知的那種西部。諾拉和盧里的路越走越近,兩人最後會相遇嗎?歐布萊特在這裡展現了傑出的敘事技巧,成功地重塑了一個被過度使用的文類及其比喻,成為《夢土》的魔力之一。這本西部小說中沒有刻板印象,只有犀利的文字在探索家的意義時也凸顯了現實的光怪陸離。
——Elizabeth Lowry,《衛報》
名人推薦:歐布萊特的文字簡潔卻又極其豐富,充分展現了西部的美以及令人猝不及防的威脅。在這樣一部角色眾多的小說中,歐布萊特仍以充滿詩意的文字細細描繪出複雜的人物特色,令人驚嘆。
——Chanelle Benz,《紐約時報》書評
一場引人發噱又驚心動魄的冒險……這不僅僅是因為歐布萊特華麗的文字帶來的文學效果,更是因為它奇妙地呈現了在那樣荒蕪嚴酷的地理環境中,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生命。
——Ron Charles,《華盛頓郵報》
二〇一一年,歐布萊特以《老虎的妻子》嶄露頭角,轟動一時,八年後,她再度回歸,獻上一本寫實與魔幻兼具...
章節試閱
密蘇里
昨夜那幾個男人策馬騎向淺灘時,我以為我們完蛋了。即使是你也一定很清楚,他們離我們有多近:他們的味道,馬轡的律動聲,馬匹的眼白。你一如往常——儘管看不見,大腿上還有取不出來的子彈——想站起來跟他們硬碰硬。也許我應該讓你去。這樣今天晚上的事說不定就不會發生,那個女孩子也不會受傷。但我怎麼會知道?我不相信我們的命運,因此也沒有準備,最後只能看著他們經過,在月光下騎著馬走上河床,遠離我們。我的等待——就算只是因為習慣——難道錯了嗎?我知道你還是很想逃。你還是很想逃;我也是,我一輩子都想逃——早在我們兩個結伴同行之前,在我六歲那年,在木板床上剛剛醒過來,我就已經在逃了。父親在身邊,波濤晃蕩,四週都是水打在船身上的嘶嘶聲。當時逃跑的是我的父親,不過我一直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逃。那時他似乎很瘦。或許也很年輕吧。他可能是名鐵匠,或者別種粗工,他從來沒有像待在船上搖來晃去的那個月休息得那麼多。那段時間日夜不分,只有我們頭上方某個地方的繩索和滑輪在黑暗中咯吱響。他叫我席恩,還有另一個我怎麼想都想不起來的名字。這段飄洋過海的過去,在我的記憶中大部分是連綿的浪沫和鹹味。當然,還有死人,包著白色的裹屍布,一個挨著一個放在船尾。
我們在港口附近找到住的地方。我們的房間可以俯視一條條曬衣繩,從一扇窗戶拉到另一扇窗戶,交錯重疊,最後消失在底下洗衣房的蒸氣中。我們父子共用一張床墊,背對著房間另一頭的瘋子,假裝他沒有一天比一天更瘋癲。走廊上永遠有人在尖叫。有人被困在不同的世界之間。我側躺著,抓著父親的外套領子,感覺蝨子在我的頭髮裡爬來爬去。
我沒有見過睡得像我父親那麼沉的人。我想,是因為碼頭的工作吧。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繃緊身子,扛著板條箱或一大捆繩子,看起來像一隻螞蟻。後來,他牽著我的手,讓下船的人潮帶著我們離開碼頭,順著大馬路來到鋼架正紛紛架起的地方。他對世界的運作方式充滿好奇心,因此覺得那種東西很神奇。他記憶力很好;有一直好不了的牙痛;還對土耳其人深惡痛絕,每次跟意氣相投的人喝茶時就說得義憤填膺。但要是某個塞爾維亞人或馬札爾人說起伊斯坦堡的鐵腕政權,情況就變得很搞笑:我那個對敵人非常執著的父親,會突然淚流滿面。他會這麼說:啊,先生。你過得更好了嗎?在這裡過得更好嗎?利斯凡别戈维奇‧阿里帕夏是名暴君,但絕不是最糟糕的!至少我們的土地很美。至少我們的家園屬於我們自己。然後他會感傷地懷念起小時候住的村子:一群凌亂散布的石屋,一條好綠好綠的河從中穿過,綠到他不知道該怎麼用新的語言來形容,只能用原來的話說,也因此將它永遠困住,成為我們兩個之間的秘密。我多想記得那個字啊。我想不通他為什麼要離開那麼美好的城鎮,來到這個臭氣沖天的海港,而那裡的人看到他手掌朝上禱告,名叫哈吉歐斯曼‧卓里奇,往往誤以為他是土耳其人,於是他拋棄那個習慣,也拋棄了那個名字。我相信有一陣子他自稱是哈吉曼‧卓里——但他是以「哈吉‧盧里」的名字下葬的,因為靈車來把他的屍體載走時,房東太太從他含混不清的名字裡選中了這幾個字。
我記得,我們的床墊都髒了。我站在樓梯上,看著馬車伕把父親裝進他的貨車。車子開走時,房東太太把手放在我的頭上,讓我留在那裡。傍晚的大雨停了,一輪落日染紅了街道。馬匹看似著了火。之後,我父親再也沒有來找過我。在水上沒有,連在夢裡也沒有。
夜復一夜,房東太太對著牆上的一具十字架禱告。她慈悲的給了我硬麵包,還有一張更硬的床墊。我給她的回報,是合掌禱告,並幫她照料旅社。我扛著肥皂水樓上樓下跑、抓老鼠、縮著身子擠進煙囪裡。有時候會有男人坐在陰暗處盯著我看,突然伸手抓我。雖然我長得皮包骨,但我不怕那些樓梯間的醉漢。我敢趁他們睡覺時踢他們幾下,所以他們學乖了,不會來惹我。又一個夏天,又一場瘟疫,馬車伕和他的黑馬又來了。一年又一年。旅社的路邊招牌上貼了一張字跡凌亂的紙。房東太太問我:你看得懂嗎?上面寫了「瘟疫房」——你知道什麼是「瘟疫房」嗎?結果瘟疫房的意思是空房間、空錢包,我們兩個人都空著肚子。下一次馬車伕再來時,她要我跟他走。她就只是站在那裡,盯著他放在她手裡的硬幣。
我在馬車伕的馬廄裡睡了一年。他是我見過最愛乾淨的男人。非得把房子弄乾淨、把拖鞋整整齊齊擺在床下才去睡。他身上唯一不整齊的地方,是一顆像象牙一樣突出的上排牙齒,讓他看起來像一隻大老鼠。我們流轉在布萊克街的窮巷陋室接收死者:那些一睡不醒,或是被室友割了喉嚨的房客。我們到的時候,有時他們還好好蓋著床單躺在床上。不過也經常出現擠在箱子裡,或被塞在地板下的房客。有錢、有親友的人,我們就送到殯葬業者那裡。無名無姓的,就載到上城的醫院,從後門送進去,好讓醫院在年輕人圍觀研究前把屍體擺好在解剖桌上。他們的內臟會被一一擺開,骨頭煮到泛白。
生意不好時,我們就得去墓地把他們拉出來。我們會給守門人兩塊錢,讓他們裝作沒看到,然後在十字架之間穿梭,尋找新翻的土塚。馬車伕會先猜頭部可能的位置,挖個地道,再讓我縮著肩膀手臂擠進去,鑽進冰冷的土地裡,拿著鐵條一直往前戳刺,直到把棺材板弄破。接著我就用手指去摸索,找到頭髮或牙齒,然後在頭上套個鬆鬆的活結。要兩人合力才能把屍體拉出來。
「這樣比用挖的輕鬆。」這是馬車伕的理由。
有時土堆會塌下來,有時屍體會卡住,我們得把挖到一半的屍體丟在那裡;有時是女人,也有小孩。而不管洗衣房的水有多燙,沾在我衣服上的墓地泥土怎麼洗也洗不掉。
有一次,我們發現兩個人共用一具棺木,臉對著臉,彷彿一起躺在棺木裡睡著了。有一次,我把手伸進去,只有泥土的觸感,以及潮濕的絨布枕頭。「有人比我們先來了,」我說,「是空的。」
有一次,我撞破木板,手指摸索過粗糙的毛髮和皮膚,剛把繩子繞過下頜骨,突然在黑暗中不知道從哪裡伸出來幾根手指,抓住我的手腕。是乾枯的手指,指尖很硬。我嚇了一跳,泥土飛濺,噴進我的喉嚨,被我吞了下去。我拚命踢,但手指緊抓著我不放,我以為我會就此消失在那個洞裡。我哭著說:「求求你,我不敢再去了。」然而,一隻斷掉的手腕加上一側扭曲的肩膀,證明我下次還是敢去。
有一次,有個大傢伙從棺材出來一半時卡住了。我坐在塵土裡,一隻蒼白的手臂壓在我的膝蓋上,後來馬車伕遞給我一把鋸子。我把那隻手臂用它原本的粗麻布衣袖包好,像扛火腿一樣扛在肩上,一路帶進城。幾天後的晚上,我看到一名獨臂巨人,紋風不動地站在魚市場的人群裡,那條破裂的衣袖就垂在他的身上。他臉色蒼白,身材圓潤,帶著笑容羞怯地看著我,彷彿我們是老朋友。他壓著那條空袖子,飄過來站在我旁邊。這樣說似乎很怪,不過我感覺到一種淡淡的麻癢環繞著我,我知道他用他的幽靈手臂攬住我的肩頭了。這是我第一次在自我的極限邊緣有這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慾望。他懊惱地嘆了一口氣,彷彿我們一直在交談。「天啊,」他說,「我快餓死了。我好想吃個美味的鱈魚派。小老闆,你不想吃嗎?」
我說:「去你的。」然後拔腿就跑。
我終於不再一直轉頭去找他——可是那種奇怪的感覺,那種在角落流連的渴望,一直沒消失。之後好幾天,我會在轟隆響的飢餓中醒來,躺在黑暗中,流著口水,耳邊有心跳聲。彷彿有什麼東西正在我的身體裡死命挖洞。普通的分量無法滿足它。吃飯時馬車伕數著我吃了幾口。他會說:「夠了,都被你吃窮了。」可是不夠——他罵我的那個量,只是一半而已。他沒看到我去討要從水果攤車上滾落的蘋果,也沒看到我趁雜貨店老闆轉身時偷小餐包。他沒看到的,還有賣糕餅的女孩子手臂上掛著一個大籃子走在街上,喊著,魚餅、魚餅。籃子大到她的身體都側一邊了。有人攔下她,她就掀開一張格子布,露出裡面堆得老高的糕餅。要吃魚餅嗎?她這樣問我,彷彿知道我體內的慾望已經快要作亂了。我蹲在巷子裡,吞了整整五個餡餅,洗衣婦人在我頭上方互相喊叫。吃的時候,那股慾望不斷增長,到最後碾壓而過,消失不見。
我再次感覺到那種慾望,已經是我們被抓到後多年的事了。我先在濟貧院待了一段時間。法官判決後,馬車伕被送往上游,我跟其他六、七個男孩子則被送到鐵路線的西邊終點。我手上的文件只寫著:盧里。
我們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經過農田和澄黃的原野,灰色的小山丘上有冒著煙的小屋,一路來到密蘇里,這個被淤泥吞沒的地方。一排牲畜圍場和房子就是城鎮。周圍的山丘上立著一根根短短的樹幹殘枝。載著粗大枝幹的拖車碾壓著道路。
他們帶我們到一個瀰漫著牲畜和木屑味道的市鎮廳,要我們站在一個板條箱搭的臺子上。其他男孩子一個個被叫下去,消失在黑暗中。為我舉手的那個老人名叫索瑞爾。他有一對髒兮兮的耳朵,走路一拐一拐的,還有一間專賣乾貨和威士忌的商舖。他的樓上房間永遠供不應求,大家都要往西部去。他另外雇用了一對兄弟:哈伯‧馬蒂和唐納文‧麥可‧馬蒂。哈伯只是個孩子,大概四、五歲吧,發脾氣時連大人都嚇得發抖。他還是名慣竊——他可以從任何人身上拿到任何東西,而且絲毫不覺得愧疚。索瑞爾不敢對他怎麼樣,因為他害怕唐納文。唐納文比哈伯大了十二歲左右吧,算是男人了,像狐狸一樣四肢修長,一頭紅髮。新長出來的一點鬍子,嫩得令他驕傲,哈伯和我卻毫不留情地取笑他。週日下午,他會溜出去,接受來自各地的拳擊手挑戰,把那些人揍得鼻青臉腫。不論他自己的臉被打得多慘,隔天上午他都會如常出現,帶著一臉僵硬的笑容煮咖啡。老頭因為我數錯錢而打我時,是唐納文省下肉不吃,幫我受傷的眼睛冰敷;打群架不長眼時,是唐納文幫我縫傷。唐納文說:「不管怎麼樣,盧里,都別讓人碰你。」
有兩年時間,我們同住一個閣樓房間。我們擦洗地板,玩法羅牌。我們拉貨物,煮茶把索瑞爾的水變成威士忌。我們笑鬧著經過灰暗的冬天,尋找在外頭上廁所而跌在雪地裡的房客。要是我們其中一人發燒,另外兩人就會跟著生病,然後又好起來,彷彿上下樓梯一樣尋常。一八五三年的夏天,唐納文跟我爬出了傷寒,可是哈伯沒有。索瑞爾老頭夠好心,替他買了棺木,所以我們不必自己做。
幾個月後,哈伯才回來。他來得無聲無息,一點跡象都沒有。看來死亡讓他失去了聲音,但並沒有讓他失去順手牽羊的衝動。我會從如幻似真的夢中翻身醒來,發現他的小手已經在我的肩上,而我的枕頭上有一些小東西:針、頂針、小型望遠鏡。他的慾望淹沒我時,就會讓我被類似的東西吸引。譬如我站在櫃檯,而某個路過的女人正在調整眼鏡,好把我們的商品看得更清楚,這時我的手指就會隱隱作痛。當時唐納文已經是職業拳擊手,隨時籠罩在源源不絕、失去理智的怒氣中。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說他的弟弟從天而降來到我的床腳。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我的床底下有一堆戒指、眼鏡、頂針及子彈。「我偷的。」唐納文發現那個箱子時,我騙他。「給哈伯的。」他打我,然後抱住我的頭,直到我的耳朵不再嗡鳴。我們把那個盒子拿到哈伯的墓地,挖了一個淺淺的洞,把偷來的東西統統倒進去。結果哈伯氣死了。有好長一段時間,他的慾望讓我夜不成眠,但我不是太介意。我希望,如果哈伯的死能讓我成為他的哥哥,或許唐納文也能成為我的哥哥。
我又換了一個盒子。但那股慾望似乎永遠不會消失。有時我會屈服,摸走一只錶或一本書,讓哈伯開心得不得了。後來,我懷疑他的慾望是不是也移植到唐納文身上,就像我這樣。會不會那就是我們兩個敢去搶劫的原因。一開始,我們只是窮極無聊使壞,做做樣子而已。午夜時分,我們在空地上喝威士忌,碰到有旅人路過,就攔下來。我們兩人只有一把六發左輪槍,不過我們的獵物並不知道。我會跟著唐納文從灌木叢裡出來,站在他後面,他則拿槍瞄準那些肥胖的滑頭和講話結結巴巴的醉漢,偶爾會有神職人員勸我們皈依上帝。很快,我們就在宿舍地板下藏了豐富的戰利品:錶、零錢包、可能對某人很重要的文件。哈伯輕鬆地坐在我的床緣,在這堆垃圾裡挑挑揀揀。用這種方式繼續在一起也不錯。
大約就是這個時候,唐納文打到一個拳擊手的眉頭,打得太猛了一點。那孩子站起來時,說話無力,眼神渙散。治安官來了,問了一些比賽公平性的問題,還有是不是唐納文收走他的手套?唐納文說他根本沒戴手套,結果治安官踢了一下他的肋骨,還問我們能給他什麼,讓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從我的戰利品中貢獻一只銀錶,可是幾天後,治安官又回來了,問:「為什麼我的新錶背面刻著『羅伯‧傑金斯』?他不就是上個星期在蘭丁路被搶的那個人嗎?」
這一次,唐納文打斷了他的下巴。
我們整個夏天都在逃,然後我們的畫像開始出現在懸賞傳單上。在布列敦、沃利斯、河口營區,我們瞄一眼那些寫著我們的名字的炭筆畫,笑他們畫得一點也不像。唐納文說:「就算迎面遇上他們也認不出來。」於是下一次我們攔了一輛驛馬車,他讓對方知道我們是馬蒂幫。他跟馬車伕說:「跟著我說一遍。」對方嘴裡含著槍管,說得含糊不清。
下一張海報將獎金增加一倍。
我們躲在某個洗衣婦家的穀倉閣樓,她半真半假地愛著唐納文,有別人在場時就叫我們先生,直到她的鄰居們都習慣我們的存在。這也讓我們受邀到好幾戶人家裡去吃飯。我們脫下帽子,一前一後,不知所措地穿過陌生人的廚房。和他們家穿著白色蕾絲、好奇微笑的女兒們圍著桌子,牽起手,含糊地感謝慈悲的上帝賜予我們豐盛的晚餐。不知怎麼的,沒有人把我們交給警方。大家都說:「誰會想到佩頓郡能這麼好運?藏了兩個勇敢的男孩子,樂於向聯邦政府證明阿肯色州的人對北方的法律有什麼看法。」
後來我們又加入了兩名生力軍,是馬蒂家的遠房親戚,艾佛瑞和馬瑟斯‧班奈特,來自田納西州,是兩個無趣、樂呵呵的傻瓜。他們只長肌肉不長腦子,不過唐納文覺得兩名馬蒂人成不了幫。有了四個人,就可以去打劫驛站。我們甚至可以去打劫馱隊——我們也真的去了,在黑暗中衝向數輛篷車,尖叫聲宛如蠟燭在我們周圍紛紛點燃。
有天晚上,我們在福丹搶了一輛驛馬車,躲過一名魯莽的紐約小子胡亂開的一槍。他的第二槍飛進了唐納文的肩膀。接下來我只知道我抓住那小子的頭髮,把他半個身體拉出馬車,其他人甚至沒有阻止我。兩個郡外的報紙說這是「粗暴行為」。一定很粗暴,只是我幾乎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後來我擦著鞋子,納悶我是什麼時候開始踢他的。
下一張海報寫著:
通緝
馬蒂幫
請聯絡佩頓郡約翰‧伯格法警
唐納文說:「這下可好了。」這話不無驕傲的味道。「現在你惹到法警來追我們了,值得慶祝。」
(待續)
密蘇里
昨夜那幾個男人策馬騎向淺灘時,我以為我們完蛋了。即使是你也一定很清楚,他們離我們有多近:他們的味道,馬轡的律動聲,馬匹的眼白。你一如往常——儘管看不見,大腿上還有取不出來的子彈——想站起來跟他們硬碰硬。也許我應該讓你去。這樣今天晚上的事說不定就不會發生,那個女孩子也不會受傷。但我怎麼會知道?我不相信我們的命運,因此也沒有準備,最後只能看著他們經過,在月光下騎著馬走上河床,遠離我們。我的等待——就算只是因為習慣——難道錯了嗎?我知道你還是很想逃。你還是很想逃;我也是,我一輩子都想逃——早...
目錄
密蘇里
上午阿馬戈
聖安東尼奧
中午阿馬戈
科羅拉多
下午阿馬戈
希拉走廊
晚上阿馬戈
鹽
上午阿馬戈
謝詞
推薦文 自己的時刻――童偉格
人物簡介
密蘇里
上午阿馬戈
聖安東尼奧
中午阿馬戈
科羅拉多
下午阿馬戈
希拉走廊
晚上阿馬戈
鹽
上午阿馬戈
謝詞
推薦文 自己的時刻――童偉格
人物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