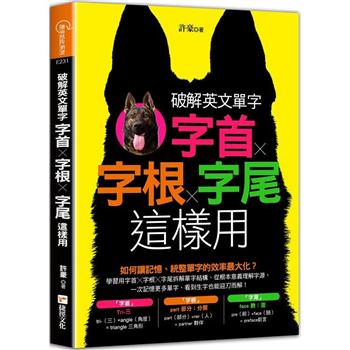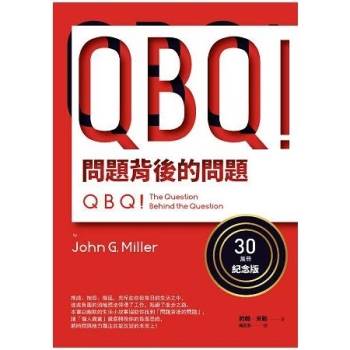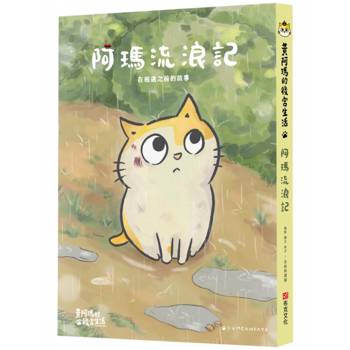偶爾請天光雲影週末喝一杯,喝全部的夜,以壯形色。
偶爾請悲傷站好,為它整衣,以便漂漂亮亮地適應人生。
李進文首次跨域──詩與繪畫共舞。
釋放藝術的體例,打開意象的邊界,放寬詩,擴充美學。
他著眼於時代,時時保有真誠的玩心……
奔蜂──取自《莊子》,即小土蜂。
小小的土蜂也有自己的「志氣」和「志記」──人小心大又何妨?困難做到的夢,才是值得尊敬的夢,試著改變現狀,不循熟知的路線,即便迷路亦無悔。
「自由體」的語字迅疾如小蜂,不停滯、不固著,亦不守規矩地飛舞,而其精短刺人,恰似蜂針!
李進文透過詩與畫的並陳、結合,或者即時互動,開闊詩意,想像力超展開。
語字與圖像,或拮抗或敦睦,甚至共舞──他帶領意象團隊,切換視角,觀照他者,剪輯人生,鼓動戲劇張力,穿行於留白與空隙……。因為美的構成和達成,必須是一種意料之外、邏輯之中的動態平衡。
他將不同的形式、觀念、感情融為一個複雜的綜合體,一個詩的小宇宙。
同時,透過寫詩與繪畫的儀式,尋找自己:
天色是我的莫札特,
彈光陰,一路變奏。
一路變奏,種種創作,
皆是尋找自己的儀式。
種種自己,每一種,
可能比顏彩更多,
可能比輕煙更瘦。
《奔蜂志》全書概分三卷,共181首詩。卷一〔有意圖〕,共選51幅彩畫與詩結合,其下三個小系列:「謀畫詩」、「流露樣」和「動靜色」,圖文交響,跨域創作,以壯詩觀。卷二〔搗語聲〕,暗喻「島嶼聲」、「禱語聲」或「搗雨聲」,涉事亦涉世,調動視角,睹微知著,幽默自適。卷三〔瞇日子〕,直面人生的憂疑,回應中年的叩問,綠化字語的荒漠,且自尋常市聲開墾另類異音。
本書特色:
․李進文現代詩「自由體」三部曲之最終篇章,亦最具挑戰。首度跨界,以畫作詩、以詩詮畫,兩相撞擊、提升、詰辯和再生。生活就是他的史詩,以多元技藝,寫出島嶼的詩。
․意匠的心!跟著美術設計回到紙書時光,感受視覺、觸感和氣味裡的溫度。自在而有機的排版,無固定模式,具動感,像詩;以裝幀創意回應內容,如對話。書衣的小蜂,用牠微小的力量牽動湖面的漣漪、掀起書本的折角,讓我們閱讀,一同朝往奔蜂的志向。書內頁三卷依詩畫內涵,採用王子雪嵩、日本書籍及彩虹色紙三種紙材印刷,以「有形」將讀者帶入「無形」的優雅、沉浸式的讀詩狀態。32開本,易於攜帶,隨性展讀,四處想像。
․榮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創作補助。
作者簡介: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臺灣高雄人,曾任遠足文化、臺灣商務印書館、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媒體記者等。著有《野想到》、《微意思》、《更悲觀更要》、《靜到突然》、《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等多部詩集和散文集,跨域著作有美術詩集《詩與藝的邂逅》、動畫童詩繪本《字然課》等。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文化部數位金鼎獎等。
章節試閱
卷一 有意圖
【謀畫詩】
●
形狀
很多東西
沒綁好,例如:
雨絲沒綁好天意,
月光沒綁好深井,
細脖子沒綁好樹,
鞋帶沒綁好一條死路,因此
人間發生各種事故。
很多東西的形狀不固定,
會變形、隱形,
會消磨、鏽蝕、幻滅,所以
難綁,
永恆沒辦法綁他們,
(永恆這種東西又太固定
成不了氣候。)
你怎麼會因為你不成形狀
而憂傷呢?
一粒沙
和一個世界,
據說死後形狀一模一樣,
一樣難綁,因為
終究虛無。
你怎麼會以為你必須活成別人
眼中的形狀才能抵抗歲月?
你怎麼會用你的形狀
解釋你的存在?
你怎麼會相信有色的眼睛?
今天夕陽的形狀
是野獸。
昨天野獸的形狀
是你的哀愁。
明天或未來一切的形狀
擠過頻寬
回到光。
●
片刻之夏
你是穗狀的,穗狀的柔荑;而你的香氣、你的眉梢降半旗,敬悼撕心裂肺的日曆。時鐘咬走一天一月又一年,老天未打疫苗第一劑,自知到了危險的年紀。久未受理人類案件,抱歉你的祈禱只能婉拒。牽掛遠距,你是無限花序。
你是繖形的,繖形的雨滴;而你的瞬息、你的詩句吹毀籓籬,你一念之間居家可以天涯,你一念之間從臥室跨到海角,你一念之間廚具幻作熱鬧街衢。牽掛遠距,你是六月躁鬱。
午後陣雨,猛敲腦門,時光如稀客蒞至……。你靜靜地反身落鎖,心之方寸,口罩圍城之地。
●
夏夜之豬
風是非法的:偷渡
入窗,涼涼地動搖我幾兩肉、
幾斤心情。
我探出窗,
以物價一般攀升的頸子
眺望天意──
多汁的夏夜,
豌豆星系活躍,緻密,
靈性老老地吹來,
窗簾一下又一下地掀開房間,
啊我聞到松露
就埋在蟲洞旁星爆區
(宇宙也像人一樣碰撞,
相互吞噬?)
而眼前
寂靜在樹枝搖曳,
而眼前
雜食的月亮
乾淨得像剛洗完澡的豬。
●
當我討論夢……
夢不喜歡我。我抓緊它,它會痛;我放開它,它心累不想動。
我不喜歡夢。它有春天的線條,用來綁架我;它用色彩吹出泡泡,要我看破。
如果,夢還留在意識固著之前、靈魂形成之初──最小位元的那個夢……如果它沒有成為我的一部分,那麼它只要做好自己就會發光,甚至絢爛。
再回想一下:夢還沒弄髒、還沒膨脹、還沒成為我的一部分之前的那個夢;之前的那個夢還沒像家貓一樣被餵食、還沒奢望不平凡、還沒以塵土捏造我……
我不喜歡夢,夢不喜歡我。──認清這點,夢才有機會自我實現,我才能不再自我欺騙;讓捏造我的塵土歸塵土,夢歸夢。
●
魅
我心入夜,蟲鳴懣懣。
想用靈魂與植物結親,想給礦物起一個雌性又好聽的拉丁學名,想戳破輕薄如紙的月光,想把星象釘在胸懷,想你或許又不怎麼想。
脈搏一鎚又一鎚,敲打入味,敲打深邃,敲打敲打,我心震震,電激雷奔。
藍與黑,空有鐵肺,滿天下盡皆低調,唯你飆高一聲雪亮的游絲。
此刻,爵士樂如你,你沉醉我;
我醉後獨自修復你的魅、孤身捉摸你的野焰。
霍然你靜音,卻充滿怒放。
我心不能阻攔你的曲線輕盪,果香,金黃。
●
狐狸詩
窗邊,一隻狐狸
捧讀海涅詩集。
晚風吹送,
秋香色窗簾好像九條尾巴晃動。
一隻狐狸沉醉的形狀
像火,也像劍。
孟德爾頌的旋律,歌的翅膀
撫拍牠……牠望向夜空:
月亮是銀狐,
北斗七星是黑狐。
捧讀海涅詩集的
一隻狐狸,
依據的文法
是戀人的臉頰(狡猾的淚,
摸索長夜。)
牠向屋外走去,「立在
月光下,
宛如一根柱子。」這是海涅的句子。
一隻狐狸的感情
只是很老還未成精。
卷一 有意圖
【謀畫詩】
●
形狀
很多東西
沒綁好,例如:
雨絲沒綁好天意,
月光沒綁好深井,
細脖子沒綁好樹,
鞋帶沒綁好一條死路,因此
人間發生各種事故。
很多東西的形狀不固定,
會變形、隱形,
會消磨、鏽蝕、幻滅,所以
難綁,
永恆沒辦法綁他們,
(永恆這種東西又太固定
成不了氣候。)
你怎麼會因為你不成形狀
而憂傷呢?
一粒沙
和一個世界,
據說死後形狀一模一樣,
一樣難綁,因為
終究虛無。
你怎麼會以為你必須活成別人
眼中的形狀才能抵抗歲月?
你怎麼會用你的形狀
解釋你的存在...
作者序
玩心──自序
1.星體
十三世紀波斯詩人魯米(Rumi 1207-1273)說:「任何你每天持之以恆在做的事情,都可以為你打開一扇通向精神深處,通向自由的門。」
近十年,我的新詩創作另一主軸是希望完成「自由體」三部曲。最初構想,有點類似惠特曼《草葉集》內容包羅萬象,詩百科似的,釋放體例,模糊邊界,不馴於詩歌規則,如同麒麟──「其為形也不類」,卻自成生態系統,從臺灣土地的生活向外折射,交響我的人間。這三部,包括已出版第一部《微意思》(寶瓶文化2015)及第二部《野想到》(木馬文化2020),第三部就是《奔蜂志》了,即便像一隻小土蜂(奔蜂)才能有限,盡了力,就是我對詩的虔誠心意。
自由體,「體」不是指體裁和文體,體是宇宙的星體。想像四十六億年前,太陽系和地球由無數「微粒子」凝聚而產生,其後,地球又經由無數的「微行星」撞擊、聚合,終至成型。無數的微行星撞擊──是促使地球誕生的源起,這三部作品中的每一則都是「微行星」,它們相互碰撞,有的聚合,有的再生,有的殞落,生命於焉肇始,這是三部曲創作的初心,原型的發生。
第一部《微意思》偏重形式與內涵的自由,即興彈奏,類散文詩,題材繽紛,語字輕盈,意象華麗,亦含組曲式的極光(或吉光片羽),強調詩的「有意思」比「有意義」更有趣。第二部《野想到》進一步加入「故事詩」,重心擺在「有故事」的觀點、諷喻與微言深意。第三部《奔蜂志》,我嘗試「跨域」,一部分結合我的繪畫,讓自由體開放對話,開闊象徵,擴充詩,更欲使語字與圖像或拮抗或敦睦,甚至共舞,將不同的形式、觀念、感情融為一個複雜的綜合體,說不定會再激盪出另一個小宇宙;日本國寶級「狂言師」野村萬齋強調藝術必須:「著眼於時代而時時保有玩心……。」狂言講求實力與技藝至上,因此詩人白萩也說,「藝術之所以能偉大的呈現在我們眼裡,正是由於技巧的偉大。」然而──當我們到了有些年紀,若想繼續探索美好的事物,保有「玩心」最是要緊,它會令生命保持靈動。
我探索著種種可能:──該如何顛覆語言的規則?該如何讓詩具有魅力和個性並解除固定方法?該如何從容地走在險峻的深淵邊界?該如何安頓陌生與穎奇而不著斧痕?該如何布局大意象和小細節?該如何雜糅日常另闢新異?該如何反思進化?我邊寫邊提問,這三部曲是種種懷疑的過程,不是終點。
2.美術詩
關於繪畫,自知青澀,我畫畫是為了詩。以我的「詩想」繪出我一個人的意味或意思,沒遠大計畫,不急於追求屬於自己的符徵。《奔蜂志》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詩集加入自己的畫作,希望視覺與詩互涉,又可單獨存在,對詩跨域,一部分因著玩心、一部分為了放寬詩。
詩與畫,有共通的藝術美學,本該相互砥礪。1950年代趙無極和具有神祕主義的詩人亨利.米修一起出版過詩畫合集。現代詩與繪畫始終緊密關聯,以詩詮畫或以畫作詩,兩相撞擊、提升、詰辯和再生。加西亞.羅卡《從橄欖樹,我離開:羅卡的十二首詩‧畫》由墨西哥超現實畫家賈布里耶.帕切科所繪;拉封登《寓言詩》則成為法國插圖藝術家多雷(Gustave Doré)的幻想舞台。
1970年代,臺灣重要的現代詩社如《創世紀》、《現代詩》和《藍星》,與「五月畫會」、「東方畫會」和「現代版畫會」交流密切。它們在詩與畫的技藝美學,有齊心追索的理念。
直到1980年代,尤其在1987年解嚴後,以結社交誼的方式較少了,但詩人與畫家仍然有合作,例如劉國松版畫與余光中的新詩結合,李錫奇的《浮生十帖》與創世紀詩人們的詩句相互詮釋,楚戈的油彩畫展《是偶然也是必然》則與他自己、管管、商禽、鄭愁予的詩作對話。
臺灣許多詩人的詩集,也採用畫家的畫作,例如洛夫名作《石室之死亡》封面為莊喆所繪,周夢蝶《還魂草》封面是席德進油畫作品〈周夢蝶畫像〉,侘寂安謐,頗似黃土水的雕塑《釋迦出山》。《創世紀》詩刊的封面更結合過丁雄泉、朱沉冬、洪根深等畫家作品,《藍星》詩刊封面亦使用楊英風、劉國松、朱德群等畫作。
如今繪畫與詩,分別走向更多元、更自我個性的方向。我試著回到詩畫同源的概念,兩者互為養分,分則獨立、合則互動,亦即採取若即若離的方式,以免陷入「圖說」,讓詩與畫皆保有自己的小宇宙。這概念,源自於十年前我曾與高雄美術館有一次大型展覽合作。
那時高美館計畫推出嶄新型態,回顧臺灣美術與現代詩壇之間的跨界淵源,由我以高美館30件典藏作品為素材進行一系列的新詩創作,與民眾分享美術與文學跨界的結合。這促使我認真思考詩(文學)與繪畫的關係。我將那次合作的詩,稱作「美術詩」。
詩與美術結合的「美術詩」不單單以詩去詮釋美術作品、也不是附庸或服務於美術品,我的概念是詩與美術平行,同位階對話,展覽時呈現一種「即時互動」的關係。欣賞一件美術品就是再造一首詩,欣賞一首詩也會再生另一幅畫,沒有一件美術品是不隱含詩質的。
雖然2021年三月之後我才開始有規律地動手畫畫,即便僅是起步,但裡頭有我對詩的敬意、對美術的詩意。我對自己說,「至少我嘗試了!」 而「嘗試(一試再試)」,不就是詩的基本「實驗精神」?
繪畫和詩一樣,有時漫無目標,在漫無目標的過程中,累積失敗的經驗夠多,就會有不錯的作品出現。總是這樣,畫家追尋生命中的節奏與符號,詩人開發獨有的音色和語言生態。但最重要的是,透過繪畫或寫詩的「儀式」,不斷地練習再練習,最終──為了找到自己。
3.奔蜂
《奔蜂志》中的詩與視覺,我以篇幅最大的第一卷來實現,共選51幅彩畫與詩結合。這個「第一次」的嘗試勇氣,或許日後能讓我敢於繼續探索新詩、精進繪畫吧?另外兩卷則糅合更多真實和想像,在「自由體」之中。希望讓三部曲抵達《奔蜂志》有一個活潑又多元的小句點。我常想,詩不能自以為有意義或創意,而是要與他人、與社會、與土地聯結,至少與自己的「心意」相聯結,方成意義或創意。
「奔蜂志」,取自《莊子.庚桑楚》:「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奔蜂,小蜂也。意即細腰小土蜂的才能有限或不足(如我)不能孵化大青蟲,而體型小的越雞也不能伏在天鵝卵上使其孵化,但我想像,奔蜂和越雞一定也有自己的「志氣」和「志記」吧!人小心大又何妨?困難做到的夢,才是値得尊敬的夢,試著改變現狀,不循熟知的路線,即便迷路亦無悔。自由體的語字迅疾如小蜂,不停滯、不固著,亦不守規矩地飛舞,而其精短刺人,恰似蜂針!
《奔蜂志》全書概分三卷,共 181 首詩。卷一〔有意圖〕,其下三個小系列:「謀畫詩」、「流露樣」和「動靜色」,圖文交響,跨域創作,以壯詩觀。卷二〔搗語聲〕,暗喻「島嶼聲」、「禱語聲」或「搗雨聲」,涉事亦涉世,調動視角,睹微知著,幽默自適。卷三〔瞇日子〕,直面人生的憂疑, 回應中年的叩問,綠化字語的荒漠,且自尋常市聲開墾另類異音。
新詩自由體三部曲,從《微意思》、《野想到》抵達《奔蜂志》,時間拉得很長,我如同島嶼上的奔蜂,體小、微不足道,但對詩亦有鴻鵠之志(許是巨大的敬畏)。生活是我一個人的史詩,我用三部曲去體現平凡平淡中的多元詩藝,寫出島嶼的詩,是為志!
特別感謝聯合報副刊和作家宇文正這些年以不定期的小專欄刊載,讓我有了規律的動機去書寫和繪畫。並感謝國家文藝基金會對《奔蜂志》的創作補助。
玩心──自序
1.星體
十三世紀波斯詩人魯米(Rumi 1207-1273)說:「任何你每天持之以恆在做的事情,都可以為你打開一扇通向精神深處,通向自由的門。」
近十年,我的新詩創作另一主軸是希望完成「自由體」三部曲。最初構想,有點類似惠特曼《草葉集》內容包羅萬象,詩百科似的,釋放體例,模糊邊界,不馴於詩歌規則,如同麒麟──「其為形也不類」,卻自成生態系統,從臺灣土地的生活向外折射,交響我的人間。這三部,包括已出版第一部《微意思》(寶瓶文化2015)及第二部《野想到》(木馬文化2020),第三部就是《奔蜂志》了,即便...
目錄
自序──玩心
卷一,有意圖
〔謀畫詩〕
形狀/片刻之夏/夏夜之豬/當我討論夢……/魅/狐狸詩/那隻貓有一個夢/刺蝟和蒲公英/我是食夢貘/豪豬/海豹/樹懶的方法/夜,請進/窗前──雪松太平鳥/一隻鳥鎖定心間/孵月亮
〔流露樣〕
風箏/叢林時光/秋天/遠方/窗與天涯/歧路/車過天涯/現象與觀念/弄孤獨/虎部彌撒曲/鳥或者臉譜/分內的事/輕煙的年/居所/鐵皮屋/和風念念/我走進園子裡/漾
〔動靜色〕
為了詩/稀微/世界的眼睛/盛夏/斟酌一些詞/龜山島/彩霞收工/小雨中的回憶/花心/悲傷就是綻放/正向/容器自述/靜物/沉思/給點顏色/靜靜的/瓶花與貓
卷二,搗語聲
疫病時期/懷人/練功/病者思慮如刃/傳達/謐謐厭秋聲/墓誌銘/說幽靈/我們/往事盎然/橄欖/夜跑/一個作家/恐懼/綺色書/小睡/網路時代巧遇孔子/夜打掃/心動/死了的故事/雨日/到了某個時刻/不要有什麼/早前傍海/相隔離/濁光品/某個夏天水果攤/人物/確認了這些就繼續生活/老樣子,給自己/夢/浮世/鎖國以後/一天/詩樣子/撐/合掌村/兼六園/茶屋街/金澤城/妙立寺/芭蕉山中座/山中溫泉/鶴仙溪/栢野大杉/無限庵/偏/情意/端午/簡訊/重訓/四月維夏/歎詞/選讀一座山/拉拉山/競選照片/銅像/被戒嚴的人/政黨/反抗/對話/致隱地/空洞/在路上/還原/臺南/青春期和全美戲院/老虎日/經過幾天陽光/民生社區/床/艾莉絲.孟若/徒勞頌
卷三,瞇日子
火光每小時不斷更新/寫詩的方法/改善/自拍照/夜的路邊/山水/詩與麵包/微塵──讀楊牧/六月/大暑/王船醮/長成好看的宜蘭/慢悠悠/狗臉的歲月/觀點/一抹說法/金秋/想/喜/星球紀事/形色/涉世景深/越山越輕/穿/意象/一個人/聖誕節可疑/鐵鏽圓舞曲/童話藍/起色/述說/你跟你心內的黑狗/漂亮的句子/編輯/後腦杓/婚/靠醉平衡/掛念/宵待草/圍爐/雪女紀/美學考/若沖畫卷/一與零/晨賴你/垂絲語/一言無以蔽之/念之深/心之境/去找龍貓/浮世繪/下午/天色變奏/異想之路/塗鴉筆記/且行且走光/野渡
自序──玩心
卷一,有意圖
〔謀畫詩〕
形狀/片刻之夏/夏夜之豬/當我討論夢……/魅/狐狸詩/那隻貓有一個夢/刺蝟和蒲公英/我是食夢貘/豪豬/海豹/樹懶的方法/夜,請進/窗前──雪松太平鳥/一隻鳥鎖定心間/孵月亮
〔流露樣〕
風箏/叢林時光/秋天/遠方/窗與天涯/歧路/車過天涯/現象與觀念/弄孤獨/虎部彌撒曲/鳥或者臉譜/分內的事/輕煙的年/居所/鐵皮屋/和風念念/我走進園子裡/漾
〔動靜色〕
為了詩/稀微/世界的眼睛/盛夏/斟酌一些詞/龜山島/彩霞收工/小雨中的回憶/花心/悲傷就是綻放/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