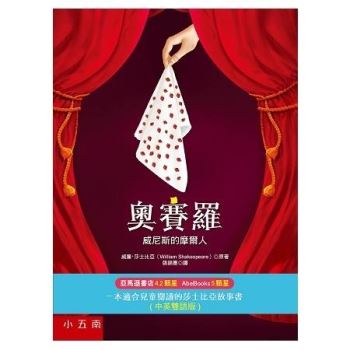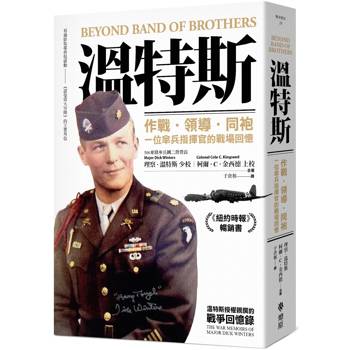曾經裝入眼簾,就會裝在心窩;曾經裝入行囊,就會裝在記憶深處。
我們就如野鳥、野花草一樣,一輩子都在尋找一個夢土!
在心靈中,在現實中,一個安適得宜的家,夢想之地。
【中國時報第二屆散文佳作獎】
【中國時報第五屆散文佳作獎】
【中國時報第第七屆新詩首獎】
【中國時報第十二屆散文甄選獎】
【第六屆吳魯芹散文獎】
【第十五屆吳三連散文獎】
──陳煌自然寫作新篇.45幅手繪生態插圖──
【藉由生態寫作、花草蟲鳥速寫,探尋自然、人我關係,一本尋仙記。】
蕭蕭.李瑞騰 誠摯推薦
在野鳥的世界裡,我已進入牠們的領域,但我依然無法進入牠們啼鳴的內心世界,和意義,但不論如何,牠們早已透過不同啼鳴而傳遍整個野地了。無論如何,牠們的啼鳴讓野地活了起來。野地活了,人與這世界也不致太孤單……
許多野生植物肆無忌憚的遍佈山丘,尤其像姑婆芋這樣看似觀賞,卻野性十足的外來植物,寬大的葉片足以捧接最多的陽光,和雨水,讓野蛙或蝸牛當運動場,有需要時還可以當雨傘使用。白鷺鷥飛遠了,我在想,山不來,我就過去,仙不見,我就去看祂。然後,或許預計在一個欲晚的雨天,撐這一把傘,石階而上,看看能不能尋到仙人。
在文字篇章之間,遨遊著、舒坦著,作者陳煌的仙人與神仙之地已駐在其中。
在陳煌的插圖與文字間,或多或少會感覺出那是人與山野之間變化無盡、無盡延伸、延伸到無始無終的無盡藏……那時空、那場景、那氣息、那蟲、那草、那鳴叫聲、那荒涼感,似乎也能聞到陳煌一個人獨自穿行在風中雨裡所摩擦出來的疏野味道。──蕭蕭(詩人)
從「延續」到「跳脫」,陳煌等於是為他新一階段的散文寫作定調,動植皆文……用《尋仙》承轉他的自然書寫,繼續為他筆下的微小動植物尋找新樂園,也為他自己「尋一個安適得宜的家」。──李瑞騰(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這本書我寫了一些微小動植物等等的微生態,自覺地去感受他們的私生活,用我自己的語言,感覺有點脫離了過去我寫生態的較沉重與嚴肅的筆調,而以較自在,適意,自然的方式關注審視他們……我想輕鬆地寫他們,還有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如此而已。──陳煌
作者簡介:
陳煌
1954年生於台灣南部鳳山,後畢業於世界新專廣播電視科,立下志願遊歷各類型雜誌媒體,出任過書訊報刊類主編,男裝時尚類雜誌、青少年類雜誌、兒童類雜誌、健康類雜誌、汽車生活類雜誌、成人類雜誌等總編輯,以及擔任中國時報系工商時報副刊撰述委員、主編。也曾受邀在中國大陸遊歷雜誌界十五年,出任女裝時尚類雜誌,創意設計類雜誌等創意總編輯,汽車生活類報刊視覺顧問,亦為北京《型男志》雜誌撰寫男裝專欄。
遊歷兩岸媒體界近四十幾年間,也同時創作散文與詩,其中散文作品多著力與自然野地生態與山鳥自然生態有關作品,出版包括《人鳥之間》(簡體字版由大陸天津百花出版集團出版)、《有蟬鄰居》……以及2022年時報文化出版的《雜念》等二十餘本散文集。
曾獲中國時報第二屆第五屆散文佳作獎,第十二屆散文甄選獎及吳魯芹散文獎,第七屆新詩首獎,第十五屆吳三連散文獎。
《尋仙》一書是2023年最新散文創作作品。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人與山野之間那一條無始無終的地平線/蕭蕭
就陳煌而言,「仙」的造字,是人與山野之間那一條變化無盡、無盡延伸、延伸到無始無終的無盡藏,永遠到不了卻也永遠引逗著的那一條地平線。
他,尋仙而來,而去。
現如今,陳煌回來了,三十年前那個原野觀察者、山野漫遊者、荒野紀錄者,散文家陳煌回來了!藉著一本三十年前自己手繪的生態細密畫,藉著那一條虛擬的地平線卻又是自己實足親踏的野地書寫,回來了!
書名《尋仙》,多麼明確、堅定,且又節制的兩個字的意志!
相對的,他的副標則是「追憶微生態私生活的自然念想」,浪漫而現實地描繪出整部散文集的質地與內涵,就是那麼「微生態」、「私生活」的「自然念想」的「追憶」,就是三十年了仍然清晰、生鮮的自然影像,自動播放,自在旁白。
《尋仙》的插圖與文字,相隔三十年,但在當今天文及地質學界的理論和觀測皆一致認為的四十五~四十六億年之間的地球年齡而言,這三十年卻只是小數點後面的微渺數字。相對的,遠離野地不到五十年的自以為「文明」的我們,當然無法察覺其間的歷史差距,當然也不確然相信那是當今人類應該嚮往或尋找的仙境!
但在陳煌的插圖與文字間,或多或少會感覺出那是人與山野之間變化無盡、無盡延伸、延伸到無始無終的無盡藏……
或多或少、或淺或淡,會察覺出陳煌曾經追尋的那時空、那場景、那氣息、那蟲、那草、那鳴叫聲、那荒涼感,似乎也能聞到陳煌一個人獨自穿行在風中雨裡所摩擦出來的疏野味道。
不曾離失,其實也未曾擁有;不曾熟稔,其實也未曾全盤俯臨與辨識。
彷彿遙遠的天邊淡月。
就像是眼前這一場四十多幅的插圖遭遇。
逐日逐日的蹲伏、觀測,模擬、繪製,逐日逐日的物華與我對視、對峙,而後揉合成我與圖繪,而後融合成天與人的兩相忘,忽忽三十年,圖繪醒來,文字醒來,我醒來你醒來,天邊的淡月也醒來。
曾經裝入眼簾,就會裝在心窩;曾經裝入行囊,就會裝在記憶深處。
只待天外的鐘聲響起。
那四十五~四十六億歲的古老地球一直醒著吧!
那十數年在荒野中晃盪的歲月、所塑寫的文字形符,一直醒著吧!
那記憶的蕨類,和泥盆紀一樣久遠,一樣醒著吧!
我喜歡陳煌這樣說:
「我們都想由流浪中創造出一個不需再流浪的家園,比如桃花源。
而這荒野就是桃花源,野生動植物的桃花源,也是風的四季的桃花源。」
陳煌黏著他的荒野,我們黏著他的荒野圖記,其實也黏著他三十年的桃花源夢想,黏著他六十年的生命沉思,黏著人類終極而未可終及的呼喚。
隨著陳煌尋仙吧!人與山野,若即若離,那一條變化無盡、無盡延伸、延伸到無終無始的仙境……
2023.4.16. 清明已過.穀雨將臨
推薦序
陳煌尋仙/李瑞騰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我開始從事編輯工作,也勤快寫作,發表一些文學評論,也陸續參與文壇活動,認識了許多年齡相若的寫作人,時相往來的不少。很快便結識了陳煌。他來自高雄,世新廣電畢業,寫詩和散文,做編輯工作,曾任《愛書人》雜誌編輯,參與《陽光小集》的創辦,記憶所及,他在《幼獅》相關刊物及各報副刊發表過很多作品。
陳煌最初的散文,和當時年輕的我輩一樣,叩問生命、呼喚青春,有著淺淺的哲理、淡淡的哀愁,出之以美美的文字,後來都收在他出版的前幾本散文集中(如《夜夜在小鎮》、《長卷》、《陽關千唱》)。但我輩青年寫作者,經歷一九七○年代後期幾年的時潮震盪(鄉土文學論戰、和美國斷交、美麗島事件),普遍意識到寫作之於我群,包括土地、歷史和人民,密切關聯,可以說是一種大覺醒吧,一九八○年以後,他們走出自我小空間,從政的、搞運動的(社運、文運、原運、客運等)、作媒體的、寫作的,甚至大專院校教書從事研究的,不同層面、不同工作形態,都可以發現有一種指向舊體制、舊社會、舊思維的新脈動。
對於自然界,陳煌原本就有所關愛,從南方北漂,在都會裡工作與生活,當自然生態保育的風潮一起,「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呼聲此起彼落,他開始寫鴿、寫蟬、寫人鳥之間、寫他對於大地的沉思、寫大自然的憂鬱、寫大自然的那些歌手、寫野地等等,陳煌作為一位自然生態作家的專業形象於焉形成。
陳煌是媒體工作者,八、九○年代,在臺北,他遊走於幾個不同類型的雜誌社之間,為稻糧謀,也通過刊物和受眾對話。這樣的工作在編輯室進行,但要能掌握時潮社脈,而且心思要非常細密;而他自己的寫作,場域是野地、山林,用學術話語來說,必須田調,觀察、紀錄、錄音、攝影,有時還要素描,他必須利用週休去做寫作的準備,真正一字一句書寫,當然只有夜間了。而如果只是一篇兩篇、一本兩本,那也還好,陳煌在上個世紀的後二十年間寫了十幾本生態散文集,獲得時報文學獎、吳魯芹獎、吳三連獎的高度肯定,肯定的不只是他的作品,也包含書寫的行為本身。究竟要有多深的自然之愛,才能如此持久奮力寫作?
陳煌談到他極重要的《人鳥之間》時說:「(此書)包括了我一年四季的完整定點觀察散文紀錄,它關於野鳥、關於昆蟲草木、關於人、關於大自然一切變化的記載,以週記方式記錄了野鳥新樂園的地誌。」「它傳達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以及一種土地愛、人文生態觀。」他痛心地說:「當它呈現在讀者您的眼前時,已不再存在。因為,它和所有已消失了的荒野自然一樣,正被人們快速無情地糟蹋。」文明反成為一種野蠻的暴力,糟蹋原始素樸的荒野,我們都知道,但無可奈何。
二○○一年夏天,陳煌去了大陸,和雜誌有關的工作,除了《新銳》創刊主編,還做過《iidea創意設計月刊》創刊主編,《汽車生活報》創意總監。在大陸待了十五年,二○一七年回到台灣。他去大陸發展,我知道;回來,我也聽說,但除了偶見他的詩文發表於報刊,還沒有機會見面。最近他來信說有新書要出版,要我這個老朋友幫他看看,寫點閱讀心得。我很高興又聯繫上,雖然已欠缺年輕時那種把酒言歡的熱情,但藉著閱讀老友的創作文本,將一大段空白歲月的情誼,牽來牽去牽起,也可以彌補一些因環境變遷和彼此際遇差異而產生的遺憾。
拜網際網路四通八達之賜,我點閱了每一筆和陳煌有關的資料,發現他在去年曾出版一本以「雲淡風清」為筆名出版的《雜念:與凡間觸動共舞的小碎步》,我注意到陳煌在〈序〉說的,這「一則則簡短有意思的雜念」,「約有一百多則,是當初從已寫完的前十分之一處約二萬字中挑選的,若有主題,那應該是:「觸動」,它們是「在四、五年前」「開始寫的」。意思是說,大約在返臺前後以降的四、五年間,他寫了約二十萬字的手記。手記體散文曾於一九七○年代風行,沈臨彬《泰瑪手記》(一九七二)、羊子喬《太陽手記》(一九七四)、渡也《歷山手記》(一九七七)等我迄今記憶猶新,陳煌以「雜念」命名,拈出「觸動」主題,實為手記。
這說明陳煌在生活中恢復了寫作,記下來的雜念以後還可以當原始素材再創作。但真的能夠雲淡風輕嗎?陳煌新書有一個副題「追憶微生態私生活的自然念想」,這句密度超高,拆開來看,首先是「追憶」,其次是「生態」、「生活」,再來是「念想」,後三者上加「微」、「私、「自然」。其實讀一下如自序之〈尋仙而來〉,首篇〈尋仙〉以及最後的〈後記〉,此書寫作之因緣及內容之主題傾向等,就可以理解了。一本薄薄的三十年前畫的生態插圖重新出土,牽引多少前塵往事,陳煌本就善感,觸動他的是當年的生態觀察和自然寫作,我也感動,只因他「為它們新寫一本書」,即這本包含約四十篇「念想」的《尋仙》。
書中所有的篇名都兩個字,都對應著一張插圖。陳煌說,許多篇章「不免多少延續著對野鳥新樂園的迷戀,以及一些些念想,不過,我試著跳脫出過去完全的生態寫作方式,加入了更多我的追憶與心念元素。」從「延續」到「跳脫」,陳煌等於是為他新一階段的散文寫作定調,動植皆文,寫作者因時因地在物我之間調整比重:「我」多一點,「物」相對少了一點;下筆重一些,話題嚴肅,讀來心也沉重,放輕鬆一些,就比較自在、適意了,讀來壓迫感沒那麼重,卻也能感受作者的憂懷。
陳煌去了大陸十餘年,基本上和臺灣文壇斷了聯繫,但這段期間有二本碩士論文探討他的寫作,一本明示研究他的「自然寫作」(李明展,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二○○九),一本專論他的「鳥類書寫」(孔淑如,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二○一○);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聯經,二○一一)有一章〈一九八○年代台灣邊緣聲音的崛起〉,其中一節論〈散文創作與自然書寫的藝術〉,雖未專論陳煌,但談完環保成為臺灣文學一個永恆主題,特舉劉克襄,談完劉克襄,他說:「同時期重要自然書寫的實踐者,還包括探險的徐仁修(一九四六~)、觀鳥的陳煌(一九五四~)、觀鷹的沈振中(一九五四~),都豐富了這階段自然散文的精神與內容。」上世紀末,陳煌的文學價值及歷史地位已經非常明確,中斷了十幾年,他當然不會忘情於荒地,用《尋仙》承轉他的自然書寫,繼續為他筆下的微小動植物尋找新樂園,也為他自己「尋一個安適得宜的家」。
此外,他一字一句寫下的大量的雜念中,是否也包含他十五年的大陸經驗?從馬英九到蔡英文,海峽變得濤驚浪駭,我想起日治下張我軍到北京,留下一本詩集《亂都之戀》(一九二五);戰爭時期吳濁流去南京一年,多年後編成一本遊記《南京雜感》(一九七七),而身為一位當代臺灣作家,陳煌大概很難不追憶在大陸的羈旅歲月,寫吧!那也曾是一塊荒地。
序
尋仙而來/陳煌
找到自己這些三十年前的手繪插圖後,就在想,為它們新寫一本書。
《尋仙》,就是。
仙人在哪,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喜歡什麼。
三十年前,我寫《人鳥之間》這本書時,原來的書名是,野鳥新樂園。
說實話,《人鳥之間》一書是我最鍾愛的,而三十年後的《尋仙》一書可視為《人鳥之間》的餘續,我一樣獨愛。
雖說,那野鳥新樂園這野地就是野鳥們的家,桃花源,烏托邦,夢想之地。
而這本書中提及的野地,或荒野等等地方,雖不盡然是指那野鳥新樂園,況且,經過這三十年後,恐怕所有的野地都已有改變,變得更糟糕不堪……但我多年來也在尋訪自己的家,一個如桃花源的家,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一個能好好思考寫作之處,那也許是類似野鳥新樂園的地方,野地,或荒野等等地方,而我,或是我們或許如野鳥,野花草一樣,都需要一個夢土。
這本書的許多章節,不免多少延續著對野鳥新樂園的迷戀,以及一些些念想,不過,我試著跳脫出過去完全的生態寫作方式,加入了更多我的追憶與心念元素。更明確地說,這本書我寫了一些微小動植物等等的微生態,自覺地去感受他們的私生活,用我自己的語言,感覺有點脫離了過去我寫生態的較沉重與嚴肅的筆調,而以較自在,適意,自然的方式關注審視他們;不,也許不該也是沉重或尖銳般的關注審視,而是說說我感受到的他們與我的原本私下生活,我與他們的關係。
我想輕鬆地寫他們,還有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如此而已。
因為如此,如此想來,這樣的記事可以讓自己一路寫下來,也感覺很開心。
而且,每篇保持較適中的字數,以利閱讀。
其中只有「追蹤」一篇文字較長,因為它寫得最早,早到我後來找到以為失散的手繪插圖之前,早到我後來想寫《尋仙》之前,而且它保留紀錄了我在野地的一回冒險情節,很有意思,故留存了下來。
當然,要尋的仙,何嘗不是我夢想中的家,桃花源,烏托邦,夢土,希望,或者是你自己朝思夕想的地方?
因為在我們心靈中,現實中,或許都需要尋仙,尋一個安適得宜的家,不論是否尋得到,心中總要供奉一個仙人,一處神仙之地,讓我們去追尋,這也很不錯的。
至於我,尋仙得如何了?
我的仙人與神仙之地已駐在這書中,在文字篇章之間,遨遊著,舒坦著。
名人推薦:推薦序
人與山野之間那一條無始無終的地平線/蕭蕭
就陳煌而言,「仙」的造字,是人與山野之間那一條變化無盡、無盡延伸、延伸到無始無終的無盡藏,永遠到不了卻也永遠引逗著的那一條地平線。
他,尋仙而來,而去。
現如今,陳煌回來了,三十年前那個原野觀察者、山野漫遊者、荒野紀錄者,散文家陳煌回來了!藉著一本三十年前自己手繪的生態細密畫,藉著那一條虛擬的地平線卻又是自己實足親踏的野地書寫,回來了!
書名《尋仙》,多麼明確、堅定,且又節制的兩個字的意志!
相對的,他的副標則...
章節試閱
尋仙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這山並不高,但一座小小宮廟就座落在群丘陵中的最高處,有長長石階直通山巔宮廟前,鮮少人跡,卻也有幾分幽靜的仙氣。
不過,把宮廟蓋在山頭的地方,顯然想多一點仙氣吧。
凡是遠離人群俗世之地,即便是在市囂的郊外,只要有了山,再有了林,沒有雲霧,而周圍卻環繞著各種野鳥環繞,也會給人隱藏仙氣的感覺吧。
再說,廟也不在大,有一定的香火就好。
香火裊裊,就接通了天庭,也能讓神仙感受到人間的所願吧。
我遠遠地望著,仰望它的屋頂,希望能看到香火如雲霧般上升,環繞,想像有仙人對膜拜他的人能有所指點迷津。不過,那上面的陽光普照,香火的煙霧大概早已飄散。有一群白鷺鷥成隊靜靜飛過,牠們攤平雙翼,潔白清瘦的身子如仙人的白袍,在迎風中,把飛影緩緩投下宮廟的屋頂,然後緩緩穿過天空,牠們在趕赴另一場香火之約嗎?
我喜歡白鷺鷥,即便牠們的叫聲一點也不討好,也不如仙班中的仙鶴,可是牠們曬優雅,安靜,潔峻,儒秀,亦有幾分仙韵,也有一種仙風道骨之感。在草地上或水邊,白鷺鷥的神態依舊儒雅,不疾不徐,即便在空中飛行,也一樣悠閒自得,一派文人墨客的清舒風流。
山上的宮廟是否有先人與仙鶴坐騎,我不知道。
但我聽說,有白鷺鷥在宮廟附近的樹林中築巢群居,牠們被人間視為吉祥鳥,牠們繁延生息之處被視為福地,所以當牠們盤旋於山巒之間,投身於宮廟天空時,人們也會認定這宮廟也許或有多少仙氣吧。
那長長的石階,向上,通向天空。
想接近宮廟,接近神仙,就得一步步修練一樣往上走。
我遠眺,石階旁似乎多矮灌木,如荊棘,咬著石階。
而且,許多野生植物肆無忌憚的遍佈山丘,尤其像姑婆芋這樣看似觀賞,卻野性十足的外來植物,寬大的葉片足以捧接最多的陽光,和雨水,讓野蛙或蝸牛當運動場,有需要時還可以當雨傘使用。
白鷺鷥飛遠了,我在想,山不來,我就過去,仙不見,我就去看祂。
然後,或許預計在一個欲晚的雨天,撐這一把傘,石階而上,看看能不能尋到仙人。
黏人
不論是哪個季節,不論是否颳風下雨,我都會以探險的心走入荒野。
那時,我以一整年的所有假日時間,一個人在荒野中獨行,走走停停,停停看看。
若是我可以停下腳步,那就隨地蹲下來,各種野草在腳邊肆意擴展領地,也被我的雙腳不經意的蹂躪,它們從不言語,也沒異議,更不反抗,像一個個憨厚的農村人。野鳥是我當時觀察紀錄的主角,野草不是。
它們生活自己的,從生死到擴展領地,從不在乎他人的眼光,與褒貶,好像這世界有了它們也不多,沒了它們也不少。不過,世界有了它們卻美麗多了,只有人們無所謂。
我知道的那塊荒野,它們一樣如此活著,生死由天一樣過日子,用自己的方式延續生命後代,靜靜的,默默地在有風的日子裡將種子散播出去,沒有風,就是黏人。
我是其中稀罕到荒野的人,一年四季中見不到幾人會出現。誰也不願,不會,不肯,不知到這荒野,更不喜被黏人。
其中,有些植物很黏人,不黏人時,只有黏偶爾經過的野狗或白鼻心或落地的野鳥身上,若是沒這些機會,有風也沒用,飛不遠,落下,也會被其他野草植物埋沒。這樣,它們還是靜靜的,默默的,不言語,沒異議,不反抗,一副生死由命的樂天。
它們知道,有的是機會。
等待,就是最好的機會。
我一直很願意蹲下來,屈膝看看它們等待的模樣,它們其實都隨時準備好了,準備好出發了,所以成熟地長成黏人那樣子,引頸翹盼。
在它們前面,在風的前面,甚至在褲管走過所經歷的前面,就是它們的世界,與未來。
我的褲角也只是無心,或無意間幫了它們一把而已。
它們就很黏人地黏在褲腳,不放,直到我有點疲憊,煩悶的硬是取下,丟在荒野地上,如它們所願,時間一到,活下來繼續黏人。
我跟它們一樣,在荒野中,我只能等待,其他什麼事都不能做,我等的是野鳥行蹤,風的行蹤,四季的行蹤,因為它們都在變化,我只能像一個旁觀者似的一旁觀察記錄,而不介入。
如果介入了,在野草叢生的那一瞬間,我的褲腳就會成為黏人植物機會主義的成就對象,我願意走遠一點,讓它們更有擴張領地的機會。如此的介入,並非絕對刻意,和干擾。它們,黏人野草植物,或許它們天生就喜歡黏人,刻意黏人,樂於黏人。
誰又不黏呢?
我黏的是荒野。
相遇
一九九○年之前,我寫了《人鳥之間》,所以我寫生畫了這張長尾水青蛾的時候,也是在那時,所謂的野鳥新樂園的荒野。
因為距離的歲月遙遠,我都不記得在何時何地和位置,甚至何種氣候與植物之下發現牠的。
但我畫下牠了。
在我的薄薄一本畫頁中,牠,長尾水青蛾出現了。
我當時很快地畫下牠,從此我再也沒遇上牠。
我總覺得,相遇只能遇見有意義的人或物,相遇才有意義。
我在荒野時,能遇見的山鳥無數,不過諸如常見的麻雀,白頭翁……等等的山鳥,我只憑牠們名叫即能辨認出牠們的名字,但是有些難得一見的山鳥如竹雞,五色鳥……等等,卻經常在無意中,或等待中相遇時,始感覺一種驚喜,覺得我終於因相遇而得以一見,認識,謀面,這樣的初初相遇的意義,在於先建立起的之後盡可能進一步的相知。在人鳥之間,牠們無須「相知」於我,也無須認識謀面於我,但對我來說,我卻是需要,必要的。
這種意義,對觀察特別重要。
只是對這隻難得一見意義下的長尾水青蛾來說,我的追憶中,除了初次的相遇外,我就無緣再與牠相遇了。
其實,應該說,牠一直都在,牠的族群一直都在。
只是我無緣再相遇罷了。
假使,我要更認識牠,我可以從電腦中獲得許多資料,但如果我想獲得更具意義的話,就會捨棄電腦,自己會在自己的不棄觀察紀錄中,讓相遇成為有意義的重要緣分,與資料。
我只依稀記得,牠忽然間的近距離出現,牠就靜靜停留在一片葉子上,好像牠原本就在那裡,不曾離開過一樣。
牠沒動,我卻心跳不已。
我在觀察記錄山鳥時,也會在意當時的天候,蟲子,林木,花草等等的四季變化,長尾水青蛾對我卻是極其陌生的。
我的相機無法對牠對焦,牠就距離我的鼻子前幾公分,我也無法後退,因為我退無可退,我身後好像是一個灌木叢生的斜坡。
在我努力穩定身子之後,我只能取出畫頁和筆。
牠靜靜讓我畫完,我已滿身大汗。
天色開始閉上眼睛,我應該離開了。
荒野,就是這樣,只有我們的相遇,才有意義。
觸角
有人如此解釋觸角,昆蟲頭部的是觸角,比如:蝸牛,甲蟲,蝴蝶等。觸鬚只在哺乳類動物裡才有,比如:海豹,海獅,狗,貓等只有觸鬚。
所以,觸角是指節肢動物頭上分節的附肢,它具有觸覺和嗅覺功能,是由柄節、梗節和鞭節組成。一般來說,甲殼動物有大小兩對觸角,蜈蚣、馬陸和昆蟲只有一對觸角,不過有昆蟲具多種觸角,如蛾類的羽毛狀觸角、蝶類的球桿狀觸角、蠅類的剛毛狀觸角、白蟻的念珠狀觸角、蜜蜂的膝狀觸角等等。
我覺得,它們很有意思,在互相近距離接觸的時候,往往先以觸角接觸,觸感在這時,似乎就能敏銳地判別對方是同類,或異類,然後做出反應。如果我在野地,以草莖去有意撥弄任何一隻昆蟲的觸角,它們會善意或沒異樣的緩緩以嗅覺來做判斷,然後緩緩爬上草莖,因為草莖在昆蟲絕大部分的環境中都會遇上,熟悉的味道讓牠們不疑有他。
據我的觀察,即便換成手指,只要不帶有異味,牠們通常都能接受,在手指上活動。有一回,我遇上一只虎頭蜂,牠單獨出現,但我還是用視線努力搜索了一下四周的環境。
四周是一個斜坡,斜坡的雜樹林茂密如蓋,我幾乎無法透過橫七豎八的各種枝葉,看清樹蓬,或蜂窩,或見到任何可疑之處。我也聽不到沉悶的空氣中,有蜂群扇動的任何聲響。一切都很安靜,安全。
唯有一絲絲的風,帶著各種植物所散發出來的味道,在熱烈陽光中蒸發。
那是一個夏季,我剛進入野地的範圍不久,也剛以冒險的心緒闖入一條野徑,那野徑通向一片雜樹林,那如同一個我未知的寶藏,至少值得一闖,探看。
但很快的,那只虎頭蜂就出現在我眼前,牠發亮的黃色身軀如馬路十字路口上閃動黃色交通標誌,一下子就警告我別輕易亂動。
牠趴在一塊突起石頭上,兩支粗短卻看似強而有力的觸角,對著我,但我只見到牠半個身子,因為牠的下半身就藏在石頭後面。
縱使如此,我也能看清牠異於一般蜜蜂的身材了,以及牠黃色甲殼外表上,還仿若劃上黑色條紋的蒙面,那像極了格鬥場上,戴著表現出試圖先威嚇震攝對手的老虎條紋面具,是令人產生畏懼的。
而那一對觸角,似乎如偵測器一樣對著我,我的一舉一動,關乎牠是否出擊。
觸角,好像在慢慢,輕輕地轉動,在悶悶不樂的空氣中轉動,我沒動,牠沒動。
我沒應對過虎頭蜂,但牠為何單獨出現在石頭上?是因為石頭上的表面還留有水漬,牠是來飲水的?還是,牠是孤獨的,獨行的?
我沒動,但感覺風在空氣中緩慢流動著,附近的草葉微微晃動著,我的心也是。
難道是我無意中侵入了牠的地盤,或是牠行經的路線了?
我面臨的野地還有多少野蜂呢,我不知道。
夏日下,樹林再密,也無法完全阻擋所有的炙陽,所以被過濾後的碎陽依舊亮閃閃的落下,落在地面,落在我身上,落在牠身上。
未久,牠都沒有任何行動,我也逐漸放下心來。
我開始轉而仔細觀察牠,這是一回在野地能好好窺視虎頭蜂的機會,也是我夢寐以求的。
我在心裡與腦海裡描繪牠,牢牢記住,並且覺得,牠好像也沒攻擊我的意圖,因此我雖然不動而汗流浹背,卻感謝牠給我難得的機會。
風,並未大作,但日照在林子外似乎慢慢黯淡了。
我感覺到,林子也開始躁動起來,歸鳥紛紛回家了。
不知為何,野風很快轉強,吹得樹葉簌簌作響,我忽然想起,也該下山返家了。
風,就這樣吹拂我的衣襟,和背包,以及碎陽,我開始覺得不對勁,牠未免不動太久了。在這不長不短的約十分鐘裡,牠不動,唯獨觸角在動。
是風的緣故,我定神去看,往前兩步,那是一只虎頭蜂的不動屍體,風乾的屍體,但外觀依舊與舉止紋風不動,牠看似很久一段時間就枯趴在那裡了。
觸角的風動,讓牠栩栩如生。
林子因牠,也有了一絲威風。
流浪
不是有魚的地方,才有貓。
我不養貓,原因無數,其中之一就是食物。
我不想為貓的食物而費心,所以不養貓。
我在野地,見到的都是流浪貓,牠們也似乎都活得很好,因為野地有的是吃的,貓雖然挑食,但野地的流浪貓卻不致挑食,而且身材苗條適中,因為活動量更大,對獵捕更用心,這就對許多小動物小昆蟲產生威脅,其中鳥巢更是牠們的美食餐桌。
野地流浪貓我見過不少,但牠們通常不想見到我,一遠遠看到人影,就往樹林草叢裡鑽,不見蹤影。對這種害羞又怕生的流浪貓,我一點辦法也沒有,野地是牠們流浪之所,也幾乎沒有天敵,如果流浪是牠們的宿命,那麼牠們會選擇野地,也不願選擇舊巷子。
其中一隻野地的流浪貓,見到我時,會先停下身子而轉頭看我一眼,如果我繼續行動,牠就會一閃而逝。若是我停下身子,牠就裝出若無其事地沿著小徑路邊走,低頭,像有點心事一樣,其實牠的其中一隻腳壞了,走路有點跛。牠身上有淡淡黃色花紋,不明顯,頭部有較顯目的黑條紋,四肢修長,我猜牠在野地生活很久了。
流浪,對牠來說,應該是每天的事,稀鬆平常的事,在大自然的無拘無束野地中流浪,看雲,聽風,坐雨,喵月,甚至小盹,仰天長睡,應該是流浪的一部份,至於四季歲月,那根本是身外瑣事,不值得一顧。我不知道牠每天幾點起床,早餐吃什麼,但我知道在野地入口的老舊警衛室後面那片山坡地,是牠的最愛。
牠經常在那裡現身,或半躺在半遮掩的植物堆後面,這樣牠隨時可以仰起上半身瞧瞧動靜,也是這樣,牠經常發現我有時用望遠鏡遠遠對著牠。牠對野地和那片山坡地四周太熟了,那可能是牠經常獵捕食物的地方,更何況偶爾牠能聞到那警衛室老管理員丟棄在附近的便當剩飯剩菜,有時換點口味,也有點意思。
有時,我好幾天才見過牠一次。
有時,我會苦澀地猜想,牠會不會出事了。
不過,牠往往在我莫名想念牠時,出現,牠還是一樣跛著腳,但健康。
野地,沒有動保團體,牠也沒人會關注,牠只是孤獨在流浪,今天在這山坡地,明天進那樹林,我不知道牠下不下山。
我不知道牠的命運會如何,但知道牠應該會安樂於流浪,安樂於死亡吧。
野地是牠的家,一整片都是,可是誰也不在乎牠。
後來,我離開那野地後就再也沒見過牠,但繼續流浪就是牠的生命。
流浪,若是心甘情願的,那牠就是豐盛的,甘之若貽。
尋仙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這山並不高,但一座小小宮廟就座落在群丘陵中的最高處,有長長石階直通山巔宮廟前,鮮少人跡,卻也有幾分幽靜的仙氣。
不過,把宮廟蓋在山頭的地方,顯然想多一點仙氣吧。
凡是遠離人群俗世之地,即便是在市囂的郊外,只要有了山,再有了林,沒有雲霧,而周圍卻環繞著各種野鳥環繞,也會給人隱藏仙氣的感覺吧。
再說,廟也不在大,有一定的香火就好。
香火裊裊,就接通了天庭,也能讓神仙感受到人間的所願吧。
我遠遠地望著,仰望它的屋頂,希望能看到香火如雲霧般上...
目錄
推薦序
人與山野之間那一條無始無終的地平線/蕭蕭(詩人)
陳煌尋仙/李瑞騰(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序
尋仙而來/陳煌
尋仙
捕手
野生
不明
晃蕩
古老
黏人
有家
山路
相遇
遺忘
長蟲
爬樹
結果
愛蝶
透明
過溪
乘風
懷念
油菜
答案
死去
會飛
活著
水岸
燈塔
仰望
事件
觸角
屬水
看望
流浪
啼鳴
叫蟲
發現
守候
偽裝
音符
深處
大椿
追蹤
後記
推薦序
人與山野之間那一條無始無終的地平線/蕭蕭(詩人)
陳煌尋仙/李瑞騰(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序
尋仙而來/陳煌
尋仙
捕手
野生
不明
晃蕩
古老
黏人
有家
山路
相遇
遺忘
長蟲
爬樹
結果
愛蝶
透明
過溪
乘風
懷念
油菜
答案
死去
會飛
活著
水岸
燈塔
仰望
事件
觸角
屬水
看望
流浪
啼鳴
叫蟲
發現
守候
偽裝
音符
深處
大椿
追蹤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