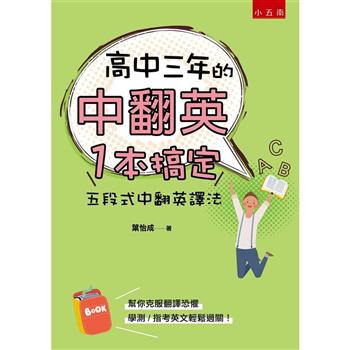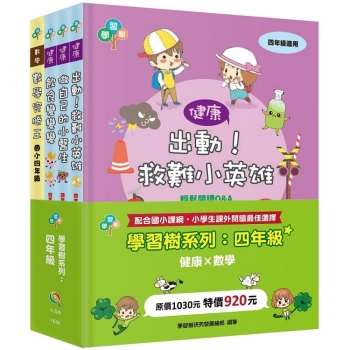她懷中這條龍,即使被人背叛了,渾身是傷,也依舊相信人,相信她……
「真正醜陋的,從來不是你──是傷你至此的那顆人心。」
比美《蒼蘭訣》的逗趣虐心,九鷺非香超高好評仙俠大作《護心》,強勢出版!
──必有一戰,只為一人。──
‧瀟灑修仙女《山河令》周也╳美強慘妖龍《人不彪悍枉少年》侯明昊,打造全新仙俠劇標竿,討論度超高熱議出圈!
‧原著作者人氣作家《蒼蘭訣》九鷺非香擔綱編劇,品質保證!
‧討論度超高,最具CP感的螢幕情侶首選!
‧今年最受期待的古裝奇幻仙俠,人妖之別,正邪之戰,強勢來襲!
被逐出師門、跟蛇妖打到修為全無的修仙叛逆弟子雁回x被愛人背叛後附身在凡人身上,欲尋回前世身體的真龍天曜!
人與妖的組合,一起找回身體!
人生難料,誰能知雁回修了十年的仙,現在卻被命運推著坐在了妖族的誓師大會現場?而今她也修了妖道,更成了正道口中的墮落妖孽。
人跟妖天然對立,是善與惡。妖生而有錯,禍亂天下;人光風霽月,護持正義,斬妖誅邪是人的責任──但妖只是出生為妖便該死嗎?人對妖不管多殘忍都能被原諒嗎?
這次,雁回要擋在全妖族的前頭,與從前的師門對抗;諷刺的是,那些說著雁回墮落該死的同門,才真的為了一己之私,害了許多無辜的生命!
她懷中這條龍,即使被人背叛了、渾身是傷,也依舊相信人,相信她……如果二十年前,天曜遇見的就是她,那她一定不會辜負這條最是溫柔的龍;天曜相信,他也一定不會被雁回傷害。
多虧這世上有雁回,才讓他體會到什麼叫驚慌失措,什麼叫失而復得,什麼叫……怦然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