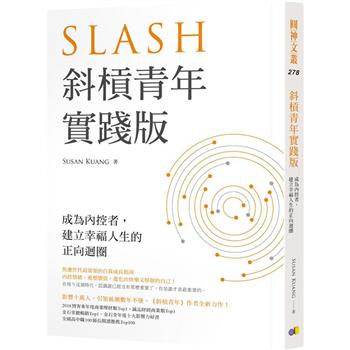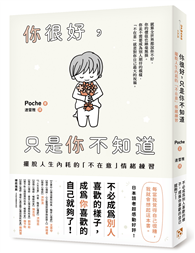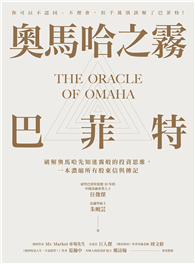「妳早就知道了我的身分,也早就打定了主意利用我?」
所以,從一開始,就全是假的嗎?
★《簪中錄》後,就是《司南》!
// 皇太孫裝成太監,身中奇毒只剩一年可活,卻把自己賭輸給神祕女子當家奴!//
‧古風探案解謎新高峰!
‧豆瓣評分高達8.6分!
‧最適合影視化的高概念作品!
他經脈受損之時,也是災變產生之刻,這一切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古代推理言情第一把交椅,《簪中錄》作者側側輕寒最新力作!
//
狂風驟雨之中,她離去的背影,
是他此生遭遇過的,
最刻骨銘心的背叛。
//
原來司南,早已察覺他就是皇太孫。那些出生入死時的默契與相護,都是誆他的戲嗎?
她犯下的每一條都是十惡不赦殺頭重罪,他絕不能成為跟餘孽糾纏的皇太孫,禍及東宮……
刁奴朱聿恆,簡直欠教訓!她是為了救公子不擇手段,但她救了全城百姓也是事實,居然把知府跟宮中才人之死都栽贓給她,呵,不是她幹的別想她認!
還好皇太孫殿下不笨,猜到了小鬍子董浪就是易容過的司南,只是嘴硬地說是網開一面,還是放她來查案……
不過越查,她越心驚。她被公子所救,養成手段通天、縱橫四海的司南;她相信公子的人品,願意為他付出生命去完成理想,但看百萬居民陷入死陣,公子為了自己的大局而無視,朱聿恆卻忍下劇痛、捨生忘死地保護百姓,她迷惑了。
她要洗清冤屈,幫助公子、保下兄弟;她也要救朱聿恆,讓他逃脫迫在眉睫的死亡,但他們,註定是會對立的兩方……
作者簡介:
側側輕寒,又名側側,知名網路作家。現居杭州。自幼好讀書,尤其喜愛歷史書,愛甜食、愛宋朝,胸無大志,自由散漫。喜歡古詩詞,不求甚解;研究過星相,可至今只認得太陽與月亮。時空廣袤,人生無限,獨自在自己的路上且行且緩。愛寫小說,曾做過編輯,作品散見於《武俠》、《奇幻》、《言情》、《公主志》等期刊。
代表作品:《司南》系列、 《簪中錄》 、《北落師門》 、《撿到一條龍》、《桃花亂》、《仲夏薔薇》、《流光之年》、《千面天使》、《奉旨逃婚》等。
章節試閱
阿南隨口「喔」了一聲,轉頭去看朱聿恒,卻發現他望著上方窗戶,又看向對面樓閣,神色略有古怪。
「怎麼了?」她問。
朱聿恒搖搖頭,將心中一些不應升起的念頭強壓下去,示意眾太監宮女都退下,然後才道:「妳是朝廷海捕罪犯,只需盡心戴罪立功即可,其餘事情,不必多想。」
「沒良心!你怎麼只記得我做過的錯事,不記得我當初救了你、救了順天、也幫了杭州的事兒啊?」阿南白了他一眼:「我當初豁命救你也沒見你感激我,現在回來幫你也不見你感念我,我怎麼這麼賤呢?」
說罷,她鬱悶地轉身,大步走向了那間偏殿。
朱聿恒默然,只覺胸口血脈微微波動,類似於抽搐的微痛順著山河社稷圖貫穿他的身體。
她確實豁命救過他。
在順天的地下,他身上的經脈被機關牽動而發作之時,為了讓他清醒過來,她解開了他的衣服,幫他吸出了瘀血——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這世上,與他最親密的女子。
心口的悸動似要衝破這些時日鬱積在胸口的憤恨,將他整個人淹沒,讓他再也維持不住疾言厲色的表象。
他唯有竭力深深呼吸,壓下心口的悸動,以免自己心口厚厚修築的堤防被她攻破。
悶聲不響的兩人,一前一後踏入了那間偏殿之中。
行宮畢竟少人來,又只是片刻歇息的偏殿,因此裡面陳設十分簡單。牆上掛著大幅祥紋織錦,靠牆放著一榻一椅。
床榻對面便是四扇長窗,窗下是供整妝的桌臺,設了一面鏡子、一個妝盒,裡面是空的。畢竟太子妃殿下隨身女官必然帶著妝奩,行宮提供的肯定不合用。
阿南在室內轉了一圈,明明可以問朱聿恒的,卻偏要去問太監:「太子妃殿下在此休息,有誰進出過這裡?」
「當時殿內一片混亂,殿下身邊的女官都在正殿幫扶各家閨秀。再說此間狹窄,因此奴婢與侍女們都守在門外,不敢驚擾休息的太子妃殿下。」
「一個人啊……」阿南自言自語著,走到窗前,將桌上的鏡子拿起來照了照。
鏡子磨得很亮,她對鏡摸了摸自己那兩撇小鬍子,又看了看正對面的右閣。
朱聿恒悶聲不響,目光從鏡子轉向瀑布。
而阿南已將鏡子放下了,指向九曲橋,說:「我去對面看看。」
走出深殿,外面熱浪撲來。他們在熱辣日頭下走過玉帶拱橋,來到右邊殿宇。
「好熱啊,這大熱天的在外面簡直受罪。」阿南出了一身汗,一邊用手扇風一邊抱怨著,就去桌上尋找茶具,想要倒一杯水。
出乎她的意料,桌上空空如也,居然沒有任何茶壺茶杯。
她終於回頭看向朱聿恒,腮幫子鼓鼓的,卻不說話。
朱聿恒示意太監去取水來,目光盯著外面的瀑布,對著空氣解釋道:「煮茶有炭氣,肯定要遠離寢殿。」
阿南白了這個彆扭的男人一眼:「要喝冷的呢?」
「宮中人手多,吩咐一聲馬上便能現做四季渴水。」
阿南心道:畢竟皇家風範,喝點水都要喊人,這也太麻煩了。
過了不久,外邊茶水送上來,卻還是滾燙的。
阿南吹著杯中茶,在殿內轉了一圈,走到窗邊望向外面。
窗戶正對著瀑布,越過瀑布便是左閣那個門窗緊閉的偏殿。水光幻彩,琉璃屋瓦雕梁畫棟一片氤氳彩光。
阿南迎著水風感嘆道:「要不是袁才人離奇死亡,這裡簡直是神仙宮闕。」
坐在桌前的朱聿恒未曾聽清,望了望她,遲疑片刻,終於起身走近她,問:「妳說什麼?」
「沒什麼,感慨而已。」阿南喝著手中終於不再燙的茶水,抬頭望望瀑布:「這瀑布聲響太大了,足以遮掩很多聲音啊……對了,在殿內香爐撒助眠香的人是誰,查到了嗎?」
「查到了。」朱聿恒皺眉道:「是袁才人身邊的女官,香也是袁才人找人採買的。」
阿南有些詫異:「是她自己?」
朱聿恒轉頭,示意韋杭之將當日殿中當值的太監宮女叫來。
其中一個年長的宮女道:「奴婢們當日將殿內安置好後,袁才人便吩咐我們都退下,說太子殿下睡眠不好,略有聲響便會驚覺。奴婢領著人出去時,看到袁才人身邊的女官拿出一包香往爐內撒,袁才人看了看,讓她再拆一包,說是瀑布聲音太吵了,怕殿下睡不安穩。」
朱聿恒補充道:「女官也已招供,袁才人為邀寵而擅自使用助眠香。」
阿南思忖著,又問那幾個宮女:「袁才人出門之時,妳們曾聽到聲響嗎?」
「瀑布聲音很大,奴婢們候在門外從始至終並未聽到任何動靜。期間怕茶水冷了,奴婢還送了一壺新的進去,當時殿下和才人都在安睡。但奴婢出來後剛將冷茶送去膳房回來,就聽到大家說袁才人出事了,奴婢當時還嚇了一跳,心說我剛剛進去時還毫無異樣呀!」
聽她這麼說,阿南便將桌上的茶壺提起,又給自己倒了杯茶。
夏日炎熱,茶水滾燙,她捏著杯子略一沉吟,又問:「當時窗戶閉了嗎?」
宮女搖頭:「如此暑熱,怎麼會閉窗呢?這通天徹地的八扇門全都開著,可以直接通向後方瀑布。」
「好,我知道了。」阿南等這群宮人都退下了,才轉頭看向朱聿恒,指著對面的偏殿道:「我心裡有個猜測,是關於這兩個左右相對的閣內,兩邊都無人時發生了什麼……你呢?」
朱聿恒緊抿雙脣,沒有回答。
他之前心中油然升起的怪異感覺,此時終於化成了可怕的預感。
左右兩閣,白光,綺霞遭受的追殺,對阿南的倉促定罪,甚至阿南所不知曉的他幼弟的災禍……都意味著同一件事情。
只是,這太過可怕的猜測,阿南不願說,他也不願接受。
他們沉默地站在瀑布前,雪浪般衝擊而下的瀑布離他們尚遠,但水風潛來,讓朱聿恒扶在窗口的手上凝結了細小的水珠。
他的手因為收得太緊,上面有青筋隱隱顯露,令這雙舉世無雙的手增添了一絲不和諧。
阿南在心裡默然嘆了一口氣,輕輕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先不必擔憂:「別怕,或許這也說明不了什麼。畢竟,我看見刺客殺袁才人的時候,你和你娘正在殿內呢。此案錯綜複雜,一定還有什麼我們所未曾窺知的真相。」
朱聿恒沒有回答,但終究還是慢慢地展開了自己的手掌,深吸一口氣,道:「我並不怕,因為我相信她。」
阿南便不再說什麼,只指著瀑布,說道:「還有,我要上去看一看這瀑布。畢竟,在出事前後瀑布的那兩次暴漲,我真的很介意。」
瀑布從兩山之間流瀉而下,左右雙峰高聳,十分險峻。
這座行宮是當年關先生為龍鳳皇帝所建的避暑行宮,在夏秋兩季炎熱之時,以水車牽引下方池水而上,順著粗大的竹筒將水送到山頂蓄水池中,化成瀑布流下,用以消暑。春冬二季則停止引水,上方蓄水池水位降低,瀑布自然消失。
朱聿恒指派了負責檢修水管的老兵帶她上山。阿南對照著地圖,沿著水車向上攀爬。
雙峰陡峭,沿途是一節節粗大的水管,為了避開岩石及過於陡峭之處,管身亦非筆直而上,而是彎折成各種角度,曲曲折折,沿山而上,倒是讓她有了攀爬上去的借力之處。
竹筒是當年關先生設計,以類箍桶的手法拼接,每一根都足有兩尺粗細。雖歷經多年風雨,但只要稍加維護,依舊滴水不漏。
她隨口問老兵:「這邊一般多久檢查一遍?」
「山頂上下往來不便,因此我等只每旬沿水管上來檢查一遍。前次瀑布異常時我也曾上來查過,當時周圍草木有被沖刷的痕跡,可能是池水暴漲之時殃及,其餘並無異樣。」
一路說著,阿南身體輕捷,不多時便攀上了崖頂,站在了蓄水池旁。
水池由條石砌築而成,池水碧綠,周圍長滿了灌木草叢,鬱鬱蔥蔥青綠逼人。阿南撥開草叢看了看,有些灌木上有折斷的痕跡,但因為過去了多日,已長出新芽,草叢更是早已恢復生機。
水池出口處攔著三層細格鐵柵欄,以免有髒物隨瀑布流下,汙了下方水池。
阿南看了看,問:「這水裡沒有魚嗎?」
老兵「咦」了一聲,詫異探頭看去,道:「不可能啊,這池中一直都有很多大小魚兒的!牠們原是順著水管上來的,數十年來在池中逐漸長大,最大的該有一、兩尺了。因池水清澈,我每次上來清理雜物都會看見牠們在水中嬉戲,並不怕人……怪事,怎麼那麼多魚兒都不見了?」
「所有魚兒都突然不見了?」阿南直起身,看著水池正在思索,忽聽身後傳來腳步聲。她回頭一看,朱聿恒已帶人爬了上來。
她詫異地挑挑眉,笑問:「殿下怎麼親自爬山上來了?」
朱聿恒沒回答,只示意韋杭之帶著眾人去守住崖下的通道:等眾人都散開了,才壓低聲音,道:「我想……若妳要檢查機關的話,可能要下水。」
「真是想到一處去了,我正要下水呢。」阿南朝他一笑,見水池邊已經只剩了他們兩人,便抬手俐落地撕下脣上鬍子和加濃的眉毛,又從懷中掏出自己隨身的東西,一股腦兒交到他手裡,再脫了外衣丟給他,只剩了裡面一件貼身的細白布衫兒:「幫我拿著,我去去就來。」
朱聿恒下意識接住她丟來的衣服,抬眼看見她在日光下蹦跳著活動身軀,忍不住在她身後低低問:「為什麼?」
但他的話剛剛出口之際,阿南已經鑽入了水中,潛了下去。
他望著碧綠水面的層層漣漪,下意識收緊了十指,緊抓住她殘留的那些溫度,彷彿這樣便能抓住自己不願承認的虛幻期望,哪怕只有一瞬。
這麼竭盡全力,是為了她自己,為了綺霞,還是,如當初在黃河邊、在楚家、在順天地下一樣,是為了……他?
蒙在他周身的樹蔭清涼,懷中的衣服還留著微溫。
池水中漣漪漸散,碧水如一塊巨大的玉石鑲嵌在遍布青苔的池壁之間,平靜無聲。
因為這太長久的寂靜,朱聿恒的心口忽然掠過一絲恐慌。
這畢竟是關先生所建造的機括,阿南未經查詢便貿然下去,若有個萬一,她是否會被這深不見底的碧綠徹底吞噬?
——至少,也該在腰間栓一條繩索,讓他能有一絲救她的機會。
他正在想著,面前凝固般的碧綠嘩啦一聲,陡然動盪起來。
水下的波濤在不斷起伏,阿南卻遲遲未曾鑽出水面,只看到暗流在綠色的水面下波動。
朱聿恒抱緊了阿南的衣服,大步走近了水池,緊張專注地看向水面。
一瞬間,他腦中閃過要跳下去尋找阿南的念頭,但未等這念頭實施,水面潑剌一聲,阿南的頭已鑽出了水面。
朱聿恒暗暗鬆了一口氣,而她向岸邊游來,抹了一把臉後看見站在池畔的他,臉上滿是古怪的神情。
她抬手抓住池壁,半個身子埋在水下,抬頭望著他欲言又止,卻就是不肯上來。
朱聿恒以為她是脫力了,便俯下身,將自己的手遞到她面前,示意要拉她上來。
阿南張了張嘴,頓了片刻,然後才有點艱難地說道:「那個……你轉過身去。」
朱聿恒疑惑的目光從她溼漉漉的臉上滑下,不自覺地看向了她隱在水下的身體。
她胸前的衣襟散開了。大概是在水下被什麼東西扯住了衣服,原本束緊的胸部也散開了,半露的胸口在不斷波動的水面下隱約起伏,讓他心口猛然一跳,臉也熱了起來。
他將懷中的衣服丟到了池邊草地上,然後飛快地轉過了身。
耳聽得嘩啦啦的出水聲,隨後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應該是她在穿衣服了。
朱聿恒盯著面前的矮樹,竭力收斂心神。
卻聽後面的阿南搞了許久,終於嘆了口氣,鬱悶道:「阿言,來幫我一下。」
他轉過身,一看見她的模樣,頓時身體又是一僵。
她背對著他站著,夏日小衫面料輕薄,又在水中打溼了,她的背籠罩著日光與波光,彷彿只蒙了一層水霧。
他素來知道她身段柔韌修長,卻不知道她的腰那麼細,腿那麼長,在溼衣和日光的勾勒下,簡直令人目眩神迷。
胸口有股灼熱的血一下衝上了腦門,他第一時間移開自己的目光,盡量悠長地深吸進一口氣,又盡量平靜地吐出,勉強抑制自己的失態。
而她卻毫無自覺,指指自己背上鬆脫後又纏成一團的布頭:「你替我繫緊吧。這東西在後背絞成一團了,我的手受過傷,那個角度我實在使不上勁。」
朱聿恒聲音帶著一絲喑啞:「我給妳拿件外袍,幫妳罩住。」
「那可不行,那不是要被人發現我是海捕女犯了?」阿南苦惱地圈臂抱住自己,這個時候真恨不得自己胸小一點了:「行了,男子漢大丈夫別婆婆媽媽的,你就當自己還在冒充太監嘛,反正……」
反正她之前被他騙了,還牽過他、抱過他呢。
朱聿恒抿緊雙脣,慢慢走過來,將那些纏住的布條解開,虛按在她的後背上,替她將亂纏的死結打開。
而她抬手將自己溼漉漉的頭髮抓起,免得被他束在衣帶中。被她刻意染黑的膚色已經有些變淡,蜜色的肌膚上尤帶水珠,修長脖頸上一縷未被攏住的髮絲蜿蜒地貼在皮膚上,曖昧地鑽入衣領之中,令他心口有種難抑的衝動,很想伸手順著衣領滑進去,幫她將這綹髮絲挑出來。
但最終,他的手只是按照她的指點,將她束胸的布條理出來,將兩頭交到她的手中,才沉默地退後兩步。
阿南隨口「喔」了一聲,轉頭去看朱聿恒,卻發現他望著上方窗戶,又看向對面樓閣,神色略有古怪。
「怎麼了?」她問。
朱聿恒搖搖頭,將心中一些不應升起的念頭強壓下去,示意眾太監宮女都退下,然後才道:「妳是朝廷海捕罪犯,只需盡心戴罪立功即可,其餘事情,不必多想。」
「沒良心!你怎麼只記得我做過的錯事,不記得我當初救了你、救了順天、也幫了杭州的事兒啊?」阿南白了他一眼:「我當初豁命救你也沒見你感激我,現在回來幫你也不見你感念我,我怎麼這麼賤呢?」
說罷,她鬱悶地轉身,大步走向了那間偏殿。
朱聿恒默然,只覺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