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邊,太極殿內賀蘭欽將矛頭直指儲君,氣氛登時緊張起來。
太女雖在大事上拎得清,且也算有為人君的氣勢,然揮霍太過、德行不修卻是她死穴。太女黨自然不會主動戳到這點,諸司官員也不會非要逆著劍鋒往上行,在這種事上能開口的,只有諫官。
賀蘭欽當堂指出太女之不德,不過是在履行諫諍職責。
這時候李乘風卻不慌亂,視線掠過賀蘭欽的臉,昂然道:「諫議大夫的意思是,東宮不修德行所以致地動天旱?」她接下去道:「那今日起,本王便齋戒減膳,閉門祈福。若真如諫議大夫及司天臺所說的『都是本王的過錯』,那本王這樣做,總該下雨了吧?」
後半句反問音調陡升,語氣中絲毫不懼諫官的攻擊與指摘。
賀蘭欽聽了她這咄咄逼人之詞,卻不動聲色。
他不開口,殿中便再無第二人敢接太女這話,這時候一直靜坐著的宗亭卻道:「天意一向難揣,只怕到頭來還是不下雨,關中百姓便是白等了。眼下當務之急,是要未雨綢繆,做最壞的打算。倘若此災避無可避,也好過屆時手忙腳亂。今年秋稅並不樂觀,卻還要貼補山東,倉部、金部、太府寺最好還是先拿個議案出來。」
他講的倒是大實話,聽起來無可指摘,且順利轉移了話題,給了眾人一個臺階下。
女皇咬緊的牙關緩緩鬆開,語氣依然沉緩。「就照宗相公所言,先擬個議案吧。」
講完,她額顳突突刺痛起來,面色瞬時發白,旁邊內侍敏銳察覺到了這變化,急急忙忙宣了退朝。
女皇起身,內侍要上前扶,她卻甩了寬大袍袖,咬牙對內侍道:「叫太女來見朕。」
群臣陸續起身,宗亭對賀蘭欽視若不見,自行轉著輪椅往外去;而那司天臺的年輕推官隨司天臺監起身後,迅速看了一眼賀蘭欽。
賀蘭欽未察覺到這目光,逕自走到李乘風面前,語氣平和地躬身道:「適當齋戒養生亦非一無是處,關中百姓企盼的這雨雪,就指望殿下了。」
李乘風眸光銳利,目標明確且狠毒。但在賀蘭欽直起身抬頭的瞬間,她卻又斂了這目光。此時有內侍匆忙跑來,對她傳達了女皇召見的口諭。她面色一沉,拂袖轉身而去。
通往內殿的路上,空氣渾濁得令人胸悶,路旁排水溝裡幾近乾涸,甚至透出臭味來;而邊上排排槐柳,也絲毫沒有要醞釀新綠的打算。
內殿破天荒地沒有燃燈,光線便暗淡許多,窗子都緊閉,守衛森嚴,恍若一座大囚牢。
而女皇,彷彿就是其中唯一的囚徒。
女皇頭疾發作,心火上更是澆了幾桶油。李乘風進殿時,恰好是這把火燒到最旺時。
她如常跪地俯身行禮,然這禮還未完,一只裝了熱燙茶水的杯子便朝她飛去。水濺溼衣袍,杯子落地而碎,瓷片飛起,從皮膚上擦過,臉上瞬間就有了血痕。
李乘風動也不動,內殿中只有女皇的聲音。
「朕與妳說過多少次了,胡鬧得有個限度。妳要吃多少苦頭才長記性?」她聲音裡透著壓迫,呼吸也因為疼痛變得濁重。
李乘風抬手擦了一下臉上的血,卻問:「倘兒臣是男兒身,朝臣們可還會說這樣的話?陛下又是否再覺得這是胡鬧?當年阿兄之行徑,比兒臣的有過之無不及,為何朝臣、陛下卻對他那般縱容,連諫官也從不指責他不修德行?只因他是男子,兒臣是女子嗎?」
她不認錯,也不服軟,女皇心頭怒火更盛,頭疾痛得人甚至睜不開眼,抬手就將案上奏抄扔過去。
李乘風穩跪不動,不閃避、不忌諱地反問:「陛下如果也是男子,如今可會落到孤身一人無人伴的地步?」
這一言將整根弦都拉緊,殿中只聞得女皇濁重得無以復加的氣息。女皇雙手緊緊按住臺案,手背上青筋根根分明,下一刻似乎就要掀翻整張御案。然她心頭怒火在瞬間轉為陰霾,整個人也委頓了下去。
「兒臣不願重蹈陛下覆轍,也不想受朝臣掌控,兒臣想像男人一樣活著。」李乘風臉上的傷口又滲出血珠子,然這回她連抹也未抹,竟是堂而皇之地起了身,不顧跌坐在案後的女皇,出了這昏昧的內殿。
◎
這時的齊州境內,愁雲滾滾,一場大雨似乎就要傾盆而下。
一眾人將驛所都翻了個遍,卻壓根未見李淳一和中郎將謝翛的身影。就在驛丞忐忑地杵在堂中,不知要怎麼辦之際,一位衛兵忽然驚道:「吳王留了信!」
他急急忙忙拿著那信筒走出來,將其遞給了都督府的使者。
使者一看那信筒上封著都督姓名,便知是給元信的。他不敢久留,趕緊出門往都督府去。
這只信筒遞到元信手上時,李淳一與謝翛已經出了城門。
元信打開那信筒,卻只拆出一張白紙,他眉毛猛地一挑,交代身邊僚佐道:「那報災奏抄緩兩日再遞。」
僚佐「喏」了一聲。元信微微斂眸看向堂中香案,又道:「對外稱吳王在齊州失蹤,開始搜尋吧。」
僚佐領命退下,外面淒厲的大雨就傾倒了下來。豆大的雨點劈里啪啦砸在地板上,從水跡斑駁到溼透也只是眨眼的工夫。
李淳一這時奔行在往東的路上,騎得飛快。謝翛快馬加鞭追上去,隔著雨簾與她大聲道:「前面有粥棚,等雨停了再走吧!」
李淳一行至粥棚前,勒韁下馬,站到棚內避雨。一場大雨阻斷了行程,正好可以歇一歇,連夜趕路到這會兒,連馬也累了。這賑災粥棚周圍人煙稀少,寂寞的大鍋裡盛滿了渾濁雨水,只有泥沙卻無一粒粟。
李淳一抖落袍子上的水,看著棚外的瓢潑大雨,眼中生出憂慮。謝翛遞給她一塊餅,稱呼穿了男裝的她為「郎君」,並問:「御史臺那兩位里行(註一),可是直接往北面去了?」
李淳一不作聲,低頭將餅掰開一小塊,塞進嘴裡。
御史臺這兩位里行都是透過今秋制科剛提上來的,出身淮南,先前都在李淳一籌建的寺觀內待著。這兩人也在李淳一此行的車隊中,但那晚還未到齊州驛所,李淳一便令他們先去北面核查災情。此外,還有水部司與倉部司幾人,也在剛進入齊州時分開出行,去檢覈受災及賑災情況了。
李淳一作為巡撫賑給使,有權決定檢覈的手段,並不需要與地方通氣。
她這番安排無可指摘,但因太沉得住氣,以至於謝翛一直在猜。直到她自己也悄無聲息出來親自核實災情,謝翛才大約明白她的想法──
進都督府之前,她必須自己心裡有一本明帳,這樣才有底,才能夠去為百姓、為朝廷爭。
天地間潮氣翻湧,流離失所的災民只能忍受這無處討說法的不仁慈。
越來越多的災民擁入臨時搭建的粥棚內,卻見不到一個州縣官吏。李淳一的馬淋了雨,甩頭低嘶,就在她打算上前將牠牽進來時,霎時有一孩童朝她衝過來。那髒兮兮的小兒幾乎是撲上來抓住她的手臂,因為餓昏了頭,甚至咬住她緊抓著乾糧的手!
謝翛反應過來,霍地將那孩子扯開,那小兒卻不餒,餓狼般再次朝李淳一撲去。謝翛猛地將那孩子抱起來,緊緊鉗制住,不讓他再胡亂攻擊。
李淳一將那塊餅遞過去,小兒一把奪過,低下頭登時狼吞虎嚥起來。待他吃完,謝翛才將他放下,鬆開雙臂,低頭問道:「你的家人呢?」
他講的是官話,小兒似乎聽不懂,只顧著舔指頭上的餅屑。
謝翛看他沒反應便也不再管,一抬頭,卻注意到李淳一的手──虎口處一排狠毒的牙印,皮肉已經破了,血珠子正往外冒。
「郎君可還好?」謝翛趕緊摸出膏藥遞過去,李淳一卻未接。
她盯向小兒額側、頸間的水泡,忽然上前兩步按住他額頭,那小小額頭滾燙,嘴巴乾裂出血。她心中一怔,下意識往後退了半步,抬頭卻見西面流民為了搶奪乾糧朝這邊擁來。
謝翛見狀不妙,一把牽過韁繩催促道:「郎君快走!」
李淳一聞聲卻還站在原地,謝翛見她動也不動,顧不得太多,抓住她的臂就推她上馬,同時自己也蹬上馬背,鞭子揮向了李淳一的那匹馬。
駿馬狂奔,李淳一卻轉過頭去看。隔著漫漫雨簾,方才那孩童兩眼瞪得老圓地看她遠去,面目裡是無盡的茫然與無措。那小小身軀忽被蜂擁而來的人群撞倒,幾度想要掙扎著爬起,卻最終沒能再站起來。
馬越是往前,人群便越是遠去,大雨裡的馬蹄聲與呼吸聲,似乎都響在耳畔。
雨漸漸停了,馬也停下來,兩人渾身都溼透。
李淳一雙手緊握著韁繩,面對謝翛「郎君怎麼了」的反覆詢問,也只低頭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
那臉慘白一片,毫無血色。
淮南水患時的可怖情形還歷歷在目,但她抬起頭,面上便換了沉靜與該有的穩重。
她回頭看了一眼,嚴肅道:「是疫病。」
粥棚裡那個孩子的命運已不可逆轉,齊州府百姓的命運亦未可知。驟雨止歇,天地間一片灰暗,馬低頭啃嚼地上枯草。謝翛聽李淳一講完,面上忍不住閃過一絲憂慮。
他在軍中也見識過疫病,但那已經是接受控制與隔離後的疫情,與民間爆發的疫病有很大區別。山東儘管富庶,但各州僅有醫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醫學生也不過十三、四個,如果疫情爆發,官方的救助與控制力量實在有限。
此時兩人已到青州境內,謝翛心中打起了退堂鼓。「殿下,可要折返回齊州府?」
「去青州州廨。」李淳一面不改色地說完,一夾馬肚便往前馳去。她周身潮溼,陰冷的風將寒意全吹進了皮肉骨頭。
沿途無人收殮的屍體隨處可見,似乎連四肢也不齊全,森森白骨被暴雨刷去汙泥、腐肉,全都露了出來。
駿馬疾馳,至青州州廨時已近傍晚。李淳一翻身下馬,剛往前兩步,門外吏卒便攔了她的路,理直氣壯地對一身布衣的她道:「州廨豈可容閒人擅入?」
李淳一站著不動,謝翛走上前,將符遞了過去。「請通報一聲。」
那吏卒捧起符來看了好一會兒,又看看他們二人馬匹,臉色瞬變。就在他要揣了那符往裡通報時,卻有人踏著積水從衙門內走出來。
那人一身緋色官袍,而青州境只有一人能穿這服色──
此人便是新任刺史顏伯辛無疑。
刺史既然為州廨最高官員,自然也是一州之長。然這一州之長,也不過二十幾歲年紀,清秀俊朗,哪怕因災情難解而枯瘦了一些,也不見頹靡之色。
李淳一看向他時,他也朝李淳一與謝翛看過去。
那吏卒倏地向顏伯辛行禮,雙手將謝翛的符奉上。顏伯辛卻不接,只板著臉問:「七個縣的縣令,到現在一個也沒來嗎?」
吏卒小聲揣測道:「按說也該到了,大約是被先前那場大雨耽擱了?」
顏伯辛面色沉重,又瞥一眼吏卒手裡捧著的符,瞬間明瞭這兩位來客的身分,但他只不卑不亢地低頭拱手。「臣未料吳王會到此地,失迎了。」言罷,他抬首看向李淳一,也不請她進州廨。
身為顏家嫡子,顏伯辛渾身上下都透著百年世族的高傲,這家人甚至不屑與出身關隴的皇家聯姻,又怎麼看得起這個家族裡的一個庶女?
謝翛剛要開口,李淳一卻已同顏伯辛道:「顏刺史是要本王與你一道等那七位縣令嗎?」
「吳王若願意一起等,那就等吧。」他順著她的話接下去,絲毫不顧她此時渾身潮溼的狼狽模樣。他脊背挺直,也不懼外面寒風,就當真站在州廨門口等轄下那七個縣的縣令。
吏卒小心翼翼將廊燈點起來,最後點到顏伯辛頭頂那盞時,夜幕徹底垂覆了下來。守在外面的衛兵一動不動,謝翛已有些沉不住氣了,而李淳一卻不動聲色,當真是陪顏伯辛站到了天黑透。
天寒地凍,下過雨的青州尤其冷。本來衣服就是潮的,李、謝二人都快被凍成了冰,顏伯辛卻看也不看他們一眼,面色沉靜簡直如死水,直到他聽到那越發近的、帶著潮溼的馬蹄聲,冰封的臉上才有了一點兒微不起眼的變化。
來者是益都、臨淄兩縣的縣令,一看這架式,各自心裡頓時「咯登」一下。兩人不明就裡,便只好對著緋袍的新刺史行了禮,然顏伯辛不開口,弄得他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杵在那。顏伯辛同樣不讓他們進州廨,他們便只好一起等那餘下的五個縣令。
兩縣令被凍得牙打顫,心中將顏伯辛與那幾個遲到的縣令狠狠罵了一通,眼角餘光則不自覺地瞥向旁邊的李淳一與謝翛。
空氣裡一點兒人聲也沒有,只有呼出來的熱氣成了團團白霧。等那五位縣令陸續到了,顏伯辛看向李淳一,道:「吳王不懼嚴寒等到現在,可是要一起參會?」
顏伯辛完全把控著局面,這點令謝翛十分不悅。
他一路上見慣了李淳一沉穩有主見的模樣,這時見她如此被動,實在不舒服。然李淳一似乎另有謀算,她視線逐一掃過那幾個縣令,開口道:「既然都到了,就不要再耽誤,進去詳談吧。」
她沒有太女咄咄逼人又張狂的架式,反而有幾分禮賢下士的謙虛、謹慎與穩重,且似乎格外沉得住氣,多少令顏伯辛心中樹立起來的偏見有一點兒動搖。一眾縣令也是吃驚,根本沒想到這著一身布衣之人竟是女皇遣派至此地的巡撫賑給使。
一眾人各懷心思進了議事公房,顏伯辛空出主位不坐,但也不請李淳一坐。李淳一不占地方官的主位,只逕自坐在他對面的位子。謝翛與顏伯辛同階,卻在他下首坐了。各縣令再依次往下坐,最末坐了個秉筆書吏。
一杯熱茶送上,連晚飯也不給,便開始議事了。
顏伯辛之所以將底下七個縣的縣令喊來,主要還是因為賑災不順利。前一任留下的爛攤子還沒解決,轉眼又碰上了大地震,這個官換誰做都難。
一書吏捧著簿子過來放下,顏伯辛壓著不動,只說:「難處我都了解,重複的話不必說,揀要緊的情況報。」
三五個縣令面面相覷,也有逕自低著頭不吭聲的,個個心中都掂著一桿秤,一頭垂著自己的考課(註二),另一頭掛著百姓生計。
「一件要緊的事也沒有?那我來說。」顏伯辛翻開簿子道:「博昌、壽光兩個縣,賑濟糧一粒也撥不出,連粥棚都只是擺擺樣子,是打算指望用朝廷的糧食來賑災嗎?義倉為什麼不開?」
被點到的兩個縣令含糊其辭道:「義倉也開過一陣子,但刁民實在過分,如今已是空了。」
「根本是從來都空無一粟吧!」顏伯辛語氣驟急。「前年、去年留縣的稅收,沒有按規矩充義倉,被拿去做什麼用了?」
兩縣令年紀也都不小,被一個年紀輕輕的刺史這般訓著,心裡十分不快,卻一點兒辦法也沒有。顏伯辛不好糊弄,在他們來之前,就已經將各縣情況摸了個透,今天這議事會,便是要找他們算帳呢!
這事一搬上檯面,在座的幾位心裡頓時沒了底,眼角餘光都默默瞟著顏伯辛手裡的簿子,不知他對底下縣鄉的情況到底清楚到什麼程度。
而謝翛這時也回過神來了。顏伯辛所做的事,本質上與李淳一在做的並無區別,說到底就是初來乍到信不過,因此要親自核驗清楚,待心中有一本明帳後,坐下來才有可能占據主動權。
顏伯辛續道:「義倉空著,連常平倉(註三)的糧都被炒到高價,逼著百姓賣永業田(註四)求一口糧嗎?青州百姓以農為生,田若賣給大戶,明年吃什麼?請問兩位明府,你們這是要逼著百姓反還是逼著百姓去死?」
其中一人仍辯駁道:「常平倉的糧價並不是官府炒上去的,是那些大戶貪得無厭且狡猾,這才──」
「大戶?兩位明府與縣中大戶毫無瓜葛來往嗎?」顏伯辛說話直截了當,直踩痛處,罵這兩位縣令與大戶之間牽扯不清,縱容土地兼併,才致貧戶無立錐之地。
那人頓時歇了聲。
「今年的考課已經結了,至於明年諸位的考課會是如何,得看能否順利渡過此次難關。」聲音因為長久疲憊略帶啞音,銳意氣勢卻不減。「實際的受災戶數,我已遣人核查過了。之前你們虛報的我暫不追究,但今日起撥給的正倉糧,要如實發放、如實記載,錯了一斗我都要計較。」
「這──」壽光縣令為難道:「但災糧發放時,局面常常不好控制,嘩嘩米糧像水一樣無度地撲出去,地上卻看不見潮,該餓著的百姓還是餓著。」
千乘縣令緊跟著附議。
「以工代賑。」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沉默的李淳一只講了四個字。
顏伯辛眼角不經意間迅疾挑了一下,幾個縣令也循聲看過去,壽光縣令搶著道:「微臣願聞其詳。」
「既然無償賑濟往往會亂,那就換個辦法。」李淳一不慌不忙接著道:「青州蒙此大震,損毀眾多,春汛將至,許多河堤得抓緊時間修補,只靠官健(註五)似乎是不夠的,不如僱用災民,這樣免得災民四處流竄,也利於儘快重建青州。」
千乘縣令聞言頻頻點頭,而顏伯辛竟是接著李淳一的話頭,往下講了以工代賑的具體實施細節。
他按在簿子上的手未再動過,那簿子也沒再翻開。
從嚴控物價到控制田畝兼併,這會議也隨著夜越來越深入,最後壽光縣令又稟道:「壽光縣內已有疫情初顯,下官一路過來時,也見有不少流民死於途中,倘不加管控,只怕要釀成大禍。」
話題終於講到疫情上,顏伯辛年輕面龐上的表情顯然更加沉重,但他仍無一絲一毫的氣餒,有條理地回道:「各縣鄉要遣專人掩埋無主屍骨,病死家中的則由家人收殮埋葬,但不得停靈;倘能借寺廟的就借寺廟,不能的要單獨設立病坊,不得探視、隨意出入。即日起,青州醫署的十三位醫學生會下各縣遣發藥方,張貼告示,周知百姓進行防疫。」
「糧食緊缺,這藥恐怕也難啊……」壽光縣令臉上又顯出憂色來。
「給百姓的防疫方不會太複雜,最多一、兩味藥,藥材也不能是稀缺物,這樣易記,平民百姓也更易獲得。」李淳一看向坐在最末的那書吏,書吏趕緊將紙筆遞上。
李淳一提筆寫完,起身將方子推至案中央。「此方是太醫署確認有效的,且之前淮南水患時亦有使用。」
顏伯辛至此已不打算再翻手下的簿子了,他用眼角餘光瞥了眼李淳一,心裡是說不出的複雜滋味。李淳一今晚僅僅說了兩件事,然在這兩件事上的想法與他心中所籌謀的出奇一致。
他心中的偏見越發動搖,但最後陡然回神,看向一眾沉默的縣令道:「還愣著做什麼?等明日天亮嗎?今晚就去做。」言罷,起身吩咐書吏將議事要點、災後條令及防疫方分抄給諸縣令,便將他們連夜趕回各自治所。
青州的雨,停了一下午,卻又下了一徹夜。
這無邊無際黑乎乎的雨,將青州淋得泥濘不堪,河道水位也瞬間湧了上來,偌大的冷寂州廨中,沒有一個人能睡好覺。
一大早,李淳一便隨顏伯辛前去治所的病坊,走到門口,顏伯辛道:「此處瘴氣甚重,殿下玉體金貴,請不要進去了,就此回吧。」
他說完看向李淳一,只見她眼底疲色甚重,面色也十分難看,嘴脣幾近發白,看起來狀態極糟。
「殿下不該來。」他察覺到她應當在發熱,而昨晚是他讓她在寒風裡穿著潮溼的袍服站了整整兩個時辰。
「無礙。」
這聲音已非常低了,顏伯辛卻不再攔她,逕自撩袍進了病坊,莫名察覺到不對,陡聞身後一陣驚呼。
「殿下!」
他驀地轉過身,卻見李淳一已是倒在泥濘的路面上。
他心中一怔,遲疑半晌,卻忽然上前兩步,低頭對失去意識的李淳一冷冰冰道了一聲「冒犯」,便俯身將她從泥地上抱起來。
天地不仁起來,當真是無計可施。需要雨水的地方一滴不肯落,不要雨的地方卻嘩啦啦倒得慷慨。
青州到處泛著潮意,重建工事難以繼續,廟宇、災棚裡人滿為患。一女童縮在阿娘懷裡,面上脖頸已長出斑疹,呼吸越發沉重,連額頭也滾燙。那母親躲在角落裡一動也不敢動,女童閉著眼,聲音嘶啞地要水喝,她阿娘便心焦起身去為她尋水。
這時忽有人在她們身邊驚叫起來。
「有人出疹子了!」
那母親面上駭然又張皇,周圍的人尖叫著避開,只有外面捂著口鼻的衛兵衝進來,要攆她們出去。
小女童昏昏無力,聞得嘈雜驚叫,想睜眼卻不能,只張嘴發出痛苦呻吟。她阿娘緊緊抱著她,眼淚迸出眼眶,憤怒又無聲地抗議著。然這抗議實在有限,周圍「快趕她們走」的呼聲越發高昂,衛兵便二話不說將她們趕出去。
雨無邊無際地下,吧答吧答落在地上,水珠子在棚外飛濺。
母女二人到底是被趕出了災棚。這幾日見慣了此景的一個垂暮老者,坐在門口呆呆望著,口裡喃喃道:「生民卑賤哪……」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青鳥(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古代小說 |
$ 221 |
言情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大眾文學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青鳥(下)
「離本王遠一點兒。」
「不可以。臣的心在殿下這裡,倘若離得太遠,臣會死的。」
被女帝厭棄放逐的么女,吳王李淳一╳傾倒眾生權臣中書侍郎,宰相宗亭!
久別重逢,各懷鬼胎,是虛情假意逢場作戲,還是裝成無意隱藏深情?
性別反轉的追夫之路!!!人氣作家趙熙之的創作經典《求女》,全新修訂出版!
*13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網路作家得主!
*原創之星,作品《夜旅人》改編電視劇!
*萬千粉絲追捧!作品題材多樣,寫作風格細膩!
//
國家大災,太女失德,接連打擊讓女皇氣得身子都不好了。
她是這座皇城的囚徒,其他人卻不願陪她一起關著。
吳王李淳一親下民間治災,天災已難控制,偏偏還有人禍。
他們捏造災情,騙取賑款;百姓死活,從來不是考慮的重點。
而關隴地方在此時亂了。
此變看似內亂,實則可能引起外患,
導火線正是宗亭跟李淳一的婚事!
宗亭出身當地,背後母族軍隊雄踞,本人也位高權重。
吳王已有一爭之力,若能破壞他跟李淳一的結盟,
拔除他宰輔之位,只當個無權的王夫,等同斷了她一臂!
他生性狡猾,城府極深,又愛吃醋,
所以他不能讓這些人如願。
他有自己的女皇,要扶著她直上青天──
作者簡介:
趙熙之
人氣作家,13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網路作家得主。作品題材多樣,寫作風格嚴謹細膩。
已出版作品:《夜旅人》、《配婚令》、《有間書坊》、《小鎮做題家》
微博:@趙熙之
微信公眾號:賣故事的趙公公
章節試閱
另一邊,太極殿內賀蘭欽將矛頭直指儲君,氣氛登時緊張起來。
太女雖在大事上拎得清,且也算有為人君的氣勢,然揮霍太過、德行不修卻是她死穴。太女黨自然不會主動戳到這點,諸司官員也不會非要逆著劍鋒往上行,在這種事上能開口的,只有諫官。
賀蘭欽當堂指出太女之不德,不過是在履行諫諍職責。
這時候李乘風卻不慌亂,視線掠過賀蘭欽的臉,昂然道:「諫議大夫的意思是,東宮不修德行所以致地動天旱?」她接下去道:「那今日起,本王便齋戒減膳,閉門祈福。若真如諫議大夫及司天臺所說的『都是本王的過錯』,那本王這樣做,總該下雨了...
太女雖在大事上拎得清,且也算有為人君的氣勢,然揮霍太過、德行不修卻是她死穴。太女黨自然不會主動戳到這點,諸司官員也不會非要逆著劍鋒往上行,在這種事上能開口的,只有諫官。
賀蘭欽當堂指出太女之不德,不過是在履行諫諍職責。
這時候李乘風卻不慌亂,視線掠過賀蘭欽的臉,昂然道:「諫議大夫的意思是,東宮不修德行所以致地動天旱?」她接下去道:「那今日起,本王便齋戒減膳,閉門祈福。若真如諫議大夫及司天臺所說的『都是本王的過錯』,那本王這樣做,總該下雨了...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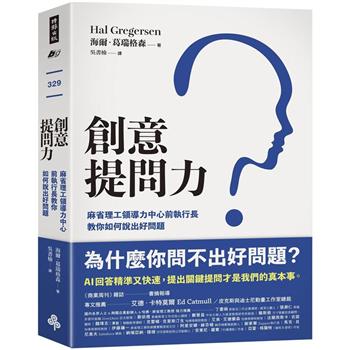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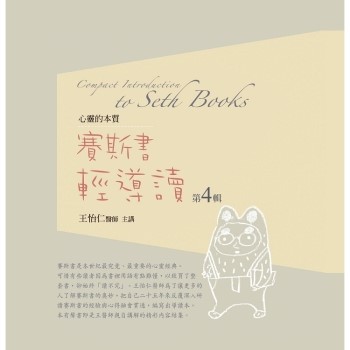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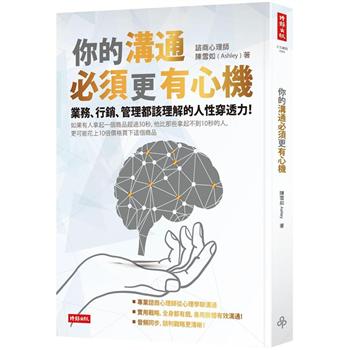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速成+歷年試題](不動產經紀人)](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