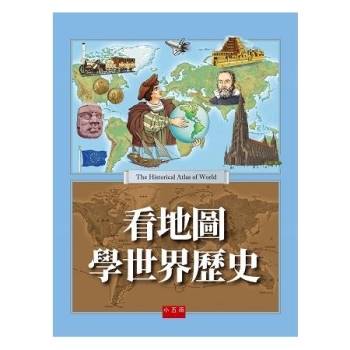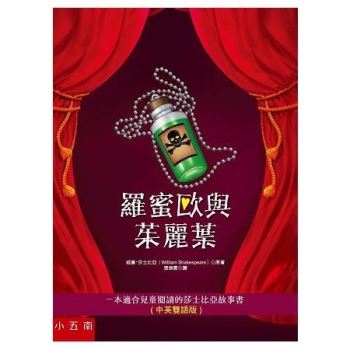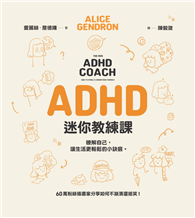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
《李海叔叔》作者尹學芸鄉土文學合集
自私人性、扭曲倫理、陰暗官場、兩代糾葛
透過刻劃社會底層生活,逐一向讀者披露——
《李海叔叔》作者尹學芸鄉土文學合集
自私人性、扭曲倫理、陰暗官場、兩代糾葛
透過刻劃社會底層生活,逐一向讀者披露——
「我在新疆的土地上行走,為什麼總聽見有人在哭——哭的原來是風。」——尹學芸
【青黴素】
正坤是罕村唯一的赤腳醫生,自從雲丫被青黴素治好,正坤便成了村民口中的「神醫」,那青黴素更是包治百病的「神藥」,但凡村民有個三病兩痛,全都擠到正坤家問診……
正坤是個唯唯諾諾的男人,什麼都聽母親趙蘭香的安排,卻娶了潑辣剽悍的鐵秀珍,原本婆媳天天吵嘴,他大氣都不敢喘一聲;可是不知從何時起,正坤變得會動粗、謾罵,昔日那個親切俊美的醫生不再……
村民開始接二連三死亡,先是正坤的父親和兩個兄弟,再來是鐵秀珍的父親和正坤自己的女兒,一切似乎都發生在給正坤看過病以後……
【東山印】
東山印,即在東山的山頂上造一枚石頭印章,印臺是基石,印柄是瞭望臺,站在該處能夠俯瞰塤城全景,印章中心鏤空的部分則是博物館,與塤城有關的歷史文物全收藏在館內。
東山印的構思源自於李東印,他是塤城的空降官員,看出塤城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蘊的古城,力圖藉由博物館提升當地知名度,如此積極的建設提案卻遭到了塤城上下的反對,而副縣長馮曖輝和其助手楊青田是少數支持者。不料,就在工程進行一年零八個月時,一輛大貨車硬生生奪走了李東印的性命……
如今楊青田仍然在官場打拚,馮曖輝早已不問世事,這次卻要求昔日下屬代為轉交一封信,原因無他——現任官員聲稱東山印「有礙觀瞻」,申請拆除,而上頭已經予以核准了……
【灰鴿子】
罕村的朱桂鳳天生有無痛症,做起事來總是瘋瘋癲癲不計後果,因此被村民戲稱為「三瘋子」,她有一個極愛自己的老公蘇小抱。
這天三瘋子找上新任官員趙寶成,控訴鄰居不讓自己偷吃雞蛋,趙寶成不耐煩地趕走這對裝瘋賣傻的夫妻。後來三瘋子不慎弄傷了腳,逢人便說是趙寶成害的,揚言要到城裡控訴他的惡行。趙寶成起初不當回事,誰知三瘋子真的這樣做了;再後來,三瘋子竟沒了一條腿——「骨壞死,不及時截肢,性命攸關。」醫院上下都這麼說,而趙寶成也被冠上了酷吏的惡名……
【四月很美】
四虎奶奶即將過百歲生日。四虎爺爺年長了奶奶十三歲,兩人膝下無子,為避免爺爺走了以後奶奶無人照顧,當年四虎爺爺跟張德培家商議好,將來由張家看顧奶奶起居,等奶奶過世之後,宅院由張家繼承,張德培原本就是個愛計較的,想了想便高興地應下。誰知道奶奶一活就是九十九歲,眼看要一百歲了,身體還十分硬朗。張家的人漸漸不耐煩起來,只有張家兒子張帥與奶奶親近些……
那日四虎奶奶說要外出賞花,由張德培的老婆段玉春推著,兩人卻在路上拌起嘴來,段玉春忿忿不平地說四虎奶奶曾經犯下「偷竊」罪,霎時間,紅衣裳、嘎拉村、麥秸垛……一件件往事如天雷般轟進四虎奶奶的腦海中!緊接著,車子失去平衡,四虎奶奶從上頭摔了下來……
【補血草】
桂二奎與屯屯是銀行裡的上下級,明面上是這樣,平時屯屯會喊二奎為「哥」,買東西送給二奎的兒子,但私下裡也沒太多交集,這種曖昧又疏離的感覺,甚至讓桂二奎的妻子、屯屯的前夫質疑兩人是否有不正當關係。
屯屯遠在新疆的父親罹患癌症,堅持要這個漂泊在塤城的小女兒親自為自己採摘補血草——一種當地出產的草藥。向桂二奎告假時,後者什麼也不說,只給了屯屯一疊鈔票。
一場看似普通的探親之行,卻意外揭開了一段埋藏多年的情緣與人倫糾葛……
本書特色
本書為尹學芸中篇鄉土小說合集,一共收錄五篇。故事以「我」(雲丫)的角度出發,記述罕村、塤城小人物間的點點滴滴:表面親切和樂的農村居民,私底下卻各懷鬼胎;聲稱為人民謀福祉的父母官,其實正打著踩踏屍體上位的算盤……作者以深厚的文學功底及洞悉世事的眼光,將對現實的觀察寄託於字裡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