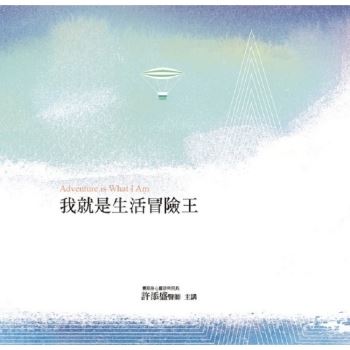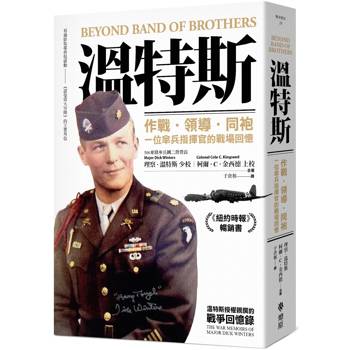「老天爺沒有眼睛……祖宗沒有眼睛……」
無惡不作的地主豪紳、被壓榨的農民、自然災害的侵襲
在農民們好不容易群起反抗時,卻又遭軍隊殘酷鎮壓
他們付出的,是難以想像的慘痛代價……
無惡不作的地主豪紳、被壓榨的農民、自然災害的侵襲
在農民們好不容易群起反抗時,卻又遭軍隊殘酷鎮壓
他們付出的,是難以想像的慘痛代價……
▎「我們不要做人了嗎?我們哪裡來這許多錢!」
葛生嫂立刻攀住了他的手臂,叫著說:「華生!我們真活不下去了!又是斷命的捐錢!聽見嗎?要我們出五元!千刀萬剮的瘟麻子!不答應!不答應!不答應……」
「不止五元呢。」黑麻子微笑地說。「還要備一桌酒席,還要……」
「還要什麼?」華生又前進了一步,準備舉起拳頭來。
黑麻子倒退了一步,說:「還要你一道去──來!」他回頭對著門外叫著。
門外一陣槍柄聲,衝進來了兩個保衛隊丁,用上著刺刀的槍尖對準著華生。
「帶他走!」黑麻子叫著說。
華生正待抵抗,一個隊丁舉著槍尖,往前走進幾步逼著他,另一個隊丁已經握住他的兩臂,接著用繩索把他捆上了。
▎「你以為我會想你嗎?我其實恨你已極!」
過了一會,她的臉上露出了苦笑,叫著說,「爸……你來……」
她父親立刻進來了。
「我聽你主意了,無論和誰訂婚……」
「真的嗎……好孩子……」她父親滿臉笑容的說。「那麼,就是……阿珊怎麼樣呢?」
菊香低下了頭。
「你終於自己清醒了,好孩子……這原是你一生的福呵……不瞞你說,人家的……訂婚戒指早就送來了……單等你答應一個『是』字呢……」
他說著從箱子裡取出一枚金戒指,交給了菊香。
菊香沒仔細看,便把它套在自己的手指上舉起來給阿英聾子看:「告訴他,我已經和別人訂婚了……是傅阿珊,聽見嗎……」
隨後她倒在床上,又傷心地哭了起來。
▎「便宜了你們這班豺狼,傅家橋人又得多受荼毒了!」
華生回過頭來,黑麻子拿著一支手槍正對著他的額角。那一邊是阿品哥的手槍對著阿波哥。不曉得在什麼時候阿如老闆已經鬆了綁,也握著一支手槍對著臺前的人群,雄糾糾地站著。戲臺後端的兩道門邊把守著孟生校長,阿品哥和阿生哥。其他的人都露著非常驚駭的神情,坐著的站起來了,站著的多退到了戲臺的後方。葛生哥發著抖,拖住了黑麻子的手臂。
傅青山站在中間,露著狡猾的微笑,喊著說:「不要怕,把武器丟掉的沒有罪,我保險。你們都是上了別人的當呀……」
群眾站住了,紛紛把扁擔,棍子,鋤頭和釘耙丟在自己的腳邊。同時臺上已經出現了十幾個灰色的兵士,一齊對群眾瞄準著駁殼槍。一個官長走到鄉長面前,行了一個軍禮,遞給他一封公文。
「奉連長命令,單捉主犯!」
本書特色
本書反映了農民在走投無路時憤怒的情緒和最後的奮起反抗,精心刻劃了不同性格、不同類型的農民形象,生動地展示了浙江農村獨具地方色彩的風俗民情,是現代鄉土文學的重要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