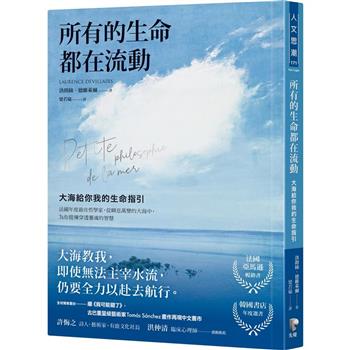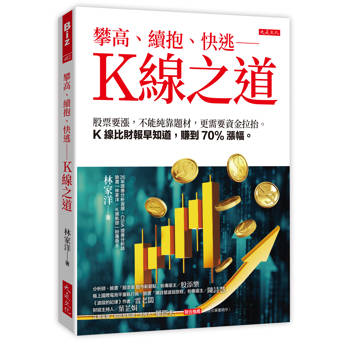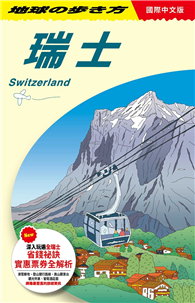一枝柔軟而富於彈性的毛筆,
為什麼演化為不可替代的載「道」之「器」?
由此產生的中國書畫藝術具有怎樣的獨特屬性?
「書為心畫」、「畫如其人」,生命與藝術如何融為一體?
以二十年之苦心孤詣,解答傳統文化所面臨的時代命題
▎「筆軟則奇怪生焉」──何以為奇?何以為怪?
蔡邕所用的「奇怪」一詞,提示了書法線條在藝術表現上的豐富性一一濃、淡、枯、潤、粗、 細、剛、柔,穩與險、暢與澀、老與嫩、奇與正,張揚與蘊蓄、精微與渾茫、迅捷與雍容、雄壯與優雅、豪邁與謹嚴、灑脫與沉鬱……任何一門藝術,都建立在對複雜多重矛盾關係的駕馭調和上,藝術的高度與藝術的難度緊密相關。
▎除了訓練,還需要那些額外的靈性,方能達到「下筆有情」
藝術的「別才」,乃是人性深處的一種妙有的光輝,一種精神與情感的力量。一個人的「別才」與生俱來,九歲的時候就有了,九十歲的時候還在,但它僅僅是成就藝術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源自精神與情感的本質力量,只有透過後天學問的滋養,技法功力的錘鍊,才有可能發揚光大,否則必然流於狂花客慧、浮光掠影。
這就好比小孩子的塗鴉往往有天真稚拙的趣味,齊白石的畫也有天真稚拙的趣味,但兩者不是一回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當代繪畫與古畫最大的不同,在於「遠意」
在俗世中浮沉的人們,「自由」談何容易?對「自由」的嚮慕,往往正是對付現實壓迫的一種心理平衡。魏晉人最崇尚自由放浪的生活態度,是因為他們身處的環境最為酷烈,只有縱情山水、享樂與玄談,才能「暫得於己」,讓慘澹壓抑的人生透出一絲縫隙來。中國人所特有的山水詩、山水畫都於此際肇端,隱逸思想也於此際發達。
當一個人流連於山水丘壑時,可以「遠」於俗情,得到精神上的解放。
▎為什麼長大後,就不知道該怎麼進步了?
人們為什麼總是在「有餘」處持續用力,而不願意去彌補「其本分之不足」呢?除了思維慣性發揮作用外,更深層的原因是,於「有餘」處能夠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以及能力所帶來的「快感」;而要彌補改進「不足」之處,則是一件麻煩而「乏趣」的事,需要清楚的認知和直面自我的勇氣。
正如一個偏好進攻的競技選手,要想改變防守意識的薄弱,如果沒有教練的訓督與引導,光靠其自身是難以辦到的。潛意識裡的迷戀、畏難與惰性,會讓他尋找各種「有利」的理論來為自己開脫,因為「人們總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求印證已有的」。
本書特色:作者站在當代人的立場,由一枝毛筆出發,提出了關於「傳統」的三十六個問題,縱橫古今、跨越東西,打破美術與文、史、哲之藩籬,以縝密的思辨、鮮活的文字、豐富的案例、精美的圖片探討了「古法」、「古意」與當下文化潮流碰撞的現實意義,揭示了跨文化、跨領域的藝術史研究新路徑,可謂一幅波瀾壯闊的多角度文化長卷。
作者簡介:
何光銳,資深媒體人。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和理論研究,在多家藝術媒體撰寫評論專欄。
章節試閱
中國人為什麼拿一枝軟筆「為難」自己?
東漢蔡邕的書論《九勢》中,有這樣一句話──「筆軟則奇怪生焉。」
這真是一句「奇怪」的話。何謂「筆軟」?何謂「奇怪」?何以「筆軟」則「奇怪生焉」?針對它的真實含義,歷來聚訟紛紛,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如果書寫者筆力軟弱,則書寫過程中不能如意,筆下出現各種不合規範的醜怪線條和結構;第二種解釋與之相反,認為因毛筆富於彈性的特點,如果書寫者運用得法,就能產生變化多端、出人意表的精彩效果。
我們知道,釋讀古文,必須「原湯化原食」,把句子放到原文的整個語境中加以理解,而不能斷章取義。蔡邕的那段原話是這樣的:「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日,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唯筆軟則奇怪生焉。」細細咀嚼體會之後,就可以把第一種解釋排除。因為文中連續出現的「自然」、「陰陽」、「藏頭護尾」、「肌膚之麗」、「勢來」、「勢去」等詞語,環環相扣,都與毛筆富於彈性的特點,亦即「筆軟」直接相關。唯「筆軟」,方可「藏頭護尾」,方有「肌膚之麗」,方能「形勢出矣」、「奇怪生焉」。
實際上,這段文字包含了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一大奧妙。
世界各民族文字,在其肇端之際,多以契刻或硬物描畫為主。中國人後來發明出毛筆,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毛筆產生後的幾千年中,多少智者能人日日操弄使用,竟然沒有想到去推翻這位性格「柔軟」的「管城侯」,以一種更便利的工具取代之。只要拿過毛筆的都知道,這枝筆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是多麼的難以控制,筆毫一入紙,立即就失去「平衡」,不是太重就是太輕,快了不成慢了更不成,那種無所適從的尷尬,就像從未溜過冰的人被套上冰鞋推到了場地中央。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似乎自找麻煩,專門跟自己過不去。因為我們的先賢在原本相對勁挺的兔、狼毫筆之外,又增添了更軟更不易對付的羊毫筆,而且還要加長筆鋒。在紙張的應用上也是如此,從表面光滑硬朗的熟紙,演進到柔軟而易於滲化的生宣。他們的用意,無異於要「戴著鐐銬跳舞」。而深究其理,則可以明瞭為何只有中國發展出以文字書寫為形式的「純抽象」的書法藝術,以及中國畫何以形成「筆墨中心論」。
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一書中,曾經觸及這一問題,他說:中國之毛筆,具有傳達韻律變動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國的字體,學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卻用最奇特不整的筆姿組合起來,而以千變萬化的結構布置,留待書家自己去決定創造。
注重表達內在節奏韻律,抒發情性,呈現哲理,是所有中國傳統藝術的共同趣向。對於書法而言,正是這些「形而上」的需求,對工具材料提出了要求,這就是毛筆誕生的必然性所在。
換句玄虛點的話說,唯具「彈性」之物方能「載道」。
如若無法傳遞韻律,則無「流美」可言,更談不上展現情性與哲理,談不上「書為心畫」、「書如其人」了。因此,書法之所以成為一種生命化的藝術,成為「中國文化核心之核心」,毛筆的特殊性不容忽視。
「筆軟則奇怪生焉」,蔡邕所用的「奇怪」一詞,提示了書法線條在藝術表現上的豐富性──濃、淡、枯、潤、粗、細、剛、柔,穩與險、暢與澀、老與嫩、奇與正,張揚與蘊蓄、精微與渾茫、迅捷與雍容、雄壯與優雅、豪邁與謹嚴、灑脫與沉鬱……任何一門藝術,都建立在對複雜多重矛盾關係的駕馭調和上,藝術的高度與藝術的難度緊密相關。拿競技體育來打個比方:足球為什麼被公認為世界第一運動,讓無數人如痴似狂?正是由於這項運動以人體中最為笨拙的部位,接觸物體中最難以控制的球體,參加一種人數最多的集體角逐,因而最富起伏變化,最難以預測,最具偶然性和戲劇性。
「腳拙」、「球圓」、「人多」,於是,「奇怪生焉」。
就書法而論,由於毛筆的軟而難操,讓習書者不得不放下傲慢自我的心態,和逾級逾等的企圖,靜氣澄懷、日復一日地在筆墨紙三者間周旋對話,熟悉、體認、順應其性理,才有可能漸次向揮灑如意、心手相忘的「段位」靠攏。否則,即便有滿肚子的才思,也只能感嘆「眼中有神,腕下有鬼」了。在這個過程中,毛筆之「軟」,實際上對「意、必、固、我」的主觀偏執,躁急剛愎的人為之力,形成了一道阻擋、緩衝、化解的「沼澤地」。「筆力」提升之進階,伴隨著自我對自然的尊重與認識,「人」與「天」的相融與相應。此中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要義。
書畫之道「肇於自然」,而其至高境界,乃達於自然。
「古」是什麼?
書法要回歸「二王」,繪畫要直溯宋元,在藝術領域,許多人開始探究「古法」,追尋「古意」,一種崇古,乃至「復古」的風氣,出現已久。與此同時,不同的聲音,對「古」的質疑和抨擊,也變得更加尖銳起來。
我們身處一個很有意思的時代,在資訊氾濫、全球互聯的大背景下,伴隨著經濟崛起,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正在甦醒。一百多年前所謂的文化碰撞,其實質是在自卑心理下的自我否定、「全線潰退」與「去傳統化」。而今天,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碰撞來日方長。在這樣一個眾流交匯、視角多元、話語權爭奪激烈的當口,圍繞「古」的討論,成為一個前沿的話題,如何理解「古」、對待「古」,則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焦點。
那麼,「古」,究竟是什麼?
「古」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古」不是「昔」,不是「舊」。凡是「舊」的東西都一律曾經「新」過,但它是速朽的、被淘汰的。現代風格的家私可能很快過時,然而,我們看看明式傢俱,那些充滿靈性的剪影,那種簡約靜穆之美,至今仍不斷地給全世界的設計師們帶來創作的靈感。
「古」也不是某些具體的形式。陳丹青的《退步集續編》中有句話說得挺好:「……文藝復興繪畫的種種造型散韻似乎早已預告了現代義大利皮鞋與男裝,俊秀雅逸……」皮鞋跟繪畫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你會發現,由文藝復興大美學滋養陶冶的民族,於造型之美何其幹練而精明……」
實際上,關於「古」的種種誤解,都是將「古」做了實體化的理解,猶如刻舟求劍,企圖到前人遺跡和故紙堆中搜羅印證,把「古」當成既定、僵化、封閉的東西,進而要麼一味摹古,泥古不化,要麼竭力謗古,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古」。
有人考證出,東晉人寫字的姿勢是席地而坐、執卷而書,為了書寫流利,必須用手指有規律地來回轉動毛筆,所謂的「古法」就是轉筆的技巧和方法。問題是,今天我們已經有了桌子椅子,怎麼辦?還要不要這個「古法」?筆者常和一些書法家朋友討論,我們應該怎樣學習王羲之?是僅僅模仿他的用筆結體,還是學習他的境界識度、傳承態度和創新精神?假設生宣和羊毫在東晉時就出現了,王羲之會如何對付,是否會寫出另一種風味的書法?
齊白石說:「……其篆刻別有天趣勝人者,唯秦漢人。秦漢人有過人之處,全在不蠢,膽敢獨造,故能超越千古……」齊白石沒有執著於古人的樣式,他學習的是古人的「不蠢」。如今齊白石也成了古人,那麼,「古」安在哉?在乎秦豉漢瓦?在乎拍賣場上的齊氏篆刻?
「古」是活潑潑的,流動的,生生不息的。「古」是超越於時空與形式之上的,是傳統中例的、優秀的成分。「古」是文化的精神內核,是「道」之所存。
「古不乖時」,「與古為新」。「古」和「新」並非對立,真正的「古」總是常變常新的,真正的「新」總是暗合於古的。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的重要革新運動,都以「復古」為號召。竊以為,「復古」之「復」,不是「重複」,走回頭路,而應理解為「回復」,從偏途回到正道上來。
提倡復古,開一代風氣的趙孟頫主張「畫貴有古意」,其實主要是糾正南宋以來柔媚纖巧和剛猛率易兩種不良傾向,進而強調「中和之美」。在其啟發引領下,元代山水畫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峰。
韓愈發起唐代古文運動,他的名言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但他的「復古」並沒有襲取前人語調,而是「戛戛獨造」,「唯陳言之務去」,恢復古代散文清新簡練之傳統,一掃南北朝以來矯揉造作之時弊。宋人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日:「李唐群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如此看來,韓愈的文章,究竟是「古」還是「新」?
值得注意的,還有蘇軾評價韓愈的兩句話──「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有衰靡,有偏溺,而後有復古。
入古出新,借古開今,乃是一種因果關係。按照「現代化」學的新觀點,「現代」與「傳統」不能截然分立,「現代」只能從「傳統」中逐漸生出。
哲學家蘭德曼(Michael Landmann)說,「個體首先必須爬上他出於其中的文化高度。」對於書畫等中國傳統藝術來說,真正的困境在於,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今天的我們已經失去,甚至不再認識這個「高度」了。
充分進入傳統,重新認識傳統,掌握傳統的內在精神,當下的「復古」潮流若能以此為取向,則前景或許未可限量。
當然,重要的,是「不蠢」。
中國人為什麼拿一枝軟筆「為難」自己?
東漢蔡邕的書論《九勢》中,有這樣一句話──「筆軟則奇怪生焉。」
這真是一句「奇怪」的話。何謂「筆軟」?何謂「奇怪」?何以「筆軟」則「奇怪生焉」?針對它的真實含義,歷來聚訟紛紛,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如果書寫者筆力軟弱,則書寫過程中不能如意,筆下出現各種不合規範的醜怪線條和結構;第二種解釋與之相反,認為因毛筆富於彈性的特點,如果書寫者運用得法,就能產生變化多端、出人意表的精彩效果。
我們知道,釋讀古文,必須「原湯化原食」,把句子放到...
目錄
中國人為什麼拿一枝軟筆「為難」自己?
「古」是什麼?
倪雲林為何不可複製?
「程式」有罪?
黃賓虹到底可不可以學?
如何正確地玩「虛」?
畫有別才?
反者「藝」之動?
怎一個「鬆」字了得?
筆墨之「厚」為何物?
面具?面目?
「遠意」是怎樣實現的?
中國畫是一種「功夫畫」?
「繁」與「簡」,孰高下?
「有餘」乎,「不足」乎?
「必然」耶,「偶然」耶?
「變」,還是「不變」?
風格即弊端?
「骨法」是怎麼一回事?
如何用「辯證法」看藝術?
你是「劍宗」還是「氣宗」?
「敏感」自何處來?
裝傻充愣豈是「拙」?
能「微妙」乎?
不可沽名學「二王」?
「可持續美感」祕密何在?
「製作」與「寫意」能否相融?
真跡數行可名世?
「風雅」由誰說了算?
正門入,偏門人?
「技進乎道」還是「技退乎道」?
「淡」之一字談何易?
該不該有個「譜」?
藝術家為什麼要讀點書?
能否把傳統還給傳統?
「自癒」:中國文化的生命模式?
一枝毛筆的青春
中國人為什麼拿一枝軟筆「為難」自己?
「古」是什麼?
倪雲林為何不可複製?
「程式」有罪?
黃賓虹到底可不可以學?
如何正確地玩「虛」?
畫有別才?
反者「藝」之動?
怎一個「鬆」字了得?
筆墨之「厚」為何物?
面具?面目?
「遠意」是怎樣實現的?
中國畫是一種「功夫畫」?
「繁」與「簡」,孰高下?
「有餘」乎,「不足」乎?
「必然」耶,「偶然」耶?
「變」,還是「不變」?
風格即弊端?
「骨法」是怎麼一回事?
如何用「辯證法」看藝術?
你是「劍宗」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