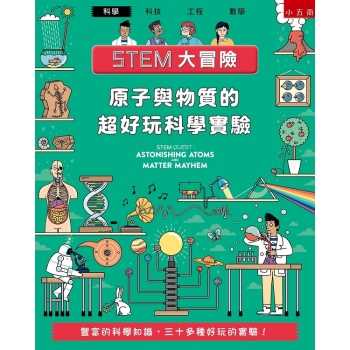上至官紳洋人,下至土匪暗娼,描寫平凡人的生存樣態
寫盡社會黑暗的現實主義小說,李劼人以文字反映時代
那兩枚烏黑眼珠,卻特別有光,特別玲瓏。
如今,則顧瞻起來,很是大膽,
敢於定睛看著你,一眼不眨,並且笑得也有力,
眼珠流動時,自然而有情趣。
寫盡社會黑暗的現實主義小說,李劼人以文字反映時代
那兩枚烏黑眼珠,卻特別有光,特別玲瓏。
如今,則顧瞻起來,很是大膽,
敢於定睛看著你,一眼不眨,並且笑得也有力,
眼珠流動時,自然而有情趣。
農家少女鄧⼳姑自小生在農村,卻夢想嫁入富裕的成都。因為家貧無法遂其所願,婚事延宕多年後,嫁給了成都郊外的興順號雜貨店掌櫃蔡興順。蔡興順憨傻忠厚,雜貨舖全靠表哥──哥老會的「袍哥」羅歪嘴罩著。豪爽仗義的羅歪嘴時常與他們往來,和潑辣美麗的鄧⼳姑眉來眼去,暗生情愫。
出了一趟遠門的羅歪嘴帶回妓女劉三金,天回鎮上也來了個來捐官的土糧戶顧天成。羅歪嘴使計和劉三金合謀坑顧天成的錢財,讓他賭輸、抵押田產,最後因為賴帳和爭風吃醋被毒打一頓,趕出天回鎮。劉三金無法求得羅歪嘴的長遠承諾,轉而撮合他和鄧⼳姑。兩人戀情在蔡興順面前也毫不遮掩,弄得小鎮人盡皆知。
顧天成返家後,經歷一連串妻子過世、女兒被人拐走、自己大病一場等衰運事件,最後靠著鄰居信洋教的鐘么嫂請來的洋醫生才痊癒。於是,他決心加入洋教,想藉此做官,向羅歪嘴復仇。在義和團攻打洋人使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時,信洋教的顧天成地位幾度翻轉,從遮遮掩掩到身價暴漲。因緣際會之下,他誣告羅歪嘴勾結義和團反洋人。四川總督因此前來砸毀興順號,逮捕蔡興順、打傷鄧⼳姑,羅歪嘴則提前出逃,不知所蹤。
為了打探羅歪嘴行蹤,顧天成找到回到父母家養傷的鄧⼳姑,卻對她心生愛慕,希望娶她為妻。為了丈夫和戀人的安全,也為了一直以來嚮往的富貴的生活,鄧⼳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展現生活樣貌¬】
唯妙唯肖地刻劃地方風俗民情、世態人情,寫活了四川文化,展現各個階層百姓的食衣住行生活樣貌,包括婚喪嫁娶、天回鎮的趕場、青羊宮的燈會、袍哥的規矩等等。
【角色刻劃鮮明】
人物眾多,形象活潑鮮明,情感奔放自由,人性複雜深邃。小說中沒有偉大的英雄,也不做過多的道德審判,而是詳實呈現在傳統的政治結構和倫理道德根基動搖之際,人們的矛盾心境和糾葛選擇。
【大量獨特方言】
小說大量使用川西方言和袍哥語言,展現地方語言的特色和魅力,也透過語言了解人物個性。
本書特色
本書是李劼人的長篇小說,描述甲午戰爭到簽訂《辛丑條約》這段時期,哥老會和洋教教民兩股勢力相互激盪、衝擊、消長,以及身在其中的市井小民的愛慾悲歡。在宛如死水般的傳統社會中,由於一個女人奮力抵抗道德和現實,讓死水泛起了一點點波動和微瀾。然而,微瀾卻又是隱隱的,展現大時代下人們掙而不脫的局限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