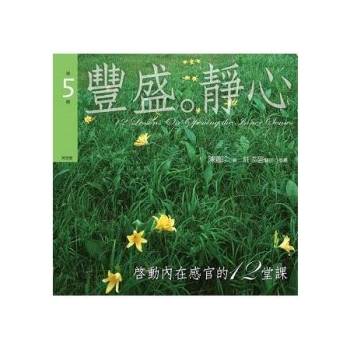兄妹、師生、同儕、親戚
各種身分的人們卻渴求相同的東西──愛
各種身分的人們卻渴求相同的東西──愛
▎究竟是出於愛,或是純粹的占有慾?
汽笛又鳴了一次,船室裡混亂起來。吉軒知道馨兒在熱望著和他握手,接吻;他怕她,遠遠的離開她。馨兒站在碼頭上望著「西安」慢慢的蠕動,她同時感著一種絕望。她的眼前是一片黑暗。「我所受的苦悶就是用情真摯者應得的報酬嗎?勝利是終歸於虛偽的戀愛者!」馨兒清醒時像發見了一條原理,不住的嘆息。
▎盲目的愛,老師與學生最禁忌的感情
我不該人工的改削我自然的戀愛以求適合於現代社會的規則的!年齡之差算得什麼?有婦之夫亦不見得絕對無受處女的愛的權力!師母的母女的將來的思慮也是阻我向先生進行戀愛的一原因。及今想來自己真愚不可及!受名義支配著的戀愛不成其為純正的戀愛,因生活的保障而發生的戀愛,也不是純正的戀愛。純正的戀愛是盲目的,一直進行不顧忌其他的一切障礙的。
▎尊嚴與生活,究竟要如何選擇
我雖然心裡不情願聽,但好奇心要逼著我站著聽。原來春英早就回來了的!我愈想愈覺得春英可憐。她是不情願到我們家裡來的!她很失望的就是住在這胡同裡的職業還不能維持她母子的生活!她不得已才到我家裡來!我還對她為禮儀上的形式上的苛責,我真是殘忍極了的人!「你看她對她的兒子如何的負責任!你把你自己和她比較看看!」悲楚和羞愧交逼著我,禁不住眼淚直流的了。
本書特色
本書收錄「現代言情小說開山祖師爺」張資平的短篇小說七篇:〈性的屈服者〉、〈晒禾灘畔的月夜〉、〈不平衡的偶力〉、〈約伯之淚〉、〈蔻拉梭〉、〈末日的受審判者〉、〈三七晚上〉。它們秉持著張資平作品一貫的文學及藝術性,說了一些戀愛,講了一些生活,說了很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