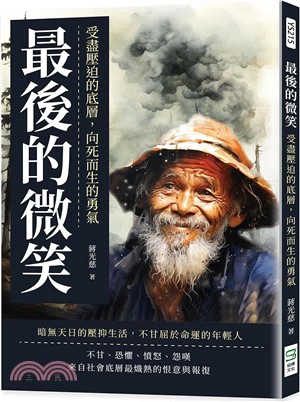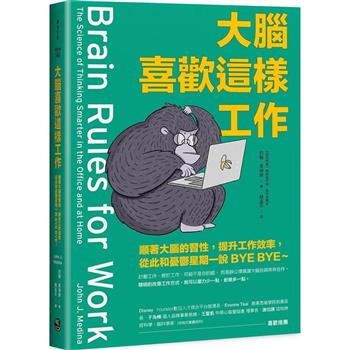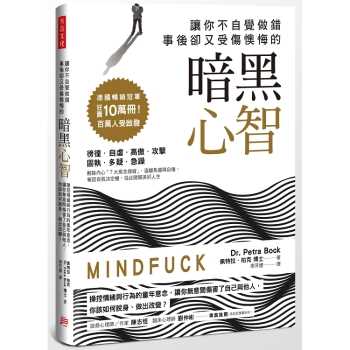暗無天日的壓抑生活
不甘屈於命運的年輕人
不甘、恐懼、憤怒、怨嘆
來自社會底層最熾熱的恨意與報復
不甘屈於命運的年輕人
不甘、恐懼、憤怒、怨嘆
來自社會底層最熾熱的恨意與報復
▎螻蟻雖小,尚且奮力一搏,生而為人,卻毫無尊嚴
他低著頭似乎在思想什麼,但他這時並沒有明白地思想到什麼。他看見地上有幾個螞蟻往來:一隻黃色的小螞蟻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尋得了一塊白模樣的食物,在用力地銜著前走的當兒,忽然遇到了一隻黑色的螞蟻,這黑色的螞蟻見著小螞蟻銜著一塊食物,便上前將它搶奪下來。小螞蟻大為憤怒,便不相讓,與黑色的螞蟻廝殺起來。小螞蟻雖然是小些,然而卻英勇異常,毫不懼怕,倒也敵得過牠的敵人。牠倆越廝殺得越有勁,阿貴這時不禁看得出神;而且向小螞蟻表示著充分的同情。他見著小螞蟻這種英勇的氣概,不禁暗暗地稱讚不置。他看著看著,忽然他的腦海中起了一層波浪,他即刻立起身來,自己向自己驚異地問道:「啊哈!我難道連這一個小螞蟻都不如嗎?喂!我還配做一個人嗎?小螞蟻被牠的同類所欺侮了,還要拚命地抵抗一下;我是一個人,難道受人欺侮了,就這樣地乖乖地算了嗎?報仇呵!……報仇!……」
▎世道不公,無奈鋌而走險
「倘若我被捉去槍斃了,」阿貴又繼續想道,「也不知他倆將要怎麼辦呵。周全福死了,還有他的賢良的老婆養活他的母親;如果我死了的時候,那我的父母將靠著誰養活呢?……」阿貴暗殺張金魁的決心,至此時不禁動搖了一下。他的爸爸和媽媽的一雙可憐的形象,縈回於他的腦際,並覺著他倆已經如同在自己的面前站著,表現著可憐的衰老的面容,射著哀求的眼光。阿貴有點茫然了:怎麼辦呢?照著自己的決定去做好呢,還是為著這兩位可憐的老人的原故,打消自己的念頭好呢?……阿貴躊躇了幾分鐘,最後還是將牙齒一緊,下了最後的決心:「我也問不了這許多!世界上的苦人多著呢,反正我也問不了這許多!阿貴!你照著原來的決定做去罷!」
▎窮人的悲歌,不甘與憤怒
「阿貴,你曉得嗎?在這個社會裡,窮人家的女子總是要被富人侮辱的,你看你的小妹妹現在是什麼樣子……」沈玉芳說至此時,將手往右邊一指,意思是叫阿貴順著她所指的方向往去。阿貴順從她的意思,便向原來的隔座望一望,見著老頭子與小姑娘還在那裡調戲著玩呢。過了一忽,靠在老頭子懷裡的小姑娘將臉轉過來,筆直地將眼光射到阿貴的身上來。阿貴起初還不十分驚異,後來慢慢地覺著她的面孔與阿蓉的相似,一等阿貴一覺到這個時,說也奇怪,他便越看她越像自己的小妹妹,這兩隻圓圓的小眼睛,這兩個圓圓的小笑窩,這一個如櫻桃也似的小口,這一切……這簡直是阿蓉,這簡直是阿貴的小妹妹了。「這難道真是我的小妹妹嗎?……」
本書特色
蔣光慈致力於普羅小說創作,他的作品多以革命鬥爭為背景,青年知識分子及農工階層為對象,寫盡當時青年們面對大環境的壓迫及悲憤而奮起挺身的精神。本書故事由主角日常的一事件觸發,用現實、幻境、夢境的交疊,帶出主角所遭遇的掙扎情緒與心境變化,走在善惡之間的抉擇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