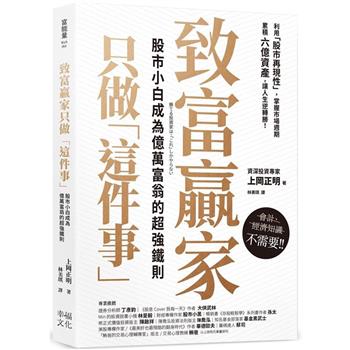自序
在鄉村和城市的時光縫隙中奔走
《流年》和《村逝》是我近幾年中短篇小說的兩部選集,《流年》關於城市,《村逝》立足鄉村,兩部小說集沒有多大關聯,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母親。假如你拿到《流年》,又恰對它感興趣的話,不妨再找來《村逝》看看,反之亦然。
當編完這兩本書時,我驚訝地發現,《流年》中首篇〈流年〉是寫年輕公務員從縣城到城市的歷程,尾篇《遍地太陽》卻是中年下崗職工從城市到農村的步履,而《村逝》中的〈村逝〉則是表達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已經一步步消失。這與我的生活奇怪地合拍。年輕的時候,羨慕城市裡的生活,好多年都在努力進城;中年的時候終於到了城市,卻時不時懷念鄉村,每逢節假日急急忙忙訂車票,返回老家探望父親、兄弟,以及一大幫還在那塊土地上生活的親人和朋友,但鄉村已經不是我生活過的鄉村。
這麼多年,身體和文字一直奔走在鄉村與城市的時光縫隙之間。
大學畢業後那幾年,我在滹沱河畔的村子裡當老師。
還是2003年,一冬天沒有下雪,立春之後卻下了一大場。雪從頭天下午紛紛揚揚下起,晚上也沒有停,第二天早上5點多起床去學校上早自習,發覺外面白茫茫的,比平時亮。推著自行車出了門,雪有半腿深,巷子裡沒有人影,也沒有任何人和動物活動過的痕跡,只有白。我有些自怨自艾,想這麼早誰會騎著自行車出門?忽然聽到一對新婚農民夫婦的聲音,婦人滿足後發出銳利的叫聲,在寂靜的早晨特別響亮。它像寺廟裡的暮鼓一樣,我眼前許多的門關上了;然而也像晨鐘一樣,同時推開一扇窗戶。我知道自己選擇的路和別人不一樣。
2008年到2011年,我在離家鄉不到100公里的市裡借調,為了好好表現,早日調過去,每個星期五趕最後一趟大巴回家。有幾個星期五連續有事情,每次忙完急匆匆趕往汽車站時,最後一班車已經走了。這時妻子經常打電話過來,問我坐上車沒有,我回答沒車了,電話那頭4歲的女兒就哇地哭了。每個星期一早上,5點多起床,要趕最早的大巴去市裡上班。孩子從前一天晚上就緊緊摟住我的手臂。到了早上,我輕輕撥開她暖呼呼的手臂,往汽車站趕。冬日的早晨,寒風呼嘯,人們都還在夢鄉中,路上只能見到清潔工在昏黃的路燈下掃馬路。新年之前,妻子騙女兒我要早一天回來,女兒一整天等著,晚上我還沒有回去,她又哭了。很晚我才回了家,女兒帶著淚睡著了,手心裡握著幼兒園給她發的一顆糖和幾瓣橘子。第二年,有一位朋友也借調到市裡,他有一輛車,拉上我兩人結伴走。我們車輪一樣旋轉,每週至少熬一個通宵加班,卻調不過去,周圍一些因為有關係的人一個一個調了進來,兩人都特別有情緒。有個星期一早上從家裡出來之後,兩人在路上邊走邊罵,車走了好久都沒有到市裡,看路標,原來光顧生氣,到了高速路出口居然沒有注意,超過去了。我們兩人商量著,乾脆別去上班了,直接開上車到省城去,找另一位朋友。但結果卻是到了下一個高速路出口返回上班的路。這多像小說呀!然而裡面的現實是生活,想像才是小說。後來我以這段經歷為背景,寫了許多篇小說,〈流年〉和〈薩達姆被抓住了嗎〉就是其中兩篇。
2011年9月,我終於調到了省城,家安頓住之後,路上跑得少了,每逢節假日回老家,基本選擇坐綠皮火車。
公里的路程,需要坐4個多小時,途經每一個村落的小站都要停。在這列車上,車廂裡一般人都很多,許多人經常連坐票也買不到,多見的是沿線村落裡的農民、帶著尼龍袋子進貨的小商販、行李放在油漆桶中的打工小夥子、眉毛做得又粗又直的鄉下姑娘、穿著校服戴著眼鏡的學生、拿著裝病歷袋子的老人……這些人大多講著各自的方言俚語,生活經歷也各自不同,坐在他們中間,我彷彿回到了從前。
中秋節回老家後,回城時為了避免擁擠,我買好了提前一天走的火車票。沒想到那天那麼多人趕車。我在候車室遇到了一位兒時的夥伴,他拖著一個很大的行李箱,打算去我所在的城市趕廟會。這位朋友性子火暴,從小愛打架,還坐過幾年牢。從牢裡出來之後,就開始做套圈圈的生意。我不知道他碩大的行李箱裡裝的是毛絨玩具,還是石膏雕塑,或者是些菸酒之類的玩意兒。和他同行的是他老婆。
我們有一句沒一句閒聊著,我知道他沒有買上坐票。快要檢票的時候,又來了位我們村坐火車的人,這位朋友馬上讓他老婆回去,說來的這個人可以幫他把行李箱弄上火車。我們兩個待的這段時間,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說過一句要我幫忙的話,我還一直以為他老婆要和他一起走。我告訴他上了火車可以和我一起擠擠,我們一家三口買了三張票。朋友說,你坐你的去吧,我和你現在說不到一起。
在城市裡,出行我一般步走或坐公車。坐公車有時免不了跑幾步趕車,但是每當看到身體臃腫的中年男女奔跑著,追趕即將離站的公車,心裡就有些淡淡的悲傷,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影子。一次讀關於梁漱溟的文章,裡面寫到這麼一段故事。伍庸伯走了20多里路趕火車,快到車站時火車已到站,本來跑步能夠趕上,可是伍庸伯繼續保持原來不疾不徐的速度,等他到了車站,火車開走了,他又步行20多里路返回去。讀到這裡,我頓時覺得公車是可以不追趕的,但自己卻沒有那份定力,遇到車要走時,還是追趕。
最為遺憾的是,這麼些年一直沒有大塊兒的創作時間,本職工作和寫作無關,甚至還干擾得很厲害。也遇到過幾位領導告誡我不要寫小說了,好好幹本職工作。寫起小說來,偷偷摸摸,急急忙忙,既怕被周圍的人發現,也唯恐被什麼事情打斷。這麼些年,寫的大多是短篇,即使這樣,也是經常有了好的想法卻沒有時間實施,或者寫了一半,狀態正好時,卻不得不去忙活什麼事情。常常想起卡夫卡《獵人格拉胡斯》中的一段話:「我一直在運動著。每當我使出最大的勁來,眼看快爬到頂點,天國的大門已向我閃閃發光時,我又在我那破舊的船上甦醒過來,發現自己仍舊在世上某一條荒涼的河流上。」但是生活中有無數我這樣的人,每天忙得死去活來,就像赫拉巴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談道:「在波爾迪鋼鐵廠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理解別人,才能理解自己。跟我在一起幹活兒的還有其他人,他們的命運比我更加艱難,然而他們卻一聲不吭。」無數次比較卡夫卡和喬伊斯,他們的性格截然不同,但都站到了文學的巔峰之上。我沒有能力,也不是那種能使自己與世俗生活完全割裂開的性格,便唯有勤奮些。記得借調的時候經常加班寫材料,有時半夜兩點鐘才睡,早上五點半鬧鐘響起來的時候困得要命,心裡告誡自己,什麼也沒有還想偷懶,便趕緊爬起來,用涼水抹把臉,開始寫小說。有段時間大概太累,早上起來枕頭上經常有鼻血。每個週末回了家,也是伏在電腦上寫東西,很少陪家裡人。有一天女兒說:「爸爸,我希望你回來後家裡就停電。」我問為什麼,女兒回答:「那樣你就不寫東西了,能陪我玩。」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用生命寫作,卻特別理解那些為了寫作拋棄一切的人,哪怕他們早早離開人世,但只要留下足夠好的作品,已經足夠了。對於一個人,他們真正活過。
幸運的是,這麼多年一步步走過來,理解支持我寫作的老師和朋友越來越多,他們像光一樣,摸不著,但無處不在。我在堅持寫短篇小說的同時,寫的中篇小說也多起來,不知不覺發表了130多篇。其中大多數作品創作時信心滿滿,寫完之後得意揚揚,覺得自己完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可是過不了多長時間,就開始懷疑、惶恐起來,便想趕緊再寫下一篇證明自己。在我懷疑自己的時候,這些可敬的老師和朋友們給予了我非常多的肯定,使我這塊稱不上璞玉的頑石從一堆石頭裡顯示出來,變得越來越有了些亮光。
其中一位我非常信賴的朋友,他的眼光十分好,在好多公眾場合給過我無私的褒獎。私下裡聊天,談到我小說存在的問題時,他覺得我的小說經常不朝一個方向努力,把力量削弱了,希望我能嘗試去寫些一竿子扎到底的小說。我對他的意見非常重視,常常想怎樣寫出這樣一篇小說。2015年月底,我讀到了A·雅莫林斯基的《契訶夫評傳》,他裡面有段話這樣評論契訶夫:「最有特色的小說缺乏純粹的敘事方面的興趣,有的小說沒頭沒尾,有的小說有一種靜止的性質,故事進行得慢,跟舞步一樣。那些小說不但不朝一個固定的結局活動,往往溜出正軌,或者故事還沒到高潮就逐步退下來。不過它們還是能夠用驚人的方法抓緊讀者的想像力。正因為不要捏造,不布疑陣,不耍聰明,原本鬆弛的地方並不故意拉緊,原本粗糙的地方也不故意削平,故事的進行適可而止的緣故,那些小說具有使讀者身臨其境的力量。」我大為興奮,我的那些「缺點」契訶夫都有,他所達到的那種自然,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而那時我差不多已經認為契訶夫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大師。文章還有一段話也頗適合我:「出身卑微,從小經人教誨,尊敬權勢,服從權力,感覺自己渺小,怎樣把奴隸的血從自己身上一點一滴地擠出去。」怎樣把奴隸的血從自己身上一點一滴地擠出去,正努力在做。
生活還在繼續,寫作也在繼續,引用契訶夫獲得「普希金文學獎」之後給朋友的信裡的一段話作為這段文字的結尾:「我的文學活動還沒有真正開始,不過是個學徒罷了,或者連學徒也不如,得從頭做起、從頭學習才行。要是今後花40年的工夫看書用功,那麼學成之後或許會朝讀者發出一個砲彈去,弄得天空也震動。」
是為序。
楊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