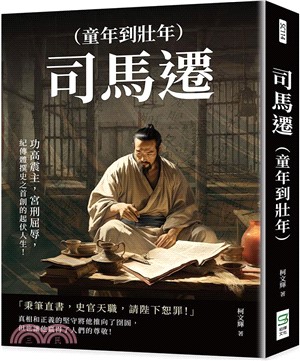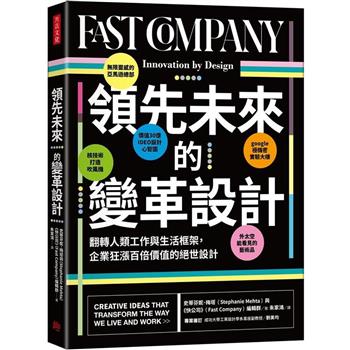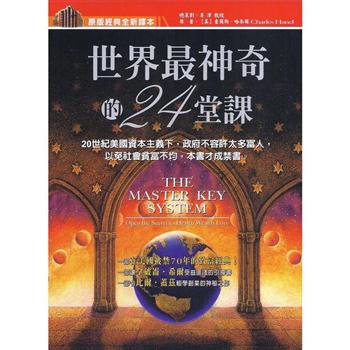「秉筆直書,史官天職,請陛下恕罪!」
真相和正義的堅守將他推向了囹圄,
但也讓他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真相和正義的堅守將他推向了囹圄,
但也讓他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功高震主──司馬遷的天才,地上不容!
《太史公書》就其識、才、情而言,可以傳誦萬載而長新。但一個朝代只能有一個人垂之不朽,那就是囊括山河勛業彪炳又有許多疏狂之處的當今漢家天子,輪不上大文豪大史學家司馬遷。……歷史有時候便是一連串遺憾的總和,畏首畏尾不是偉丈夫!故而《太史公書》必須立即焚燬,只因為此書太博大,博大到地不能載,天不能容。只有我如日之升似月之恆的大漢朝才能出這位太史公,他是史學王國執牛耳的霸主。不,簡直是一位皇帝。
■亦福亦禍──司馬遷幼年聰慧,但未必是好事!
孺子尚小,唱起民謠,鸚鵡學舌,何曾解意?然情真氣旺,又太聰明,好表露愛憎,未必能立足於朝廷!當今萬歲,喜聞頌辭,行屍走肉,靠唯唯諾諾可以束帶立於朝,祿享公卿。我平生最恨八面玲瓏的人,有時希望遷兒長大能圓融保身,有時又為這類念頭而羞赧。做人難哪,不讀書則不明事理;讀了書又無用武之地,反換得一串串煩惱,是無路之路呀!
■仗義執言──司馬遷的正義,使其身陷囹圄!
臣與李陵多年罕遇,平素無杯酒之歡。然觀其為人,事親孝順,臨財廉潔,從不苟取。與朝中同僚相處極講信譽,對部下視若弟侄,解衣推食,身先箭矢,志在殉朝廷之急,被長輩視為可教之才,朝野推為國士。身陷絕境,登高一呼,傷病者奮起,矢盡道窮,殺得敵人橫屍上萬。他平日少應酬,每次戰報來朝,大人們舉觴為陛下稱壽,都講古之任何名將不過如此。言猶在耳,今為一官一人一家計,對敗將降將說盡惡行,與昔日所讚頌者判若兩人,令臣不解。李陵降匈奴,將來能否立功而歸,不宜早做斷語。
本書特色
本書分為上、下二卷,作者以生動的筆觸描寫出史學家司馬遷的一生。包含司馬遷的童年時期、與父母關係、結婚對象、相知好友,以及在人生路上所遇見的人事物,甚至是下獄受刑的心境,帶領大家感受這位完成曠世巨作《史記》的天才所經歷之苦難與一切,無論是對歷史感興趣還是尋求深刻故事的愛好者,皆能在本書中獲得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