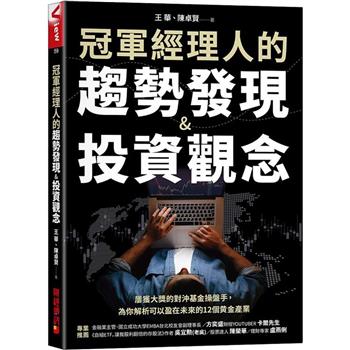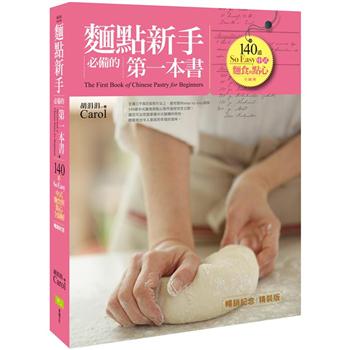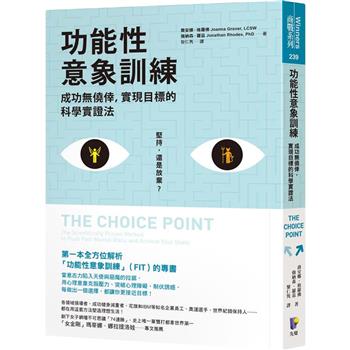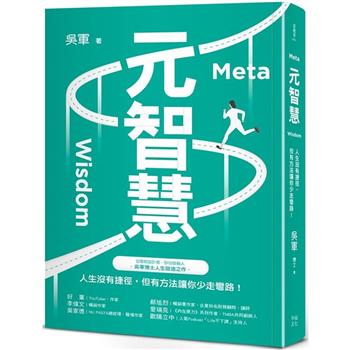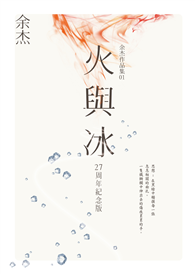愛情,向來是快速成道的方式。
直探靈魂深處的「愛與恐懼」。
///
每個人都在尋找靈魂伴侶,
但真相是:「自始至終我是完整的,
我不是值得被愛,而是已經被愛。」
17萬人追蹤、華文靈性療癒作家高瑞希
高瑞希以最誠實的文字,
深刻地,扎實且疼痛的去明白,直探靈魂深處的「愛與恐懼」。
///
每個人都在尋找靈魂伴侶,
但真相是:「自始至終我是完整的,
我不是值得被愛,而是已經被愛。」
那男人說:「我只能給妳無條件的愛,但就是不能愛妳。」他是不婚主義者,也是一個不會有專一關係的人。
經歷過各種情感關係的失敗,涵蓋被騙成為第三者,或無故消失的前男友、冷暴力的前男友、遇衝突會裝沒事打哈哈的前男友……如今她終於遇到一個能好好面對情緒、照顧自己跟照顧他人的男性,一切都完美無比。
唯獨不能一對一。
————我發現自己是不斷在生長的大樹,日日拔高,開散枝枒,可是整個樹幹是空心的,我不知道是什麼在推著我前進。
————我想要「真正的接納自己」,不是一下接納,一下又討厭自己。
▋在不被愛的情境裡,進行一場自愛的修練
他說:「自愛是一個人發自內心覺得自己很特別,若因此被擺在一個次等的位置,也不會在意。」
她說:「自愛是你要重視自己現在的需求。」
同一個字彙,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
經歷了整整一年的反覆、探索、清空之後,內在聲音無預期地在極度放鬆下,悄然浮現……
╔═════════════╗
自愛,是選擇愛自己的方式。
這是交給自己定義的。
╚═════════════╝
▋歷經恐懼和自我懷疑,終於找到靈魂伴侶
真實,是軟弱與慾望的集合體。當我們願意以行動撬開它,必會迎來一股釋放,心會出現難以言喻的擴張感,美也瞬間誕生。
————原來我一直在尋覓的靈魂伴侶,早就在了。
————我早就被愛,我從未失去任何。我被我的靈魂深深愛著。
【原來,愛是……】
每個人都喜歡講顯化,卻不知道顯化的都是慾望,所以始終無法滿足,始終活在匱乏裡。真實的愛、滿足跟快樂,是我們在不抱期待的付出時就會知道,我們早就都顯化我們有的東西。會呼吸的人用不著顯化空氣,就只是呼吸而已。
【原來,恐懼在……】
我知道,我要發自內心承擔他們怎麼想我。我必須一一解開那些束縛我的未來預言,還有過去。我首先要做的,是不能逃避。
恐懼和愛,始終纏纏綿綿,即便你今生今世都活在恐懼裡,倘若你沒有因為恐懼停下腳步,它終將帶你找到愛,看見輝煌。
親身穿越了一趟恐懼之旅,高瑞希終於了解——「任何人,只能對自己的靈魂有交代。」
讀者好評推薦
「我一直因自己有太多紛雜的情緒想法交參而卑微,謝謝瑞希梳理得這麼清楚,如此真誠,讓我可以擁抱這份美麗。」
「妳是勇敢的靈魂,願意扒開來寫出自己的故事。」
「每個人都會有盲點,希望自己如妳一般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