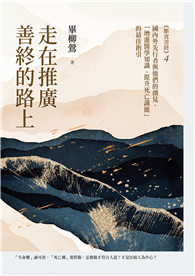名人推薦:
蔣亞妮(作家)——專文推薦
吳妮民(醫師╱作家)、吳曉樂(作家)、李蘋芬(詩人)、陳雪(小說家)、崔舜華(作家)——好評推薦
《滿花》裡的女性與所有女性,不結果,也是花,有些否定,成就了肯定。——蔣亞妮(作家)
對女性來說,從初經伊始,「合宜地生養」,就一直是個困擾(或自擾);彷彿要到停經的那天,世界才會對我們罷手。
人生很難,生人也很難。
時代往低婚育率邁進,代理孕母正要修法,而世界會否稍稍寬容鬆動?林文心的《滿花》,以冷調、精確、俐落的文字,對生育及身體提出奇情的幻想、現實的模擬,勾連出五篇精巧好看的作品。——吳妮民(醫師╱作家)
林文心對女性身體的不厭其煩,對我來說簡直就是「愛」的同義複詞。這個意志,從《遊樂場所》到《滿花》都未有轉移。中國作家盛可以於《子宮》一書說道:子宮像重軛卡在女性的脖子上。《滿花》裡,重軛形化成更輕盈、更自然而然的厄運,充盈於空氣之間(以至於無從抵禦)——瓜熟了,就沒有蒂的事了。又有誰錯呢。——吳曉樂(作家)
植物萌芽、生長與凋萎,有人知曉它的一生就這樣安靜行進。它不知道養花人因為感覺到愛,而幸運的(苟且的)不再搖搖欲墜。
林文心的小說把身體攤開來,向內拗折,擠出一件長得有點像誰的事物(是孩子嗎?還是自身的鬼魂);向外離心旋轉,使世界顛倒、使它暈眩,在新生的肉上面留下齒痕,與後來的自己相認。
——李蘋芬(詩人)
媒體推薦:
沒結果的花
蔣亞妮(作家)
多年來,我經常在閱讀中與許多一流的小說相逢,長久積累,成為了厚厚一沓書單,卻在每次與人分享的時刻,才忽然警醒地發現,那幾經心秤反覆查驗才說出口的每一本故事與作者,常常滿是女性的名字。至今,每一次公開談到「女性」一詞,依然會緊張到冒汗,當我試圖從各種課堂理論、人生經驗中理解性別,並對伴隨著性別的各種危險,自捏大腿提醒小心時,都代表著我無法忽視自己也是一個女性。
因此我無法不關注女性,不管她們是女孩、少女、女人或者其他的集合體,也不管她們說著什麼樣的故事,展現了什麼形態的身體,我都無法移開目光,就像讀林文心的小說,無法不切膚感受。從林文心的第一本小說《遊樂場所》離開,轉身走進《滿花》,過往暴力卻透著別樣抒情的筆,被她寫乾了墨水,一寫到底,發現原來身體才是真正的場所,青春期的堡壘已然熟成。林文心在《滿花》裡,以女性為絕對座標,勇敢地揭開她為女生、寫女身、發女聲——如此純粹與強大的企圖。
血胎一體,她把身體切得更開,張得更大,說到底女性的身體最終都會被拿來問出那道終極提問:「妳要生小孩嗎?」如同多年前Iris Marion Young 在她的名作《像女孩那樣丟球》中所提出的種種思考,幾乎所有的小女孩都被在童年被交付了玩娃娃這樣的「任務」,而不是在球場玩球,女性的身體有其天職,天職顯然並不設定在球場(也不在許多地方)。因此,當女性開始跨越界線,多半會在為男孩制定的遊戲規則下,遭受不公平的待遇,這讓女性的身體滿是各種無法想像的記號,被劃滿了黃線、紅線與雙黃線,《滿花》就是林文心決意從違停變作超速與無照駕駛的犯規。
如今我們已有花樣繁複的哲學論述與各類故事,聚焦向身體,更多時候,身體的意涵仍是寬廣於身體之外的,身體流出的血汙、身體與它的使用者、身體姿勢再到身體穿戴的美好事物……一如上個世紀朱天文作《世紀末的華麗》那般:「不事情節,專寫衣裳」(王德威語),女性慢慢地書寫著一件衣服又一件衣服,以及種種讓我們褪下衣服的人事後,終於從衣服寫回肉身,真正的身體,得由血肉構成。在《滿花》的5+1則故事裡頭,滿是女性的身體,身體裡頭還有身體,子宮裡頭收納著成熟與飽滿的卵子,有些等待誕生、有些已通過產道降生為人,有些則錯過了適孕年齡。然而與生育有關的不一定總是誕生,也可能如同小說裡頭,導向了各種求子、無子、失子……不同情狀、不同疑問。
林文心以活生生的身體(lived body)直球對決,生與不生,都是《滿花》的提問,並且就是問問,無人有責任作答。我想起電影《芭比》,開篇如創世紀般的短片裡頭,一群小女孩玩著扮家家酒的遊戲,初時她們手上只能拿著奶瓶、廚具以及仿真嬰兒,直到擁有完美身材與衣飾的「芭比」降生,小女孩們丟開家與兒,擁抱了自己真正喜歡的身體。《滿花》做得比這更好也更多,像是進一步質疑著,為什麼我們還是得玩洋娃娃?
這五篇小說中的每個女性,也全都選擇先跳過「妳要生小孩嗎?」這道題目,試圖問出更核心、更有邏輯的問題,像是:為什麼要生?為什麼是我來生?為什麼母親非得愛著自己的小孩?於是〈長生萬物〉裡的母親,那個身為「旭哥的妻子」、「咪咪的母親」、沒有名姓的「她」,坦白告訴了我們:「如果身為一位好母親的必要條件是樂於成為母親,她想自己並不符合資格。」並且在「咪咪」從嬰兒成長為孩童、再成少女後,「她仍然沒有愛上咪咪,世上仍然沒人知道這個秘密。」小說中的每一個女性成為母親後,或開始思考變成母親的模樣後,就沒有任何一次誕生是純然的喜悅。《滿花》的開篇〈扎根向下〉,召喚出了一個總被忽視卻永恆存在的母親原型,透過嬰兒視角描寫出了她的樣貌:「母親是一個不快樂的人。她的哀傷就像這一天之中被鎖定的每一件事,無法改變。」不快樂也並不專屬於母親,就連〈沃土〉中,那對不斷輪流灌溉、偷偷觀察,甚至較量著彼此身體誰更合適生育,誰又更合適做瑜珈的女性伴侶間,依然沒有誰的身體比較甘願,比較快樂。因為女性的身體裡面不只有身體,還有秘密,以及比秘密更神秘的賀爾蒙、催產素,包含了科學與神秘學,自成了一組天圓地方,內建宇宙,重瓣之花(flore pleno)。
相對於女性,男性寫者們更熱衷談論生死二元、存在幻滅的宏觀哲學論述,長時以來,他們像是紀錄片般,在大片疆土中尋找景深,男性心智也更常被視為代表理性思考的主體。林文心的《滿花》也很貼切地在此刻,為現代女性說出真心話:「我本無意宏觀。」如後記所言,這本書的初始,像是一時情動:「若說前五篇是站在分歧之處上思考生育,那我私心想將附錄一篇視為一切的前身,那既是關於時間與生長、關於選擇與被選擇、關於自我指認,當然也關於女性如我,究竟是如何走到種種問題之前。」感受永遠比思考先抵達,不知何故,卻經常落得比思考更滯後。
《滿花》帶我們回到一切之前,看看那些屬於她、屬於我,也屬於妳的感受,當我讀到林文心悄然在後記藏進更多問題時,縱然知道問題不必回答,還是想要低聲偷偷回應,(我會讓自己的孩子吃鹹酥雞當晚餐)。請允許我借用《滿花》暗藏的文法句型,「為什麼不行?」它是問句,也是肯定句。
換個句式,再來一次,《滿花》裡的女性與所有女性,不結果,也是花,有些否定,成就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