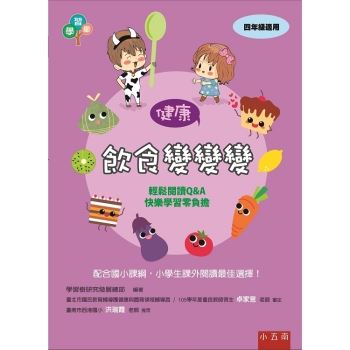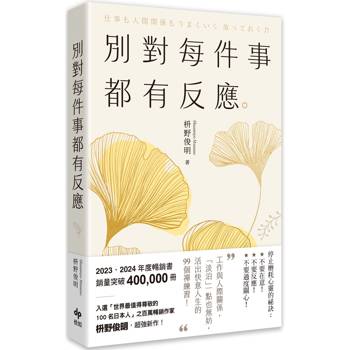1
豔紅
豔紅的裙子
福馬林液體裡僅有的鮮明
恍如隔世的午後
濃重的霧靄裡
一重一重剝離的情欲
那些溫煦的等待中的鳶尾花
裝裱在試管的囚籠裡
纖細的腰肢
和瘦削的手指試圖抓住的
濃鬱的情愛
蒼白的帶著細小顆粒感的肌膚
碎裂和背信的苦楚留下
豔紅色的烙印
吸吮著靈魂的無眠的凌晨
踟躕不前
穢褻的骯髒的死亡著的乖戾
曉霧逐漸濃重的暮光裡
虛情假意地哀悼
豔紅色的長裙
2
統計數字
孤獨感被操縱
獨立的個體被掐頭去尾
扁平均一地
凌遲成計畫中的圖景
少數派的四面楚歌
荒謬地在龐大的數字裡
找到歸屬性的膠著
另一些更加龐大的數字
覬覦著僅存的空氣
它們忖度形單影隻者的靈魂
殺伐開始的時候
慘烈的不只有湮滅的瞬間
還有妄加掩飾的嫉妒
無法成為對方的
便要在統計數字裡消失
遙遠的地方
或者近在咫尺
眼中的光芒熄滅在纏繞的盔甲裡
目光交錯的瞬間
終於了然
曾經帶給自己溫暖的
是親手剝離的他人的盔甲
3
紅與黑
紅色的雙層巴士
紅色的摩天輪
紅色的霓虹燈
紅色的單肩包
在亂離、動盪、
寧靜又渺遠的
黑色裡浮現
消失
閃耀
冷卻
彼此視而不見
紅色在沒有光的地方
沉默
變成黑色
黑色跳動著
掙扎著
像曾經的紅
以上內容節錄自《春日遲》凜之◎著.白象文化出版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6263640542.pdf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春日遲的圖書 |
 |
春日遲 作者:凜之 出版社: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7-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6 |
中文書 |
$ 176 |
小說 |
$ 18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春日遲
詩是一種自我為鏡的回憶,這回憶是對未來的虛構
◎這些詩,寫於十九到二十三歲,生活在兩座城市的雙重性孤獨的間隙。
◎寫詩的無用與私語態令我著迷,可能也只是,女人錯失雨季的自圓其說。
◎書寫作為一種與本我的對談和對時間迅即流逝的對抗,成為唯一可以擊破窒息感的石器。
對月獨酌時的絮語亦如春日遲遲,
暖陽當頭,霍地起了縠皺。
都市裡的浮囂在隔了山海的層樓之上,
也自有一種天真可愛。
從寒冬而來的遺落了起點的悄然沉寂著的歲月
遲遲的春日的熏紫的暮靄
跋涉過凜與暗的無涯的碎石路
我們在這樣的列車上相逢
我們要去往何方 晦暗的光影的未央
異樣靈敏的聽覺只餘下孤注一擲的逼狹的慰藉
泡影一般相擁的暖意
無數個此去經年
無數個春日遲遲
◎代理經銷:白象文化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6263640542.pdf
作者簡介:
凜之
北京人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學士
香港大學建築研一
業餘寫詩畫畫
作品散見於《聲韻》
喜歡思考發呆的拖延症晚期intp
章節試閱
1
豔紅
豔紅的裙子
福馬林液體裡僅有的鮮明
恍如隔世的午後
濃重的霧靄裡
一重一重剝離的情欲
那些溫煦的等待中的鳶尾花
裝裱在試管的囚籠裡
纖細的腰肢
和瘦削的手指試圖抓住的
濃鬱的情愛
蒼白的帶著細小顆粒感的肌膚
碎裂和背信的苦楚留下
豔紅色的烙印
吸吮著靈魂的無眠的凌晨
踟躕不前
穢褻的骯髒的死亡著的乖戾
曉霧逐漸濃重的暮光裡
虛情假意地哀悼
豔紅色的長裙
2
統計數字
孤獨感被操縱
獨立的個體被掐頭去尾
扁平均一地
凌遲成計畫中的圖景
少數派的四面楚歌
荒謬地在龐大的數字裡
找到歸...
豔紅
豔紅的裙子
福馬林液體裡僅有的鮮明
恍如隔世的午後
濃重的霧靄裡
一重一重剝離的情欲
那些溫煦的等待中的鳶尾花
裝裱在試管的囚籠裡
纖細的腰肢
和瘦削的手指試圖抓住的
濃鬱的情愛
蒼白的帶著細小顆粒感的肌膚
碎裂和背信的苦楚留下
豔紅色的烙印
吸吮著靈魂的無眠的凌晨
踟躕不前
穢褻的骯髒的死亡著的乖戾
曉霧逐漸濃重的暮光裡
虛情假意地哀悼
豔紅色的長裙
2
統計數字
孤獨感被操縱
獨立的個體被掐頭去尾
扁平均一地
凌遲成計畫中的圖景
少數派的四面楚歌
荒謬地在龐大的數字裡
找到歸...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豔紅
統計數字
紅與黑
頭髮
初雪
不告而別
米原
桃紅起泡酒
默
6766
老舊未來
冬季
自圓其說
等雨
錯失雨季
女人
虛幻的信仰
葡萄抑或是明天
秋色在白色木椅裡漸深
義無反顧
她
科尼亞轉舞
春日遲
復仇
只有背影的中年男子
古城
初夏的教堂
破碎
如何
如果
男人和女人
夏蟲語冰
閣樓
緩慢
恰到好處
Ferrara
異鄉人
自我之敵
細雪
從來
二十六歲的時候
愛
我們
夢不適合多於三層
跋
統計數字
紅與黑
頭髮
初雪
不告而別
米原
桃紅起泡酒
默
6766
老舊未來
冬季
自圓其說
等雨
錯失雨季
女人
虛幻的信仰
葡萄抑或是明天
秋色在白色木椅裡漸深
義無反顧
她
科尼亞轉舞
春日遲
復仇
只有背影的中年男子
古城
初夏的教堂
破碎
如何
如果
男人和女人
夏蟲語冰
閣樓
緩慢
恰到好處
Ferrara
異鄉人
自我之敵
細雪
從來
二十六歲的時候
愛
我們
夢不適合多於三層
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