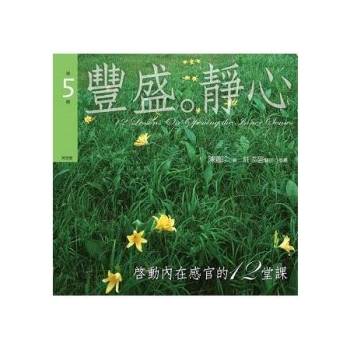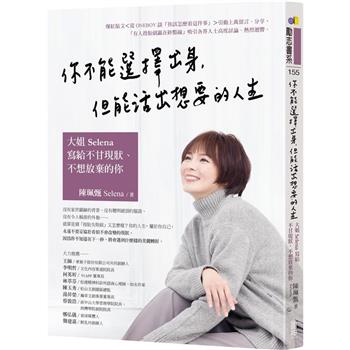五、方广夺嫡
佛在菩提树下悟道,证得“三明”——发现无我与报果的真相——缘起,以此统一自由、良序两端——兼总成立世间流转与清净出离,一时独步五天。鹿苑首度说法,直至垂般涅槃,四十五年循循善诱,始终孜孜不倦。教法异常鲜明,可谓一以贯之:以根本般若——缘起原理、法印实相、四谛大纲为中心,撷取前人经验,改造而成三学、八正道、六度等诸行法,应机施设,令教学效果极大化。此间,除了基础逻辑架构(缘起无我),多是对于传统文化成果的继承、扬弃与总结;不仅是集大成者,还有质的飞跃——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堪称古印度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既然其来有自,佛教便不是真空圣坛上的标本,其产生和发展必然会与时空背景紧密关联。默雷说:“一个学说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之重要并不亚于这个学说的内容本身。(《宗教改革的政治后果》)”是故,唯有纵览全局,才能精准把握佛教思想发展脉搏,领略最真实的佛教及其处境。本篇通过对印度宗教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简述佛教超越传统、方广超越部派脱颖而出的始末因缘。
早在佛教诞生前数世纪,古印度文化发展已然进入“轴心期”。婆罗门与治权合作,积极建立良序;利用“教说天启”、“梵化种姓”、“教职至上”、“神力决定”、“祭祀万能”、“灵魂不灭”诸说,垄断一切特权乃至社会资源,成为“哲人王”。这一文化理念与制度建设经过长期试验,逐渐走向成熟;由于顺应了时代、人心、治事之需,成为后续数千年来南亚次大陆上主流思想的骨干(犹吾伦的儒家)。然而,这一理念与模式基于“神本逻辑”,存在重大缺陷;譬如循环论证等,令既得利益趋于极端。由过度剥削的现实,引起被统阶级的反弹——总有人不愿意接受“命运”安排,便会反思其设计的合理性(乃至存在本身)。在当时,流民本就不少,汇聚成势;随着理想性的开发,有了理论依据,开始具备引动潮流的力能。他们模仿老年婆罗门的修道模式——主动脱离社会组织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专志于冥想并履践各种理念。依循梵志的修验成果——“奥义书”,别有新的追求——探索出离之道。既然价值另立,那么基于旧文化的一切上层建筑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人被称作沙门,成为反抗传统教权与文化垄断的中坚力量。同时,作为时代反题,也推动着位居主流的吠陀文化、婆罗门教、奥义书思想更往印度教发展阶段演进。
从神权理念到沙门思想,其内涵有着深刻变化,尤其是针对“梵”的诠释。吠陀文化注重神力,此时的“神”——“梵”几乎就是人格——“梵天”;作为“第一因”,必须积极取悦,否则将会失去“再生”权利(形同精神枷锁)。祭司口衔天宪,突显族群差异,俨然人间代言。婆罗门教将“神”推往形上,目的是与社会现实捆绑,让制度设计变得天经地义(类似董氏“天人”理念)。此时的“梵”仍具人格,但已有了高于一般神祇的超越性;作为最高意义的存在,与之“同在”成为全新目的。在此阶段,教界讨论的重心放在组织良序,尚无兴趣开发“宇宙本源”、“存在形态”等课题。随着文化积淀,“梵”被抬高至“位格”——成为无形的最高价值(“大梵”),由此带来沙门崛起的契机。与婆罗门教相比,“奥义书”更重履践;而且宽宥形下,令种姓差异弭平在理论上变得可行。既然“梵”在形上——超脱世俗,与之“合一”成为修道终极目标(此前“梵”具人格,世人追求“与梵同在”,类似神教的“永息主怀”)。有情不断轮转,灵魂生死不灭;唯有与“梵”契合,方能脱离苦海。形上之“梵”、形下之“我”居然可以“合一”;何以实现?两者关系?是一是异?这些课题成为时代显学。
沙门接棒梵志的修道理念与模式,继而更进一步:既然最高价值才是吾辈追求,“大梵”不外乎“至理”,则臻于至理即可;于是,舍弃现象世间各种美好(继而摒弃一切存在有的价值),清净出离、轮回止息成为唯一旨趣。由此“否定”形下之神祇,认为业报——法则才是主宰,神不过是世间有情里的一环;在绝对清净的标准面前,神与众生无异(在色界看来,欲界高低无非福德体现)。神亦在凡尘(三界)中,则无法赐予解脱乃至相关智慧;所以,拯救不能赖他,只能是靠自己。至此,人类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命运起伏不再仰赖神意、人间也不再是神国的对照;由于间接摆脱了附属地位,让人获得从未有过的尊严(从“神本”理念到“人本”倾向,人格乍立)。
再来看现实面。劳苦大众财力有限,供养婆罗门需要“黄金”,而沙门仅需少量餐食,自然更易亲近。且他们的学说——“免生死、尽轮回”,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隐隐然还压过神教一头,自然更叫人期待。这一选择无疑符合人性,尤其是不被神职高看一眼的低种姓者,纷纷“箪食壶浆”(遑论原住民本就没有“来世期许”)。沙门取得社会认可,又有稳定资源支持,吸引更多人士加盟,包括锐意探寻终极真理的社会精英。他们基于“灵魂逻辑”,摆脱“神定理念”,提出各种理论与方法(以各种“因力”代替“神力”),并各自抱团实践;彼此争鸣不已,一时异说纷纭。神与神国不再可靠,无异跌落神坛;如此针锋相对——“三大纲领”岌岌可危,婆罗门教有了劲敌。这一历史时期,东方由刹帝利治权主导的国度迅速发展起来;他们赞助新兴思想,与西方教权体制社会互成犄角之势。
在热切出世的慕道者中,就有后来成就佛果、建立佛教的释迦族王储乔达摩‧悉达多。怹本出身贵胄,复入沙门阵营;特殊的社经地位与文化素养,令其得以针对既有学说展开全面批判。释尊博采众长、触类旁通,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的本质——正反二题两大根本诉求——维持良序与解脱缠缚,由于立场不同所致水火不容、相持不下。因为前无古人,只能摸索行进;利用现有工具综合判断,果然发现端倪。经充分继承、普遍扬弃、杰出架构、积极辟新,借鉴并改造传统戒定技法,开创全新慧观之道。
在瑜伽状态中,检视有为世间,发现一切生命现象皆为“识现”——经验。(此处并不涉及“外客观存在”,不能说有说无!)继而辨析“存在”:无非心、色二法——具有质碍现象(有体积与相状)的物质性法和与之相对的非物质性法。蕴、处、界等诸法和合聚集,迅速生灭(无常)、不受控制(无我)——“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待缘而生、缘尽则灭”,完全不由人力与神祇所左右。由此可知:诸行因缘生,刹那即败谢;意志不能移,恒尔如实谛。
这就怪了:“神”、“梵”有无可以暂且不论,“我”是怎么来的?继而剖析“心流”。“大脑”本能地串联起此前各种经历——将诸多生命现象之体验汇总,并据时间顺序编排记忆;如此混合之印象(仍是经验),乃安立“我”的“观念”——“我见”。长期第一视角所致“本位”惯习,出于不能忍可的逼迫性,为“我见”安立“我体”,才是事实真相——“我”的本质;并无阿特曼、灵魂、命根、神识等实体存在,一切无非“无明”——随顺误会而已。故说:如是二无我,真实且可验;由非理抗拒,坚执而苦剧。
“事与愿违”——主观不明乃至逃避——不达实相的“无明”与不离我执之“爱染”,是为苦恼不住之源本、轮转不息的正因。于是,同样依据缘起法则,唯有端正态度,切实修验,亲见真谛、破除无明、接受事实,方能解决问题——不再被假相所囚困,不再怀有不实幻想,熄灭三毒烦恼,杜绝一切非理执着与追求,以至不生不灭的寂静,也即生死永断、恼苦永尽的涅槃。乃云:世间因缘灭,出离诸漏有;具足三达者,无明尽死尽。
“天上天下无如佛”,可谓独领风骚。三点道理。第一、佛教拥有全新逻辑架构——缘起无我(中正之道),对于传统文化全面而彻底地批判(针对基于灵魂逻辑,自由、良序两种倾向所导致的两极),意味着已然成功“脱嵌”。第二、涅槃绝非一类特殊形态的“永生”,故得突破“我”与“梵”的局限;基于不同原理,实现伟大成就,达到全新高度。第三、目标是解脱,工具是智慧,两者只能由己证得,绝不仰赖祭职口中的神意;至此,人类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超越三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实现人格独立。由此三点,佛与佛教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爱敬与拥戴,成为文化明星。
以上內容節錄自《自由与良序——佛教初学廿一讲》天佑 法师◎著.白象文化出版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6263645189.pdf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自由与良序——佛教初学廿一讲的圖書 |
 |
自由与良序——佛教初学廿一讲 作者:天佑法师 出版社: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自由与良序——佛教初学廿一讲
通过本书,领略最真实的佛教。
◎充分把握时空环境、文化背景,全面介绍佛教义理、历史沿革。
◎基于般若,正本清源;宗奉人间佛教理念,以期实现理性信仰。
◎绝无含糊其辞、故弄玄虚,行文深入浅出,让更多人结下胜缘。
这是一本系统介绍佛教的入门读物。通过对古印度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的解读,争取管窥佛教产生的真实缘由;并且凭藉义理诠释,发掘佛教超越外学的关键所在。暨在全面检讨传统文化发展局限的过程中,发见佛教的独到处、殊胜义、闪光点,乃至最终成为时代之选的肯綮。全书共有三个章节,分别绍介孕育佛教的时空环境与文化传统、佛教产生发展流布的始末梗概、佛教初基义理演绎及其历史沿革,以此探讨佛教从何而生、因何兴衰、以何为胜三大主题。阅读本书,可以领略最真实的佛教。
◎代理經銷:白象文化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6263645189.pdf
作者簡介:
天佑法師
早年师从著名佛教学者唐仲容先生。后于成一长老、弘法和上座下圆顶。长期从事佛教思想发展史与弥勒文化的研究工作。著有《自由与良序——佛教初学廿一讲》、《弥勒文化研究》、《瑜伽菩萨戒知行集》、《印顺导师弥勒文钞选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记》、《弥勒大成佛经讲记》、《八名普密陀罗尼经讲记》等。
章節試閱
五、方广夺嫡
佛在菩提树下悟道,证得“三明”——发现无我与报果的真相——缘起,以此统一自由、良序两端——兼总成立世间流转与清净出离,一时独步五天。鹿苑首度说法,直至垂般涅槃,四十五年循循善诱,始终孜孜不倦。教法异常鲜明,可谓一以贯之:以根本般若——缘起原理、法印实相、四谛大纲为中心,撷取前人经验,改造而成三学、八正道、六度等诸行法,应机施设,令教学效果极大化。此间,除了基础逻辑架构(缘起无我),多是对于传统文化成果的继承、扬弃与总结;不仅是集大成者,还有质的飞跃——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堪称古印度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既然其来有自,佛教便不是真空圣坛上的标本,...
佛在菩提树下悟道,证得“三明”——发现无我与报果的真相——缘起,以此统一自由、良序两端——兼总成立世间流转与清净出离,一时独步五天。鹿苑首度说法,直至垂般涅槃,四十五年循循善诱,始终孜孜不倦。教法异常鲜明,可谓一以贯之:以根本般若——缘起原理、法印实相、四谛大纲为中心,撷取前人经验,改造而成三学、八正道、六度等诸行法,应机施设,令教学效果极大化。此间,除了基础逻辑架构(缘起无我),多是对于传统文化成果的继承、扬弃与总结;不仅是集大成者,还有质的飞跃——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堪称古印度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既然其来有自,佛教便不是真空圣坛上的标本,...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长期以来都有一个误区,以为佛教超然独立,仿佛“天降”一般,与时代及其文化背景毫无关联。这种看法无异神话,显然违背缘起法则。这既不利于正本清源——探究佛教真谛,又有阻断佛教命脉——令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隐忧。笔者认为,想要认清一个事物,必要寻根溯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通过梳理文献,利用现代文化工具,力图管窥佛教最真实的面貌。
目錄
前言
第一节 其来有自
一、人性所需
二、地理因缘
三、雅利安人
四、印度神教
五、沙门思潮
六、身份问题
七、因果异说
第二节 领略三宝
一、释尊正传
二、念佛四端
三、上首弟子
四、随念之法
五、经典结集
六、部派分蘖
七、理念分化
第三节 义理初基
一、根本要义
二、一以贯之
三、学处知津
四、定慧等持
五、方广夺嫡
六、大乘课纲
七、净土方便
杂文附
觉悟宣言
佛教四端
缘起理观
无我刍谈
撂干货——研习佛教有得
谈谈信与不信
佛教徒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
刍议人间佛教
如果做好人做好事没有好报
素食文化与佛教饮食观
护生之辨
佛教的本质是认识论
关...
第一节 其来有自
一、人性所需
二、地理因缘
三、雅利安人
四、印度神教
五、沙门思潮
六、身份问题
七、因果异说
第二节 领略三宝
一、释尊正传
二、念佛四端
三、上首弟子
四、随念之法
五、经典结集
六、部派分蘖
七、理念分化
第三节 义理初基
一、根本要义
二、一以贯之
三、学处知津
四、定慧等持
五、方广夺嫡
六、大乘课纲
七、净土方便
杂文附
觉悟宣言
佛教四端
缘起理观
无我刍谈
撂干货——研习佛教有得
谈谈信与不信
佛教徒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
刍议人间佛教
如果做好人做好事没有好报
素食文化与佛教饮食观
护生之辨
佛教的本质是认识论
关...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