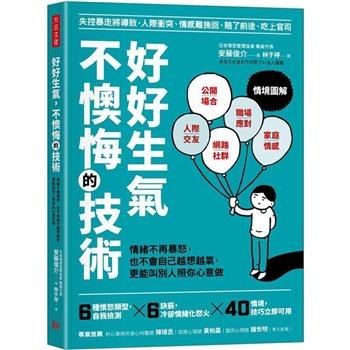本書是繼《國語文學史》之後,胡適又一文學史的力作。
白話文學史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若去掉白話文學史,就只是「古文傳統史」罷了。
「古文傳統史」是模仿的、死的文學史;「白話文學史」是創造的、活的文學史。因此,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
白話文學不是近幾年幾個人憑空捏造出來,而是經過一千幾百年歷史進化的產兒,否則絕不可能在短短時間內變成一種全國的白話文運動(即新文學運動),引起那麼多人的響應與共鳴。
因為1800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寫書了;1000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寫詩詞了;7、800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寫小說了;600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
本書特色:
1.本書雖名為《白話文學史》,實是中國文學史,且是中國文學史最中心的部分。除此之外,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熱鬧、最富創造性、最代表時代的文學史。
2.「白話文學」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說話的作品。「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臺上說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
3.書中每討論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定舉出相對應的作品為例。所以本書不僅是文學史,還是中國文學名著選本。
作者簡介:
胡適
字適之,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其曾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在文學、哲學、史學等許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戴東原的哲學》、《白話文學史》、《盧山遊記》、《胡適文選》、《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四十自述》、《南遊雜憶》、《胡適留學日記》、《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民主、科學,提倡懷疑主義。也提倡白話文和新詩,致力推翻兩千多年的文言文。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1962年病逝,中央研究院於院內成立了胡適紀念館。在研究院附近另有一胡適公園,為胡適的墓地。
章節試閱
第一篇──唐以前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了。戰國時,各地方言很不統一。孟軻說: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書中又提及「南蠻鴃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韓非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可見當時各地的方言很不相同。方言不同而當時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見文字與語言已不能不分開了。
戰國時文體與語體已分開,故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有「同文書」的必要。《史記》記始皇事屢提及「同書文字」(《琅琊石刻》)、「同文書」(〈李斯傳〉)、「車同軌,書同文字」(〈始皇本紀〉)。後人往往以為秦「同文書」不過是字體上的改變。但我們看當時的情勢,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當日「書同文」必不止於字體上的改變,必是想用一種文字作為統一的文字;因為要做到這一步,故字體的變簡也是一種必要。
《史記》描寫人物時,往往保留一、兩句方言,例如漢高祖與陳涉的鄉人所說。《史記》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當時的文字。當時疆域日廣,方言自然也更多。我們翻開揚雄的《方言》,便可想見當日方言的差異。例如《方言》的第三節云:
娥,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妦。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
「通語」二字屢見於《方言》全書中,通語即是當時比較最普通的話。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二節:
敦,豐,厖, ,憮,般,嘏,奕,戎,京,奘,將,大也。凡物之大貌曰豐。厖,深之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或曰憮。宋魯陳衛之間謂之嘏,或曰戎。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為之作釋也。
此可見統一之後,有許多方言上的怪癖之點漸漸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這種語言上的統一,究竟只限於一小部分,故揚雄當漢成帝時常常拿著一管筆、四尺布去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訪問他們各地的異語,做成十五卷《方言》。
當時的方言既如此不統一,「國語統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當時的政府只能用「文言」來做全國交通的媒介。漢武帝時,公孫弘做丞相,奏曰: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
——《史記》、《漢書‧儒林傳》參用
可見當時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這可見古文在那個時候已成了一種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種政策,叫各郡縣挑選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師,讀書一年,畢業之後,補「文學掌故」缺(也見〈儒林傳〉)。之後又把這些「文學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國的「卒史」與「屬」。當時太學,武帝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經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資格是「先用誦多者」。這樣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識傳播到各地了。從此以後,政府都只消照樣提倡,各地方的人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讀古書,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爾雅」的古文。
這個方法—後來時時加上修改,總名叫做科舉—真是保存古文的絕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個命令,定一種科舉的標準,四方的人自然會開學堂,自然會把子弟送去讀古書,做科舉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費一個錢的學校經費,就可以使全國少年的心思精力都歸到這一條路上去。漢武帝到現在,足足的二千年,古體文的勢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元朝把科舉停了近八十年,白話的文學就開始蓬蓬勃勃地的興起來了;科舉回來了,古文的勢力也回來了。直到現在,科舉廢了十幾年了,國語文學的運動方才起來。科舉若不廢止,國語的運動絕不能這樣容易勝利。這是我從二千年的歷史裡得來的一個保存古文的祕訣。
科舉的政策把古文保存了二千年,這固然是國語文學的大不幸。但我們平心而論,這件事也未嘗沒有絕大好處。中國的民族自從秦漢以來,土地漸漸擴大,吸收了無數的民族。中國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鮮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滿洲,在南方征服了無數小民族,從江浙直到湖廣,從湖廣直到雲貴。這個開化的事業,不但遍於中國本部,還推廣到高麗、日本、安南等國。這個極偉大開化事業,足足費了兩千年。在這兩千年之中,中國民族拿來開化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國的古文明。而傳播這個古文明的工具,在當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們可以說,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國民族教育自己子孫的工具,還做了二千年中國民族教育無數亞洲民族的工具。
這件事業的偉大,在世界史上沒有別的比例。只有希臘羅馬的古文化,靠著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費了一千年的工夫,開化北歐的無數野蠻民族,只有這一件事可以說是有同等的偉大。這兩件事—中國古文明開化亞東,與歐洲古文明開化歐洲—是世界史上兩件無比的大事。但是有一個大不同之點,歐洲各民族從中古時代爬出來的時候,雖然還用拉丁文做公用的文字,但是不久義大利就有國語的文學了;不久法國、英國、西班牙、德國也有國語的文學了,不久北歐、東歐各國也都有國語的文學了;拉丁文從此「作古」了。何以中國古文的勢力能支持二千年之久?何以中國的國語文學到今日方才成為有意的運動呢?
我想,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第一,歐洲各種新民族從那開化時代爬出來的時候,那神聖羅馬帝國早已支不住了,早已無有能力統一全歐了,故歐洲分為許多獨立小國,故各國的國語文學能自由發展。但中國自從漢以後,分裂的時候很短,統一的時間極長,故沒有一種方言能有採用作國語的機會。第二,歐洲人不曾發明科舉的政策。況且沒有統一的帝國,統一的科舉政策也不能實行。拉丁文沒有科舉的維持,故死的早。中國的古文有科舉的維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權威。
中國自元朝統一南北後,六百多年不再分裂:況且科舉的制度自明太祖以來,五百多年不曾停止。在這個絕對的權威之下,應該不會有國語文學發生了。做白話文學的人,不但不能拿白話文來應考求功名,有時還不敢叫人知道他曾做過白話的作品。故《水滸》、《金瓶梅》等書的作者至今無人知道。白話文學既不能求實利,又不能得虛名,而無數的白話文學作家只因為實在忍不住那文學的衝動,只因為實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寧可犧牲功名富貴,寧可犧牲一時的榮譽,勤勤懇懇地替中國創作了許多的國語文學作品。政府的權力、科第的引誘、文人的毀譽,都壓不住這一點國語文學的衝動。這不是國語文學史上最純潔、最光榮的一段歷史嗎?
還有一層,中國的統一帝國與科舉制度維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勢力,使國語的文學遲至今日方能正式成立,這件事於國語本身的進化也有一種間接的好影響。因為國語經過二千年的自由進化,不曾受文人學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寫定與規定,故國語的文法越變越簡易,越變越方便,就成了一種全世界最簡易、最有理的文法。(參看《胡適文存》卷三,《國語文法概論》)古人說:「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這四個字來恭賀我們的國語了!
第一篇──唐以前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了。戰國時,各地方言很不統一。孟軻說: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書中又提及「南蠻鴃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韓非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可見當時各地的方言很不相同。方言不同而當時文字上的交...
作者序
自序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要我去講國語文學史。我在八星期之內編了十五篇講義,約有八萬字,有石印的本子,其子目如下:
第一講 我為什麼要講國語文學史呢?
第二講 古文是何時死的?
第三講 第一期
(一)—─漢朝的平民文學
第四講 第一期
(二)—─三國六朝
第五講 第一期
(三)—─唐上
第六講 第一期
(三)—─唐中
第七講 第一期
(三)—─唐下
第八講 第一期
(四)—─五代十國的詞
第九講 第一期
(五)—─北宋(1)文與詩
第十講 第一期
(五)—─北宋(2)宋詞
第十一講 第一期的白話散文
第十二講 總論第二期的白話文學
第十三講 第二期上之一(1)南宋的詩
第十四講 第二期上之一(2)南宋的詞
第十五講 第二期上之一(3)南宋的白話文
後來國語講習所畢業了,我的講義也就停止了。次年(一九二二)三月二十三日,我到天津南開學校去講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想要修改我的《國語文學史》稿本。那晚上便把原來的講義刪去一部分,歸併作三篇,總目如下:
第一講 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
第二講 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第三講 兩宋的白話文學
我的日記上說:
......原書分兩期的計畫,至此一齊打破。原書分北宋歸上期,南宋歸下期,尤無理。禪宗白話文的發現,與宋《京本小說》的發現,是我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但這個改革還不能使我滿意。次日(三月二十四日)我在旅館裡又擬了一個大計畫,定出《國語文學史》的新綱目如下:
一、引論
二、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話文學—《國風》
三、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是白話的嗎
四、漢魏六朝的民間文學
1.古文學的死期
2.漢代的民間文學
3.三國六朝的平民文學
五、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1.初唐到盛唐
2.中唐的詩
3.中唐的古文與白話散文
4.晚唐的詩與白話散文
5.晚唐五代的詞
六、兩宋的白話文學
1.宋初的文學略論
2.北宋詩
3.南宋的白話詩
4.北宋的白話詞
5.南宋的白話詞
6.白話語錄
7.白話小說
七、金元的白話文學
1.總論
2.曲一 小令
3.曲二 弦索套數
4.曲三 戲劇
5.小說
八、明代的白話文學
1.文學的復古
2.白話小說的成人時期
九、清代的白話文學
1.古文學的末路
2.小說上清室盛時
3.小說下清室末年
十、國語文學的運動
這個計畫很可以代表我當時對於白話文學史的見解。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自然是加上漢以前的一段,從《國風》說起。
但這個修改計畫後來竟沒有工夫實行。不久我就辦《努力》週報了;一年之後,我又病了。重作《國語文學史》的志願遂一擱六、七年,中間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二年)暑假中我在南開大學講過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刪改本,共分三篇,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講。同年十二月,教育部開第四屆國語講習所,我又講了一次,即用南開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種油印本。這個本子就是後來北京翻印的《國語文學史》的底本。
我的朋友黎劭西先生在北京師範等處講國語文學史時,曾把我的改訂本增補一點,印作臨時的講義。我的學生在別處當教員的,也有翻印這部講義作教本的。有許多朋友常常勸我把這部書編完付印,我也有這個志願,但我始終不能騰出工夫來做這件事。
去年(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春間,我在外國收到家信,說北京文化學社把我的《國語文學史》講義排印出版了,有疑古玄同先生的題字,有黎劭西先生的長序。當時我很奇怪,便有信去問劭西。後來我回到上海,收著劭西的回信,始知文化學社是他的學生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開辦的,他們翻印此書不過是用作同學們的參考講義,並且說明以一千部為限。他們既不是為牟利起見,我也不便責備他們。不過拿這種見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備、匆匆趕成的草稿出來問世,實在叫我十分難為情。我為自贖這種罪過起見,遂決心修改這部書。
恰巧那時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創立新月書店。我雖然只有一百塊錢的股本,卻也不好意思不盡一點股東的義務,於是我答應他們把這部文學史修改出來,給他們出版。
這書的初稿作於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中間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幾十斤鹽,頭髮也多白了幾十莖,見解也應該有點進境了。這六年之中,國內國外添了不少的文學史料。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寫本的俗文學,經羅振玉先生、王國維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許多篇可以供我們的採用了。我前年(一九二六)在巴黎、倫敦也收了一些俗文學的史料,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中國俗文學的史料。唐人小說《遊仙窟》在日本流傳甚久,向來不曾得中國學者的注意,近年如魯迅先生、如英國韋來(Waley)先生都看重這部書。羅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經詩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寶貴的了。近年鹽谷溫博士在內閣文庫及官內省圖書寮裡發見了《全相平話》、吳昌齡的《西遊記》,明人的小說多種,都給我們添了不少史料。此外的其他發見還不少,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國內學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寶貴的結果。《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雜劇與小說,不但給我們添了重要史料,還讓我們知道這些書在當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總集《太平樂府》與《陽春白雪》的流通也是近年的事。《白雪遺音》雖不知落在誰家,但鄭振鐸先生的《白雪遺音選》也夠使我們高興了。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近十年內,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收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在這一方面,常惠、白啟明、鍾敬文、顧頡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這些歌謠的出現使我們知道真正平民文學的樣子。—以上種種,都是近年國內新添的絕大一批極重要的材料。
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這些新史料作根據,我的文學史自然不能不澈底修改一遍。新出的證據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後的文學變遷大勢,並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文學逐漸演變的線索。六年前的許多假設,有些現在已得著新證據了,有些現在須大大地改動了。如六年前我說寒山的詩應該是晚唐的產品,但敦煌出現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懷疑了。懷疑便引我去尋找新證據,寒山的時代竟因此得著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國語文學史》初稿裡斷定唐朝一代的詩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敦煌的新史料給我添了無數佐證,同時卻又使我知道白話化的趨勢比我六年前所懸想的還更早幾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卻不料隋唐之際已有了白話詩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剛見著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說》時還很詫異,卻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說了!六年前那些自以為大膽驚人的假設,現在看來,竟是過於膽小,過於持重的見解了。
這麼一來,我就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原稿十五講之中,第一講(本書的「前言」)是早已刪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國語文學史》無此一章)現在卻完全恢復了;第二講稍有刪改,也保留了;第三講與第四講(北京印本的第二、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從漢初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頁,不滿二萬五千字;在新改本裡卻占了近五百頁,約二十一萬字,增加至九倍之多。我本想把上卷寫到唐末五代才結束的,現在已寫了五百頁,沒有法子,只好把唐代一代分作兩編,上編偏重韻文,下編從古文運動說起,側重散文方面的演變。依這樣的規模做下去,這部書大概有七十萬字至一百萬字,何時完功,誰也不敢預料。前兩個月,我有信給疑古玄同先生,說了一句戲言道:「且把上卷結束付印,留待十年後再續下去。」「十年」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舊例,卻不料玄同先生來信提出「嚴重抗議」,他說的讓我不好意思引在這裡,但我可以附帶聲明一句:這部文學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內繼續編成的。
現在要說明這部書的體例。
第一,這書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我在本書的「前言」裡曾說: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於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但我不能不用那傳統的死文學來做比較,故這部書時時討論到古文學的歷史,叫人知道某種白話文學產生時有什麼傳統文學當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得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說話的作品。我從前曾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依這三個標準,我認定《史記》、《漢書》裡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於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二者—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這樣寬大的範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學了。
第三,我這部文學史裡,每討論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定要舉出這人或這派的作品作為例子。故這部書不但是文學史,還可算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選本。文學史的著作者絕不可假定讀者手頭案上總堆著無數名家的專集或總集。西洋的文學史家也往往不肯多舉例;單說某人的某一篇詩是如何如何;所以這種文學史上只看見許多人名、詩題、書名,正同舊式朝代史上堆著無數人名、年號一樣。這種抽象的文學史是沒有趣味,也沒有多大實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書不曾從《三百篇》做起。這是因為我去年從外國回來,手上沒有書籍,不敢做這一段很難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將來能補作一篇古代文學史,即作為這本書的「前編」。我的朋友陸侃如先生和馮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學史》。他們的見地與功力都是很適宜於做這種工作的,我盼望他們的書能早日出來,好補我的書的缺陷。
此外,這本書裡有許多見解是我個人的見地,雖然是辛苦得來的居多,卻也難保沒有錯誤。例如我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又如說建安文學的主要事業在於製作樂府歌辭,又如說故事詩起來的時代,又如說佛教文學發生影響之晚與「唱導」、「梵唄」方法的重要,又如說白話詩的四種來源,又如王梵志與寒山的考證、李杜的優劣論、天寶大亂後文學的特別色彩說,盧仝、張籍的特別注重......,這些見解,我很期盼讀者特別注意,並且很誠懇地盼望他們批評指教。
在客中寫二十萬字的書,隨寫隨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書剛排好時,我又發見新證據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後,加個後記,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後記一節。有時候,發現太遲了,書已印好,只有在正誤表裡加上改正。如第十一章裡,我曾說:「後唐無保大年號,五代時也沒有一個年號有十一年之長的;保大乃遼時年號,當宋宣和三年至六年。」當時我檢查陳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曆》,只見一個保大年號。後來我在廬山,偶然翻到《廬山志》裡的彭濱〈舍利塔記〉,忽見有南唐保大的年號,便記下來;回上海後,我又檢查別的書,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號。這一段只好列在正誤表裡,等到再版時再挖改了。
我開始改作此書時,北京的藏書都不曾搬來,全靠朋友借書給我參考。張菊生先生(元濟)借書最多;他家中沒有的,便往東方圖書館轉借來給我用。這是我最感激的。余上沅先生、程萬孚先生,還有新月書店的幾位朋友,都幫我校對這部書,都是應該道謝的。疑古玄同先生給此書題字,我也要謝謝他。
一九二八,六,五。
前言 我為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捏造出來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歷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的歷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一千幾百年歷史進化的產兒。國語文學若沒有這一千幾百年的歷史,若不是歷史進化的結果,這幾年來的運動絕不會那樣的容易,絕不能在那麼短的時期內變成一種全國的運動,絕不能在三、五年內引起那麼多人的響應與贊助。現在有些人不明白這個歷史的背景,以為文學的運動是這幾年來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這是大錯的。我們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做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是一百四十五年前的作品。我們要知道,這幾百年來,中國社會裡行銷最廣、勢力最大的書籍,並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程、朱語錄,也不是韓、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遠」的白話小說!這就是國語文學的歷史的背景。這個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滸》、《紅樓夢》......已經在社會上養成了白話文學的信用,時機已成熟了,故國語文學的運動者能於短時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們今日收的功效,其實大部分全靠那無數白話文人、白話詩人替我們種下了種子,造成了空氣。我們現在研究這一、二千年的白話文學史,正是要我們明白這個歷史進化的趨勢。
我們懂得了這段歷史,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參加的運動已經有了無數的前輩、無數的先鋒了;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繼續做無數開路先鋒沒有做完的事業,要替他們修殘補闕,要替他們發揮光大。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個什麼地位。老實說罷,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道:「西洋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代表那一個時代的精神。何以我們中國的文學不能代表時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的差別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錯讀了文學史,所以你覺得中國文學不代表時代了。其實你看的『文學史』,只是『古文傳統史』。在那『古文傳統史』上,做文的只會模仿韓、柳、歐、蘇;做詩的只會模仿李、杜、蘇、黃: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了。你要想尋那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1,千萬不要去尋那『肖子』的文學家,你應該去尋那『不肖子』的文學!你要曉得,當吳汝綸、馬其昶、林紓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時候,有個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場現形記》,有個劉鶚也正在做《老殘遊記》,有個吳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你要尋清末的時代文學的代表,還是尋吳汝綸呢?還是尋吳趼人呢?你要曉得,當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韓愈、歐陽修的『肖子』時,有個吳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個曹雪芹也正在做《紅樓夢》。那個雍正、乾隆時代的代表文學,究竟是《望溪文集》與《惜抱軒文集》呢?還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呢?再回頭一兩百年,當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極力模仿秦、漢,唐順之、歸有光極力恢復唐、宋的時候,《水滸傳》也出來了,《金瓶梅》也出來了。你想,還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來代表時代呢?還是拿《水滸傳》與《金瓶梅》來代表時代呢?—這樣倒數上去,明朝的傳奇、元朝的雜劇與小曲、宋朝的詞,都是如此。中國文學史上何嘗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我們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裡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裡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學家的文學,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於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
「古文傳統史」乃是模仿的文學史,乃是死文學的歷史;我們講的白話文學史乃是創造的文學史,乃是活文學的歷史。因此,我說:國語文學的進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換句話說,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
有人說:「照你那樣說, 白話文學既是歷史進化的自然趨勢, 那麼白話文學遲早總會成立的—也可以說白話文學當《水滸》、《紅樓》風行的時候,早已成立了—又何必要我們來做國語文學的運動呢?何不聽其自然,豈不更省事嗎?」
這又錯了。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演進是無意識的、很遲緩的、很不經濟的,難保不退化的。
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為時間忽然縮短了,因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地加上了一鞭。白話文學的歷史也是如此,那自然演進的趨勢是很明瞭的;有眼珠的都應該看得出。但是這一千多年以來,「元曲」出來了,又漸漸的退回去,變成貴族的崑曲;《水滸傳》與《西遊記》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甚至於《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出來了,人們還仍舊做他們的駢文或古文!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史,只有自然的演進,沒有有意的革命;沒有人明明白白的喊道:「你瞧!這是活文學,那是死文學;這是真文學,那是假文學!」因為沒有這種有意的鼓吹,故有眼珠的和沒眼珠的一樣,都看不出那自然進化的方向。這幾年來的「文學革命」,所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為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新青年》的貢獻只在他在那緩步徐行的文學演進的歷程上,猛力地加上了一鞭。這一鞭就把人們的眼珠子打出火來了。從前他們可以不睬《水滸傳》,可以不睬《紅樓夢》,現在他們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這一睬可不得了了,因為那一千多年的啞子,從此以後,便都大吹大擂的做有意的鼓吹了。因為是有意的人力促進,故白話文學的運動能在這十年之中收穫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績。假使十年前我們不加上這一鞭;遲早總有人出來加上這一筆的;也許十年之後,或者五十年之後,這個革命總免不掉。但是這十年或五十年的寶貴光陰豈不要白白地糟蹋了嗎?
故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種下了近年文學革命的種子;近年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給一段長歷史作一個小結束:從此以後,中國文學永遠脫離了盲目的自然演化,走上了有意創作的新路了。
自序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要我去講國語文學史。我在八星期之內編了十五篇講義,約有八萬字,有石印的本子,其子目如下:
第一講 我為什麼要講國語文學史呢?
第二講 古文是何時死的?
第三講 第一期
(一)—─漢朝的平民文學
第四講 第一期
(二)—─三國六朝
第五講 第一期
(三)—─唐上
第六講 第一期
(三)—─唐中
第七講 第一期
(三)—─唐下
第八講 第一期
(四)—─五代十國的詞
第九講 第一期
(五)—─北宋(1)文與詩
第十講 第一期
(五)—─北宋(2)宋詞
第十一講 第一期的白話散文
第...
目錄
自序
前言 我為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
第一篇 唐以前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第二章 白話文學的背景
第三章 漢朝的民歌
第四章 漢朝的散文
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第六章 故事詩的起來
第七章 南北新民族的文學
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
第九章 佛教的翻譯文學(上)
第十章 佛教的翻譯文學(下)
第二篇 唐朝
第十一章 唐初的白話詩
第十二章 八世紀的樂府新詞
第十三章 歌唱自然的詩人
第十四章 杜甫
第十五章 大曆長慶間的詩人
第十六章 元稹、白居易
自序
前言 我為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
第一篇 唐以前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第二章 白話文學的背景
第三章 漢朝的民歌
第四章 漢朝的散文
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第六章 故事詩的起來
第七章 南北新民族的文學
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
第九章 佛教的翻譯文學(上)
第十章 佛教的翻譯文學(下)
第二篇 唐朝
第十一章 唐初的白話詩
第十二章 八世紀的樂府新詞
第十三章 歌唱自然的詩人
第十四章 杜甫
第十五章 大曆長慶間的詩人
第十六章 元稹、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