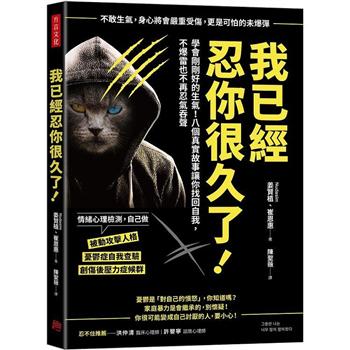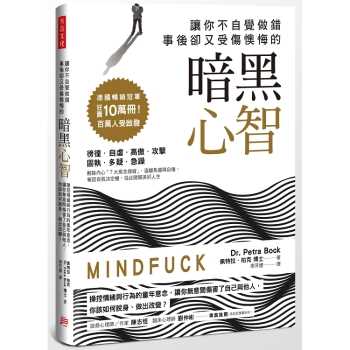序
由於人類的理性運作有其共同性,因此「推理方法」不僅存在於西方,中國與印度的文化傳統中,也有各具特色的「推理」思想。「Logic」在印度稱為「因明」,是有關探究事物原因的學問;在中國則曾被稱作「名學」、「辯學」或「名辯學」。從中國推理方法與西方邏輯相通的一面看,固然有一些相同的要素;不過,由於自然、人文環境的不同,語言表達上的差異,中、西思維方式也有其各自特殊的一面,包括推理的目的、表現方式、主要推理類型等面向都有別於印度與西方。在西方所發展的邏輯系統,重視推論的必然性、正確性,而華人的思維方法相對來說,則較著重改變人行為的實用性與有效性,像在中國古代說服君王的想法、論辯治國之道以及倫理、教化等問題,所涉及的許多思辨、推理方法。在表現方式上,古希臘最早的邏輯研究,受到幾何學與數學的影響,因此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322)的「三段論」既有明確的論式,也有系統的推演規則。中國古代不同於希臘的這種純演繹的推理方式,而是以「類比推論」為主,類比推論的內容涉及接收訊息者的主觀聯想與解讀,因此不能僅從推論形式上考察,還涉及思想內容在文化、思潮脈絡下的可推、不可推或如何推等問題。這些差異源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條件,思維方法、推理方式與人們的生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思維方法、推論形式與思想內容以及外在環境因素都有連帶的關係,需要視為一整體來進行探究。
近數十年來,有關中國名學、辯學、名辯學及中國邏輯史的研究,已有相當之成果。如早期的虞愚、汪奠基、沈有鼎、溫公頤;之後的孫中原、崔清田、劉培育、周云之等學者,以及他們所培養出的一批中壯年學者,大都已在中國各大學任教,在學術界有一定之影響力,在他們的相關著作中已有初步系統及持續性的發展。至於臺灣學界對於中國古代論辯與推理方法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從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研究者首先會確立研究的範圍,再透過閱讀各個家派或某思想家之文獻,進行理解、詮釋、重構等程序,篩選出與「推理」相關的材料。或某些研究者基於對「邏輯」此一概念內涵的理解與把握,再進行材料篩選。在名稱方面,有些學者為區別與西方「邏輯」的不同而採用「名辯思想」或「名辯邏輯」來表述。基本上,許多學者已發現依循《墨子.小取》中的名、辭、說、辯結構,或《荀子.正名》中的名、辭、辨說結構來進行研究是可行之路,並擴大涵蓋範圍,將「認知」與「知識」的相關材料,如《墨經》、《荀子》、《公孫龍子》等認識論的相關思想納入研究對象,因為「名」的確立來自正確的認識,認知的結果為「實」,而「名」反映「實」的內涵;透過概念之「名」組成語句之「辭」,經由不同的語句、推理的「說」構成論點不同的「辯」等思想內容。因此大體上,整個先秦名辯思想的理論是在:認知、名、辭、說、辯的理論架構下,進行相關材料的解讀,研究其中的思維方法與推理規則,進而加以比較並嘗試建立系統。
相應於中國古代名辯學的發展脈絡,本書《論辯與推理——先秦思維方法的對比與轉化》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其一,談名辯與推理:介紹荀子、墨子、韓非子的名辯思想與先秦儒、道、墨、法、名各家的推理方法,是對名辯思想的基本概念與推理方法的介紹。其二,論辯方法與比較:先從出土文獻《戰國縱橫家書》說明縱橫家蘇秦的論辯方法,再將墨子與蘇秦、墨子與孟子、孟子與荀子的論辯觀與方法進行比較。其三,名辯思想的轉化與應用:從墨家思維方法來掌握意義單元的「思想單位」,並從名家公孫龍、惠施及辯者的思想,以及「思想單位」的意義架構來比較儒家與墨家的論辯;此外也將「思想單位」應用於哲學諮商和管理學的跨域研究,進行古代思想的對比整合、古今互通的對比應用。全書從名、辭、說、辯析論,比較到轉化、發展與應用,有其整體性的理路架構。
在中國古代學術研究方面,學界較重視各家各派實質內容的研究,對於古人如何進行思考及其推理方法,則較為忽視。雖然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思維方法的重要性,但每個人的工作、生活、人際互動中,經常都要運用思辨、推理等思維方法,以解決問題。在教育上,我們也需要訓練學習者具有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當我們思考日常問題或進行道德推理時,除了學習西方邏輯之外,也要了解中國古代思維方法與推理應用的智慧。因此本書將筆者近年有關中國名辯學的研究成果集結成冊,或可有拋磚引玉之效,提供有興趣的同道做進一步的討論與研究。此外,由於古代思維方法所具備的實用性與有效性,如何推廣應用於現代生活,這也是值得發展的方向,期待讀者們的回饋與指教。
李賢中
於臺灣大學哲學系水源校區
202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