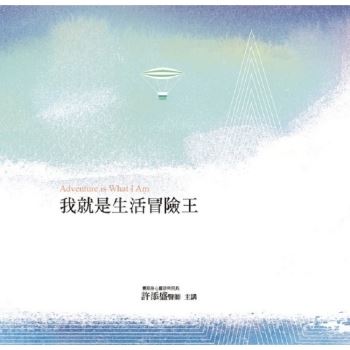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媒體與大眾傳播理論的圖書 |
 |
媒體與大眾傳播理論 作者:Denis McQuail、Mark Deuze / 譯者:羅世宏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24-03-10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711 |
大眾傳播 |
$ 810 |
媒體傳播 |
$ 810 |
社會人文 |
$ 837 |
中文書 |
$ 855 |
大眾傳播學群 |
$ 85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媒體與大眾傳播理論
內容簡介
這部影響深遠的經典傳播學著作已出版第七版,在大數據、演算法文化、人工智慧、全球平台治理、串流媒體和大眾自我傳播的時代,持續思索「大眾」媒體和傳播以及媒體理論的重要性,並關注更多面向的多樣性,大幅拓寬領域敘事引用的觀點和資料來源的廣度,以反映媒體製作世界的變化,為研究二十一世紀的媒體和大眾傳播領域之重要參考書,期能啟發各個世代的學生、媒體和大眾傳播學者。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
阿姆斯特丹大學傳播研究學院榮譽教授與榮譽院士,已於2017年6月25日於倫敦辭世。
馬克.德茲(Mark Deuze)
阿姆斯特丹大學媒體研究教授。
譯者簡介
羅世宏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財團法人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TFAI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
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
阿姆斯特丹大學傳播研究學院榮譽教授與榮譽院士,已於2017年6月25日於倫敦辭世。
馬克.德茲(Mark Deuze)
阿姆斯特丹大學媒體研究教授。
譯者簡介
羅世宏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財團法人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TFAI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
目錄
序言
如何使用本書
第一篇 先導
1 緒論
2 大眾媒體的興衰與復返
第二篇 理論
3 大眾傳播的概念和模式
4 媒體與社會理論
5 媒體、大眾傳播與文化
6 新媒體理論
第三篇 結構
7 媒體結構與績效表現:原理與問責
8 媒體經濟學與治理
9 全球大眾傳播
第四篇 組織
10 媒體組織:結構和影響
11 媒體文化的產製
第五篇 內容
12 媒體內容:問題、概念和分析方法
13 媒體類型、格式和文本
第六篇 閱聽人
14 閱聽人理論與研究傳統
15 閱聽人形構與經驗
第七篇 效果
16 媒體效果的過程和模式
17 媒體效果的典律
第八篇 結語
18 未來
解釋名詞
參考文獻
作者索引
名詞索引
如何使用本書
第一篇 先導
1 緒論
2 大眾媒體的興衰與復返
第二篇 理論
3 大眾傳播的概念和模式
4 媒體與社會理論
5 媒體、大眾傳播與文化
6 新媒體理論
第三篇 結構
7 媒體結構與績效表現:原理與問責
8 媒體經濟學與治理
9 全球大眾傳播
第四篇 組織
10 媒體組織:結構和影響
11 媒體文化的產製
第五篇 內容
12 媒體內容:問題、概念和分析方法
13 媒體類型、格式和文本
第六篇 閱聽人
14 閱聽人理論與研究傳統
15 閱聽人形構與經驗
第七篇 效果
16 媒體效果的過程和模式
17 媒體效果的典律
第八篇 結語
18 未來
解釋名詞
參考文獻
作者索引
名詞索引
序
序
最初的機緣是在2009年,丹尼斯和我在義大利帕多瓦的小咖啡館外喝咖啡。我們當時參加一個由《歐洲傳播學刊》舉辦的媒體變遷影響研討會。與會專家圍繞媒體和大眾傳播理論與研究的「價值」概念展開了重要討論(參見McQuail, 2009)。我們的貢獻是什麼?作為一個領域,我們可以向世界講述什麼故事?我們如何防止我們的訊息被社會學、心理學等其他較老的學科收編和殖民?聊著聊著,我問他傳播領域這本重要教科書的新版本,而且想知道他這本書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並解答這些存在主義哲學層次的問題。他笑了笑說,第六版很快就會出版——而這將會是他的最後一版。我當下感受到這句話的重量——他這本書在塑造和定義大眾傳播領域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對闡明傳播研究的(或可能的)知識貢獻的巨大影響,以及這本書對我個人生涯及理解我正在做的事情上發揮的重大作用。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一個念頭開始醞釀,或許更像是出於一種情感而非念頭:我感到需要做點什麼——對於這本書,對於丹尼斯的遺產,對於所有在全球各地的學校和大學中透過《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自學的學生——從1983年到2010年,以及2010年以後。在Sage出版社的Mila Steele的熱情支持下,我開始為本書新的第七版擬定提案。最初的計畫在2013年提出——它過於雄心勃勃,原本預期我能找到讓我停止教學一到兩年的方式,完全專注於這本將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教科書。儘管丹尼斯在接下來幾年裡盡最大努力支持和鼓勵我,但計畫還是趕不上變化。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10年之後,我搬回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大學開始一份要求很高的新工作,並重組了我在1990年代曾經玩過的樂團Skinflower。
然後到了2017年,6月25日當天傳來丹尼斯辭世這個令人悲慟的消息。1997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初見丹尼斯的情景依稀在目,當時正逢阿姆斯特丹大學傳播研究學院成立,而我是首批博士生之一。美好回憶之一是院方安排的活動,丹尼斯與首批博士生座談,針對博士生的論文構想提供回饋建議。在那個初次見面的場合,他開懷大笑:「我只希望你們能找到時間和金錢,去做你們打算做的所有事情!」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有幸與Piet Bakker合授傳播理論課程,對阿姆斯特丹大學一年級學生講授《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這本教科書。這一初體驗啟發了我後來在明斯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以及回到阿姆斯特丹大學(這次是在媒體研究系)教授此類大學部課程的方式和熱愛。
簡單說,無論是個人機緣或專業因素,我一直有很多理由擁抱他的這本堪稱「眾書之書」(book of books)的鉅著。他去世後,我再也沒有任何藉口:這項工作必須開始了。感謝Sage出版社的Mila和Michael Ainsley的持續支持和指導,我的朋友兼同事Pauline van Romondt Vis在處理書稿和對初步評估所需完成的工作,提供了寶貴幫助,以及幾位親愛的朋友和專家:Peter Neijens、Terry Flew、Kaarle Nordenstreng、Peter Golding、Claes De Vreese、Cristina Archetti和Sonia Livingstone——的批判性閱讀的慧眼,他們願意為本書審閱部分章節的初稿。從2017到2019年間,我持續撰寫第七版,期間偶爾停工,忙於教學、其他研究計畫、音樂表演,以及烤肉活動。
這本新版的《麥奎爾的媒體與大眾傳播理論》,首先是向丹尼斯的著作和影響的致敬。這既體現在忠於他對本書(和領域)的結構安排,也體現在將他的敘述延伸到我們當前所處的普遍、無處不在、行動/移動、社交和隨時在線上的媒體世界。同時,我也自由地稍微改變了一些安排。您會注意到,我們在書名中添加了「媒體」 一詞,以使媒體理論在學術領域取得的智識進展得到應有的重視,並表明我們有意讓理論的哲學思辨傳統與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發展出來的媒體與社會研究有所對話。在本書中,你不會看到這些研究領域處於明確分隔的狀態,這既受到我自己學術背景的啟發,更重要的是來自於傳播領域內持續呼籲的影響,要求更加整合的理論框架、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及多重檢核(triangulation),以便恰當地應對大眾媒體環境與大眾傳播過程的複雜性和細微差別。
第二個調整之處是引用新文獻,將相關討論推進到21世紀。丹尼斯開展的這本教科書,我試圖盡我所能地繼續下去,以大幅拓寬我們領域敘事引用的觀點和資料來源的廣度。這意味的是避免獨尊美國和英國學者,更多地關注更多面向的多樣性,同時也更加重視來自世界各地開放近用的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和書籍。
鑒於我自己鑽研媒體工作(media work)的背景,我試圖讓關於製作、內容和閱聽人的章節足以反映媒體製作世界的變化。同時,我們努力為整本書中關於媒體閱聽人的說法添加更多細微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Sonia Livingstone的洞見和評論。
為了保持敘事的流暢,我決定將丹尼斯關於需要規範性理論(normative theory)的明確論點打散到本書的其他章節中。他在這個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讓學生和學者對媒體在社會中的需求和期望負起責任,他闡述的規範關切讓我們意識到在媒體與大眾傳播的研究中指導著我們的理想主義,甚至懷有希望的假設和觀點。透過將原本是一個獨立章節的規範理論的各個部分整合起來,我希望能夠恰如其分地對待丹尼斯如此重視的部分。
對於之前被分開討論的「社會文化」媒體效果,以及媒體對新聞、民意/公眾輿論和政治傳播的影響和效果,我也採取了相同的處理方式。我遵循阿姆斯特丹同事Patti Valkenburg和Jochen Peter在各種著作中建議的方法,透過研究(大眾)媒體效果的經典焦點,而不是摘要和分開討論各種(有關媒體效果的)特定理論。
回顧這個過程,我發現先導篇(第1章和第2章)和結語(第18章)花了我最多時間,以探索、調查且最後熱情地論證,思索「大眾」媒體和傳播以及媒體理論的持續重要性,在大數據、演算法文化、人工智慧、全球平台治理、串流媒體和大眾自我傳播的時代——所有這些過程,如果沒有大眾傳播和大眾媒體理論的幫助,我們是無法充分理解的。
正如我在本書中多次論證的那樣,媒體和大眾傳播理論和研究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的是關於我們所處的現實和世界的兩個基本假設:首先,媒體是全球日常生活經驗中普遍且無所不在的一部分。第二,所有這些中介傳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都會產生影響。儘管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來自大學(及大學之外)的大多數研究人員將這些核心觀察結果視為後見之明、次要問題或影響他們研究的現象的問題所在。我們假設「世界上」的任何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中介的(mediated),這並不是支持科技決定論或媒體中心論的思維方式,而是對我們領域核心的肯認,以及我們如何理解全球化和個體化的雙重過程、後國家組織與其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對應物、不斷進行中的自動化和科技吸納一切,以及回歸情感和真實性作為指導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還有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全球性挑戰:氣候變遷、人道主義危機和永續發展。所有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透過媒體來理解,以媒體的術語進行,並且需要一部分地透過媒體來回應這些挑戰。我衷心希望這本更新版的著作有助於啟發各個世代的學生、媒體和大眾傳播學者。對我來說,能夠參與這項工作是一個莫大的榮幸。
最初的機緣是在2009年,丹尼斯和我在義大利帕多瓦的小咖啡館外喝咖啡。我們當時參加一個由《歐洲傳播學刊》舉辦的媒體變遷影響研討會。與會專家圍繞媒體和大眾傳播理論與研究的「價值」概念展開了重要討論(參見McQuail, 2009)。我們的貢獻是什麼?作為一個領域,我們可以向世界講述什麼故事?我們如何防止我們的訊息被社會學、心理學等其他較老的學科收編和殖民?聊著聊著,我問他傳播領域這本重要教科書的新版本,而且想知道他這本書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並解答這些存在主義哲學層次的問題。他笑了笑說,第六版很快就會出版——而這將會是他的最後一版。我當下感受到這句話的重量——他這本書在塑造和定義大眾傳播領域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對闡明傳播研究的(或可能的)知識貢獻的巨大影響,以及這本書對我個人生涯及理解我正在做的事情上發揮的重大作用。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一個念頭開始醞釀,或許更像是出於一種情感而非念頭:我感到需要做點什麼——對於這本書,對於丹尼斯的遺產,對於所有在全球各地的學校和大學中透過《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自學的學生——從1983年到2010年,以及2010年以後。在Sage出版社的Mila Steele的熱情支持下,我開始為本書新的第七版擬定提案。最初的計畫在2013年提出——它過於雄心勃勃,原本預期我能找到讓我停止教學一到兩年的方式,完全專注於這本將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教科書。儘管丹尼斯在接下來幾年裡盡最大努力支持和鼓勵我,但計畫還是趕不上變化。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10年之後,我搬回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大學開始一份要求很高的新工作,並重組了我在1990年代曾經玩過的樂團Skinflower。
然後到了2017年,6月25日當天傳來丹尼斯辭世這個令人悲慟的消息。1997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初見丹尼斯的情景依稀在目,當時正逢阿姆斯特丹大學傳播研究學院成立,而我是首批博士生之一。美好回憶之一是院方安排的活動,丹尼斯與首批博士生座談,針對博士生的論文構想提供回饋建議。在那個初次見面的場合,他開懷大笑:「我只希望你們能找到時間和金錢,去做你們打算做的所有事情!」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有幸與Piet Bakker合授傳播理論課程,對阿姆斯特丹大學一年級學生講授《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這本教科書。這一初體驗啟發了我後來在明斯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以及回到阿姆斯特丹大學(這次是在媒體研究系)教授此類大學部課程的方式和熱愛。
簡單說,無論是個人機緣或專業因素,我一直有很多理由擁抱他的這本堪稱「眾書之書」(book of books)的鉅著。他去世後,我再也沒有任何藉口:這項工作必須開始了。感謝Sage出版社的Mila和Michael Ainsley的持續支持和指導,我的朋友兼同事Pauline van Romondt Vis在處理書稿和對初步評估所需完成的工作,提供了寶貴幫助,以及幾位親愛的朋友和專家:Peter Neijens、Terry Flew、Kaarle Nordenstreng、Peter Golding、Claes De Vreese、Cristina Archetti和Sonia Livingstone——的批判性閱讀的慧眼,他們願意為本書審閱部分章節的初稿。從2017到2019年間,我持續撰寫第七版,期間偶爾停工,忙於教學、其他研究計畫、音樂表演,以及烤肉活動。
這本新版的《麥奎爾的媒體與大眾傳播理論》,首先是向丹尼斯的著作和影響的致敬。這既體現在忠於他對本書(和領域)的結構安排,也體現在將他的敘述延伸到我們當前所處的普遍、無處不在、行動/移動、社交和隨時在線上的媒體世界。同時,我也自由地稍微改變了一些安排。您會注意到,我們在書名中添加了「媒體」 一詞,以使媒體理論在學術領域取得的智識進展得到應有的重視,並表明我們有意讓理論的哲學思辨傳統與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發展出來的媒體與社會研究有所對話。在本書中,你不會看到這些研究領域處於明確分隔的狀態,這既受到我自己學術背景的啟發,更重要的是來自於傳播領域內持續呼籲的影響,要求更加整合的理論框架、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及多重檢核(triangulation),以便恰當地應對大眾媒體環境與大眾傳播過程的複雜性和細微差別。
第二個調整之處是引用新文獻,將相關討論推進到21世紀。丹尼斯開展的這本教科書,我試圖盡我所能地繼續下去,以大幅拓寬我們領域敘事引用的觀點和資料來源的廣度。這意味的是避免獨尊美國和英國學者,更多地關注更多面向的多樣性,同時也更加重視來自世界各地開放近用的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和書籍。
鑒於我自己鑽研媒體工作(media work)的背景,我試圖讓關於製作、內容和閱聽人的章節足以反映媒體製作世界的變化。同時,我們努力為整本書中關於媒體閱聽人的說法添加更多細微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Sonia Livingstone的洞見和評論。
為了保持敘事的流暢,我決定將丹尼斯關於需要規範性理論(normative theory)的明確論點打散到本書的其他章節中。他在這個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讓學生和學者對媒體在社會中的需求和期望負起責任,他闡述的規範關切讓我們意識到在媒體與大眾傳播的研究中指導著我們的理想主義,甚至懷有希望的假設和觀點。透過將原本是一個獨立章節的規範理論的各個部分整合起來,我希望能夠恰如其分地對待丹尼斯如此重視的部分。
對於之前被分開討論的「社會文化」媒體效果,以及媒體對新聞、民意/公眾輿論和政治傳播的影響和效果,我也採取了相同的處理方式。我遵循阿姆斯特丹同事Patti Valkenburg和Jochen Peter在各種著作中建議的方法,透過研究(大眾)媒體效果的經典焦點,而不是摘要和分開討論各種(有關媒體效果的)特定理論。
回顧這個過程,我發現先導篇(第1章和第2章)和結語(第18章)花了我最多時間,以探索、調查且最後熱情地論證,思索「大眾」媒體和傳播以及媒體理論的持續重要性,在大數據、演算法文化、人工智慧、全球平台治理、串流媒體和大眾自我傳播的時代——所有這些過程,如果沒有大眾傳播和大眾媒體理論的幫助,我們是無法充分理解的。
正如我在本書中多次論證的那樣,媒體和大眾傳播理論和研究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的是關於我們所處的現實和世界的兩個基本假設:首先,媒體是全球日常生活經驗中普遍且無所不在的一部分。第二,所有這些中介傳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都會產生影響。儘管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來自大學(及大學之外)的大多數研究人員將這些核心觀察結果視為後見之明、次要問題或影響他們研究的現象的問題所在。我們假設「世界上」的任何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中介的(mediated),這並不是支持科技決定論或媒體中心論的思維方式,而是對我們領域核心的肯認,以及我們如何理解全球化和個體化的雙重過程、後國家組織與其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對應物、不斷進行中的自動化和科技吸納一切,以及回歸情感和真實性作為指導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還有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全球性挑戰:氣候變遷、人道主義危機和永續發展。所有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透過媒體來理解,以媒體的術語進行,並且需要一部分地透過媒體來回應這些挑戰。我衷心希望這本更新版的著作有助於啟發各個世代的學生、媒體和大眾傳播學者。對我來說,能夠參與這項工作是一個莫大的榮幸。
馬克.德茲
2020年寫於阿姆斯特丹、(英格蘭北海岸的小村莊)西頓斯魯斯
2020年寫於阿姆斯特丹、(英格蘭北海岸的小村莊)西頓斯魯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