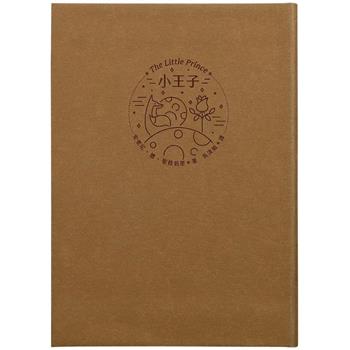序
為霞尚滿天──金聖華著《人來人往》序
金耀基
(一)
認識金聖華教授已經半個世紀了。一九七七年我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 書院是一「 共和國」, 金聖華是共和國「 校園生活及文化委員會」 的靈魂人物。新亞八年院長任期中,我們成爲相知相識的同事。院中同仁多以「大金」、「小金」稱呼我與聖華,我們彼此則以「本家」互稱。那時,我剛過「不惑之年」,「小金」小我幾歲,風華正茂,嬌柔優雅,妻元禎一直以「嬌滴滴」 稱她而不名。一九八五年離任院長,回到本職的社會學系。在中大三十四年中, 我夫婦與聖華和她夫婿Alan 一直有來有往,可説是通家之好。二〇〇四年我自中大退休,我與本家見面雖少了許多,但我每月在《明報月刊》總看到她的專欄,看完就交給妻分享,元禎總不忘讚「她寫得很美」。八十年代後,金聖華在翻譯專業上,又出書,又演講,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就卓越,聲名日盛, 一九八七年《牛津高階雙語詞典》的序文,就是請金聖華、余光中、陸谷孫三位撰寫的。一九九一年金聖華更當選為「香港翻譯學會會長」。當看到她譯的《傅雷家書》時,我脫口說「聖手譯華章」,聖華已是譯壇「聖」手,她譯的文字也成爲篇篇「華」章了。近二十年來,為林青霞視作文學「繆司」的金聖華,除了鑄刻翻譯的華章,更撰寫金雕玉琢的散文,翻譯與散文是金聖華的文學雙璧。聖華的散文不止精,而且多,這些年來,我曾先後爲她其中三本散文集題簽,即《打開一扇門》(一九九五)、《友緣、有緣》(二〇一〇)與《樹有千千花》( 二〇一六), 我禁不住暗讚聖華筆耕的勤奮。二〇二二年, 聖華贈我《 談心─與林青霞一起走過的十八年》,一見驚豔。此書所展現的是金聖華陪伴、見證一代巨星林青霞從影壇向文壇半個成功轉身的絢爛畫卷。《談心》問世不及一年,二〇二三年六月聖華又交來厚厚一大曡以《人來人往》爲名的書稿。這是本家第一次開口要我寫序,我自然是欣然應命。
(二)
《人來人往》共四十六篇文字,分爲六輯,每輯有個主題。
第一輯「 文藝漫筆」, 是聖華寫她文藝生涯中所結緣的人與事, 她寫林青霞、白先勇、宋淇、楊憲益、莫言、李景端、徐俊、黃秀蓮等, 在她生花之筆下,每一篇都是一個文藝世界有光有熱的故事。
第二輯「暖心親情」,我們看到了聖華的私己世界,她用最有溫度的筆法寫出了她的三代親情。此輯寫的:有母親手溫的拐杖;老父送給他老妻親繪的一束紅玫瑰;夫婿Alan 溫良恭儉讓的「忘我」;女兒的體貼與善良;兒子有一個「老是笑臉迎人的面龐」;還有經年參商萬里相隔,卻感常在身邊的大哥。聖華經歷過家人的生離死別,但她一輩子都沐浴在溫馨的親情中。
第三輯「生活點滴」,這一輯聖華寫的是自己。看到她寫〈不厭其煩與不勝其煩〉,不禁會心失笑,日常之事,有的是不「厭」其煩,蓋心之所欲,樂在其中;有的是不「勝」其煩,蓋浪費生命,苦不堪言耳。一字之別,盡見她的生活姿態。有意思的是,作者從走路、zoom、磁力共振體驗這樣生活點滴的經驗中卻引發出對生命真諦的悟覺。
第四輯「回首往昔」,暮年晚秋,撫今思昔,聖華的彩筆讓我們見到她濃濃詩情的少女歲月,看到她青春時代的喜與愛,樂與怒。聖華不悲秋,不傷春,在回顧青葱華年的時刻,總是聲氣風發地說,「珍惜今朝」!
第五輯「巴黎歲月」。巴黎是作者的夢鄉,她的文學博士學位是在巴黎大學獲得的。但她寫讀書時最初寄住的「婦女宮」(救世軍宿舍的別名)卻是一所奇心(對不起,本家)的是聖華「冒火」的樣子,看到她「法文說得最多最沒有顧忌」的樣子。聖華還是深愛她的夢鄉,愛到不敢寫,「怕寫不盡她的好,道不清她的美」,所以她不寫巴黎,而是寫「花都三劍客」,那是她三位巴黎的妙友。「巴黎歲月」是聖華常存心中如霧如嵐的回憶。
第六輯「追思故友」,這一輯寫的是聖華對逝去友人的追思。〈愛美的赤子〉寫的是譯林高手喬志高;〈記勞公二三事〉寫的是哲學大師勞思光;〈一斛晶瑩念詩翁〉寫的是大詩人余光中,〈將人心深處的悲愴化爲音符〉寫的是鋼琴家傅聰;〈懷念羅新璋〉寫的是傅雷的入室弟子羅新璋;〈當時明月在〉寫的是至交大才女林文月。聖華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榮譽博士、院士寫讚詞的特聘撰稿人,她總是在不失「真」的底綫上,以最恰當的文學語言寫出各個「主人翁」的大德大美。且看她以〈爲人不忘「悟聖」,處事樂聞「和聲」〉寫中大和聲書院創立人李和聲,真是善頌善禱!
(未完)
自序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我離開出生地上海,隨媽媽、娘娘(祖母)、四爹(四叔)一起上路, 經天津輾轉赴台, 跟早已在那裡工作的爸爸會合。那時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時代變遷,此去經年,再返回故里,已經是悠悠三十載後的事情了。
從上海出發,要先坐四小時火車去南京,然後擺渡到浦口,再坐津浦路到天津,在天津乘船,經香港再前往台灣。那是我第一次坐長途火車,一路上,只覺得路遙遙而人茫茫,仿佛一直走不到盡頭。當年幼小的自己,雖然面對四周的一切感到新鮮好奇,然而心底卻已泛起絲絲莫名的離愁─想念熟悉的環境,想念留在家裡的哥哥,想念窗前的碧茵屋後的樹……。
此行路途迂迴而曲折,回想起來,那時媽媽一個弱質女子,扶老攜幼,萬里投親,真不知道她是怎麼挺過來的。只是當年的我,少不更事,媽媽的艱辛奔波一點都記不起,只記得火車上人頭湧湧,衆聲喧嘩,列車沿途一站站的停,停站時小販一擁而上,叫賣食物雜貨,有一種燒雞特別好吃,味道甘香,至今難忘。車廂中有人上,有人下,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然後,又在隆隆車聲中,各自奔向不同的前程了。
長大後,從台灣搬遷到香港,在此接受中學和大專教育,接著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也曾到過美加歐洲進修,紐澳亞非遨遊,行履遍及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然而,真正安身立命的場所,卻是我駐足超越半個世紀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從學生年代到執教時期,眼看著背山面海的校址,從草創階段發展到高樓林立,我追隨著中大的足跡,亦步亦趨,在此成長,在此拓展,在此邁上漫漫人生路。
每次上學或上班,從中大的前身崇基學院開始,都是搭趁火車往返的。在沒有電氣火車的日子,設備簡陋的舊車,在鐵路上搖搖晃晃,一路汽笛長鳴,穿山越洞而馳,路旁一邊綠田伸展,一邊碧波蕩漾,倒也別有風味。那時候,列車上擠滿了窗友或同儕,大家都青春年少,心中懷著一個浪漫的夢,期望著有一天能施展抱負,仗劍走天涯!
多少年過去了,如今的列車,風馳電掣,速度驚人,在急劇的節奏中,車站更加熙熙攘攘,車上更加人來人往,不知衆人心中是否懷著更加繽紛的夢?
生命,是一列火車,從啟程到終點,要經歷過遙遠的路程,此中有高山,有低谷;有大城,有小鎮;有遼闊的草原,有狹隘的關卡,甚至還有黑黝黝的漫長隧道。
每到一站,都有人上車下車,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這本書記錄的,就是在生命的旅途上,生活的列車中,我所遇見的人與事。人生如羈旅,你我皆過客,大千世界,芸芸眾生,那麼多來往的人群之中,為什麼我會邂逅他或她?邂逅了,又留下什麼難忘的片刻,銘心的交會?
都說,從出世的那一刻起,我們由父母帶領,協同踏上生命的列車,儘管周圍嘈雜,我們仍能坐看人潮,好整以暇,因為有椿萱依傍,世界在面前踏步邁進,或碎步走過,我們都不孤單。然後,到了某一站,他們抵達終點了,不得不打開車門,揮手握別而去。
接著,火車前行,人來人往,我們又遇上了形形色色的他鄉客,在孤獨的旅程中,縱使萍水相逢,卻也會找到志同道合的知音,共度溫馨怡情的片刻。多少次,在火車停站的時刻,我們曾經攜手共遊,到站旁的草原上去閒眺,去採擷,直至採得滿懷芬芳,才盡興而返。火車再次啟動,有的朋友提前退場,然而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的溫言細語,卻縈繞腦際長相憶,常駐心中永難忘。有的朋友卻留下相伴,我們日日相依,夜夜談心,在晨曦夕照中,言笑晏晏,共賞窗外的景色,閒看風雲的變幻。
這本書所收錄的,大多是二〇一八年以來發表在各種報章刊物(其中以《明報月刊》為主)上的散文,涉及文藝漫筆、暖心親情、生活點滴、往昔歲月等範疇,主要分為寫他人、說自己、思故友三類,記述熙來攘往的生命之旅中,值得追憶的人與事,願以此與長長列車、迢迢旅途上往返的朋友共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