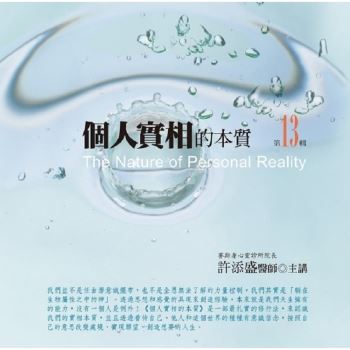前言
戰爭是否仍在遠方?
兩年多前覓得一間高樓小屋,一心要把俯瞰整個淡水河出海口的大陽台當書房。一張高腳圓桌,一對高腳椅,從早伏案寫到黃昏收工,抬頭便是灼灼海口嚥日。
《止戰》一書的書寫還充滿獨特的聽覺與嗅覺感官經驗。高樓旁就是後備動員幹部訓練中心(忠莊營區),本來只有星期二下午固定傳來稀稀疏疏的打靶聲。後來想是美國敦促急了,要求國軍拿出戰鬥的決心與毅力,哪怕是後備軍人教召都被迫加強認真了起來,每日上午下午都傳來一陣接著一陣的實彈射擊打靶聲。《止戰》一書就是在槍聲陣陣、空氣中不時瀰漫著淡淡煙硝味中完成。
站在陽台同樣的位置,看中秋節前後漁人碼頭這邊的煙火燦爛,有時也看八里海灘那邊的漢光演習。站在陽台同樣的位置,抬頭可見從桃園機場起飛的民航機,在高高的藍天白雲之上悠緩移動,有時則是戰鬥軍機以極大的聲爆凌空飛掠。更有兩次深夜被驚醒,衝到陽台同樣的位置俯身下望,兩輛雲豹裝甲車一前一後,以震耳欲聾聲緩慢行駛在中正路上,超現實感十足。淡水是個神奇的地方,戰爭遺跡處處,就連每日清晨散步的滬尾砲台公園,也是中法戰爭滬尾之役的古戰場。站在陽台同樣的位置,也清楚可見忠莊營區內一棟橘紅色平頂小屋,昔日冷戰時期的「成功閣招待所」,台灣最早期與美國中情局合作、用來訓練突襲中國的情報人員之地,當然也用來審訊拷打共軍俘虜。一牆之隔,如今牆外已是熱鬧非凡的福容飯店與各種遊樂設施,遊人如織。
除了空間的感官經驗、歷史記憶與日常生活外,《止戰》一書也有來自時間催逼的焦慮與不安。全書的構想起心動念於二○二二年八月時任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台海關係空前緊張,二○二三年二月寫完緒論與第一章,俄烏戰爭爆發,十月交稿校對之際,以巴衝突中東戰火一發不可收拾,才又臨時增添了此篇前言。《止戰》談戰爭,聚焦台海,但詭譎多變的台海緊張關係與俄烏、以巴戰爭的相繼爆發,好似時時都在催逼著資料的增添、詮釋的更新與思考的持續摺曲。時間瞬息萬變,但在帶來焦慮與不安的同時,有時卻也彷彿可以超級詭異地陷入一種凝止不動,而讓人更感挫折沮喪。就讓我們先來看看下面這段文字:
許多以色列媒體主張,如果有平民或孩童遭到殺害,那是因為哈馬斯躲藏於平民之中,利用孩童當擋箭牌,並使得以色列必須合法地殺害平民和孩童以求自保,不受哈馬斯攻擊……如果被迫擊砲與磷彈殺害的巴勒斯坦孩童是人盾(human shields)的話,那他們根本就不是孩童,而是軍備武裝的一小部分,推進並教唆對以色列的攻擊。
這段文字說明了以色列何以會徹底違反《日內瓦公約》、無差別地轟炸平民百姓、犯下戰爭罪,而所謂民主國家的「西方價值」也一直為其開啟著綠燈通行。對以色列而言,巴勒斯坦孩童不是孩童,孩童是哈馬斯(Hamas)的武裝盾牌,平民不是平民,平民是以色列總理與國防部長矢志復仇口號中的動物野獸,等同於哈馬斯。衝突爆發一個月來,加薩地區已有超過數千名孩童喪命,平均每十分鐘就有一名巴勒斯坦孩童死去,但老神在在的美國總統拜登卻堅稱不相信巴勒斯坦所提供的傷亡數據統計。
但最弔詭的是,這段文字並非針對當下的以巴戰爭。這段文字早早就出現在二○一○年《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作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乃全球知名的女性主義學者,早年以《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揚名立萬,亦著有《分道揚鑣:猶太性與猶太復國主義批判》(Parting Ways: Jewishness and the Critique of Zionism)、《非暴力的力量:一種倫理─政治繫結》(The Force of Nonviolence: An Ethico-Political Bind)等書,深刻反省戰爭。巴特勒身為猶太裔美國人,卻堅決反對猶太人要無條件認同以色列,更嚴厲批判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自是引來眾多猶太人的集結抗議,指其不僅「反美」、「反以色列」,更「反猶太」(巴特勒所遭受最嚴重的死亡威脅,反倒是來自其性/別理論在拉美國家產生的重大影響)。巴特勒在此所言的「人盾」,乃是針對二○○八年十二月以色列對加薩發動的一場為期二十二天的軍事攻擊,以反擊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南方城鎮發射火箭。巴勒斯坦人權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統計此次攻擊使得一千四百一十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四千三百三十六名巴勒斯坦人受傷,而大部分傷者與死者皆為平民。聯合國特派員李察‧福克(Richard Falk)提供的數字則是:一千四百三十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九百六十人為平民,而這些平民之中,有一百二十一人為女性,兩百八十八人為孩童。
但時間彷彿凝止不動,十多年前的批判介入,其思維與修辭恍如今日,可見仇恨糾結依舊不解。這就是巴特勒一再苦心孤詣、批判再批判的「戰爭的框架」,一種「行規範之名而不思索」(non-thinking in the name of the normative),一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言「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而得以讓武裝衝突一再出現,以眼還眼、以暴制暴,反覆循環中,人間煉獄迭至。但如果我們覺得巴特勒或鄂蘭的分析太過抽象,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一位十九歲以色列少女充滿憤怒與憂傷的控訴。她不是那位廣為媒體報導的十九歲以色列女兵,當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五十年來最猛烈的攻擊後,原本在紐約渡假的她,立即返回以色列參戰,旋即為捍衛國家而陣亡。她比較像另一位十九歲的俄羅斯少女,曾因在其就讀的大學散發反戰傳單而受處罰,後更因在IG上發文批評俄軍入侵烏克蘭而遭到逮捕。這位十九歲的以色列少女覺得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開口閉口矢言「復仇」甚是可恥,她和同年齡的俄羅斯少女一樣都挑戰自己國家的「戰爭的框架」,都不願重複「行規範之名而不思索」。
這位生長在加薩邊境以色列貝里屯墾區(Kibbutz Be’eri)的少女,剛剛僥倖逃過了哈馬斯的血腥屠殺,但在鏡頭前她強烈要求的不是復仇,而是「公平正義的和平」(a just peace)。她提及在戰場上殞落的小時玩伴,從幼稚園開始就殷切表達長大後要加入軍隊,她質疑難道將來她也必須這樣教育她的孩子嗎?她也憤怒自己的國家對加薩平民的猛烈攻擊,甚至不惜炸死人質。她所謂的「和平」絕不是由以色列單邊界定下的殖民暴力、種族隔離與嚴格軍事管控。她所謂的「公平正義」乃是要讓在以色列南部尼格夫沙漠不斷被以色列強行驅離的阿拉伯遊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s in Negev),能夠和她所在的貝里屯墾區一樣獲得資源。7 十九歲的以色列少女和巴特勒居然都異口同聲地說,在生死存亡的掙扎邊緣,不要用OK繃(鐵穹,軍隊,屠殺)蓋住正在流血的傷口。而此「公平正義的和平」就是多年來巴特勒所一再強調的「基進平等」(radical equality)。若中東地區「戰爭的框架」乃是讓可迫害性、可受傷性、可弔唁性出現巨大的差別分配─某些生命珍貴,某些生命如草芥,某些生命值得保護,某些生命隨時可棄─那如何停止「行規範之名而不思索」,便是阻斷既有戰爭認識論的第一步,而不是陷落在宗教差異、歷史仇恨、地緣政治之中束手無策。
那什麼會是台海之間「戰爭的框架」呢?我們如何有可能鬆動、拆解或創造、轉化台海戰爭的特定認識論立場呢?《止戰》正是以此初衷展開對台海戰爭的「哲學思考」與「倫理行動」。此處的「倫理」不是道德、教條、誡命,而是「關係性」(relationality),一個有關訴求與回應的行動:「倫理性的首要意涵並非描述行徑或傾向,而是標示出一種理解關係架構的方式,並理解到意義、感知、行動和言說都是在關係架構中才得以可能。關係性描繪的是一種訴求的結構,而我們在此結構中被召喚採取行動,或以特定方式回應召喚」。我們如何能將「關係性」帶入對「主體」與「主權」的思考之中呢?我們又如何能將戰爭的「哲學思考」轉化為日常生活的倫理實踐呢?《止戰》正是希望透過重重的思考難局測試,期許能在台海「戰爭的框架」中走出不一樣的路,說出不一樣的話,做出不一樣的事。
緒論
「止戰」作為難局
為何要談「止戰」?如果「止戰」不等於停止戰爭,那「止戰」有可能成為啟動戰爭的極限思考、一個有關戰爭「不可能性」(不是戰爭的不可能,而是思考戰爭的不可能)的極限思考嗎?「止戰」究竟與眾人更為耳熟能詳、在台灣亦已吵成一團的「反戰」、「避戰」、「引戰」或「備戰」有何差異之處嗎?
本書緒論嘗試從一個中文方塊字「止」與一個希臘字源的外文字aporia開始談起,企圖由前者開展出「止」的說文解字,再構連後者aporia所可能帶出的理論概念,以便能在當前「台海戰爭」眾聲喧嘩的論述之中,給出一種在「戰爭vs.和平」之外的差異思考。如果「戰爭vs.和平」的二元對立無法成立,如果「要和平」抑或「要戰爭」的二選一徹底失效,如果戰爭威脅恆常在「掌控」與「失控」之間擺盪,那我們將如何重新看待兵凶戰危的台海對峙呢?
就讓我們先從「止」的歧義說起。《說文解字》卷三對「止」的解釋:「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凡止之屬皆從止」。故若就象形圖示而言,止乃基址根部,可被視覺化為草木萌發初生時長出地面的根幹;若就引申假借而言,草木之基址根部如同人之基址根部,故「以止為足」,「止」即足。
由此可見在東漢許慎的文字學詮釋中,「止」由草木之下基轉而成為人之下基,「止」即足,自是與「行走」緊密貼合,已與草木無涉。此處的「足」乃下肢的總稱,包括股(大腿)、脛(小腿)、蹠(腳掌)、跟(足後為跟、足踵);亦可專指膝蓋以下的部分,亦即脛(小腿),一如《說文解字》所言「足,人之足也,在下,從止口」,口象膝形,「腳,脛也」,足之別稱。
此外亦有暫時脫離《說文解字》而回歸商朝甲骨文「字形」的嘗試,將「以止為足」的範圍,直接縮小到「蹠、跟」,踝骨以下的部分,亦即腳板,包括腳趾、腳掌、腳跟。「止」於是轉而成為人腳板的象形,不再是「象艸木出有址」,而是三個腳趾,加上腳掌與腳跟。「止」
之為腳板的象形,更常被附會到「步」的造字,視其為上下前後兩個「止」,亦即一右前、一左後的兩個腳板,表示雙足往前行走之意。
但不論是較大範圍的「股、脛、蹠、跟」,或較小範圍的「脛」、「蹠、跟」,「以止為足」所帶出的,都是「行走」的動態身體姿勢。但「止」的「邁步向前」,卻也同時弔詭地與「停住不動」相通,彷彿是要「止」在邁步向前所到達之處停住不動(「止於至善」、「適可而止」、「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由此產生停留、歇息、駐守、居住之意。故「止」究竟是「邁步向前」、抑或「停住不動」,抑或「邁步向前」與「停住不動」之間的交錯參差,實乃動靜難分、進退難辨。而「止」的歧異/歧義與不確定性,乃直接關乎我們對「止戰」的詮釋方式:「止戰」究竟是「邁步向前」迎向戰爭,還是「停住不動」止息戰爭,抑或是直接踩在戰爭的邊界極限之上「停也,足也,禮也,息也,待也,留也」(《廣韻》對「止」之詮釋),一時之間恐難有定論。
一‧「止戈為武」的戰爭與和平
接下來就讓我們以「武」為例,來再次凸顯「止戰」的弔詭與多重。「武」乃「止」與「戈」所構成的異文會意字,而「武」作為戰爭抑或和平的不確定性,乃直接來自「止」作為「邁步向前」抑或「停住不動」的不確定性。在此我們可以嘗試比較兩個古文字學的不同版本與詮釋方式。第一個版本當然是再次回到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許慎此處所引用的,乃是最為人所熟知「止戈為武」的說法,典出《左傳‧宣公十二年》,原文為「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意指合止戈二字而成的「武」,其真正要義乃是止息干戈(干戈皆為古代兵器,「戢兵」乃收藏兵器)以停止戰事與紛爭。換言之,「武」的最高境界乃是停止動用武器、消弭軍事行動。
第二個則是殷墟甲骨文的版本。誠如古文字學學者于省吾在《殷契駢枝三編‧古文雜釋》所言,「武從戈從止,本義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
此處所言最早甲骨文的「止」乃是展示行動,「止戈」遂不再是「止息干戈」,「止戈」已徹底翻轉為「戈止」,亦即手上持戈、腳步向前、揮兵向敵、征戰討伐。「按武取止戈之意,不確。所從止乃足趾之趾本字。甲骨文從止多表示行動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