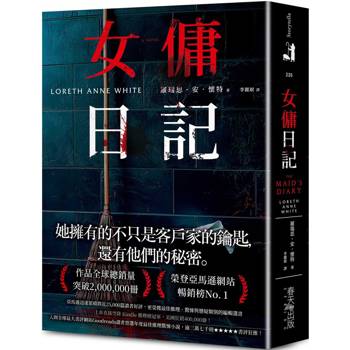突然,他成了一個瘋狂的人。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哈金最震撼代表作。
這本小說是開端也是告別,
它標誌著我與中國的決裂。——哈金
一九八九年,萬堅在中國北方的山寧大學裡當研究生,某日他的指導教授楊慎民突然中風,與楊教授的女兒梅梅已訂下婚約的他,責無旁貸擔起照顧的責任。不過住院療養的楊教授行徑愈發詭異,時不時吟詩、唱起革命歌曲,大聲對著看不見的人求饒、抗議學校不公……這些究竟是精神崩潰下的胡言亂語,或者當中攙雜著不為人知的真話?
本書主題是六四天安門事件,這是哈金人生的轉捩點。全書以第一人稱書寫,透過主角萬堅毫無矯飾的目光,寫出個人被集體瘋狂包圍並掐住喉頭的苦澀,及其對心靈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壞作用。哈金在序文中坦承最難寫的就是天安門事件的那一章,他視之為作家的道德責任。本書至今仍是書寫六四事件最具影響力的一本書,被譽為哈金最震撼也最令人著迷的不凡傑作。
「我要寫一部小說,把這些法西斯分子全寫進去。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最令中共抓狂的一本書。
直視令人窒息的中國共產黨社會以及知識分子所遭受無止盡的妥協和騙局。
從個人對國家的盲目忠誠,寫到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的凶暴,哈金筆下的萬堅就像卡夫卡小說裡的主角,愈努力愈挫敗。始於個人的瘋狂,結束於集體的瘋狂,《瘋狂》為魯迅筆下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中國,在廿世紀後半中共政權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不講道理,殺人如麻的凶暴行徑,留下最具影響力的批判和見證。
真是個瘋子!他讓我既想笑又想哭。
淚眼模糊。
「自從上了回來的火車,我就被一個可怕的幻象折磨著。我看見中國像一個老醜婆,衰朽又瘋狂,竟吞噬兒女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她貪得無厭,以前已吃掉許多小生命,現在又大嚼新血肉,將來肯定還要吃下去。我擺脫不了這個恐怖幻象,整天對自己說:「中國是吃自己的崽子的老母狗!」叫我怎能不毛骨悚然,叫我怎能不心驚肉跳!兩夜前的騷動還在我耳旁喧囂不止,我怕我就要瘋了。」
「天安門事件不僅僅使我們覺醒,也讓我們從此了斷了與國家的合同。
在更深的層次中,《瘋狂》寫的是這種民族的創傷和整個一代人的反叛。」
——哈金,新版序
繁體中文二十週年紀念新版。香港知名詩人黃燦然翻譯。
特別收錄新版作者序
國際好評
哈金將平凡的生活變成猶如黃金般……令人難以忘懷……充滿痛苦……一本值得被銘記的不朽作品。——《華盛頓郵報》
哈金對於他筆下的角色的同理心,與他不給予角色一絲喘息空間的態度相得益彰。閱讀他的作品彷彿墜入愛河:你會感受到焦慮、深刻的自我意識,以及產生一種針對世界的不愉快的敏銳感覺——但不知為何,這反而成為一種樂趣……就像是遇到最優秀的寫實主義作家,哈金將最強大的情感力量滲透進最樸實的文句中。——《紐約客》
一部極具智慧的傑作。《瘋狂》尖銳、批判性強,但又融合了哈金質樸的散文風格,替這位偉大作家豐富著作錦上添花。——《舊金山紀事報》
一部繼承了契訶夫及川端康成最高傳統的文學傑作,充滿了令人心痛的純粹。——《休士頓紀事報》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瘋狂(二十週年紀念新版)的圖書 |
 |
瘋狂(二十週年紀念新版) 作者:哈金 / 譯者:黃燦然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1-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8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6 |
美國文學 |
$ 300 |
文學作品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美國現代文學 |
$ 316 |
英美文學 |
$ 316 |
文學小說 |
$ 316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40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瘋狂(二十週年紀念新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哈金(Ha Jin)
本名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五年。在校主攻英美文學,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4年獲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1985年,赴美留學,並於1992年獲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學位。2014年獲選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終身院士。現任教於美國波士頓大學。
著有三本詩集:《沉默之間》(Between Silence)、《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s)和《殘骸》(Wreckage)。論文集《在他鄉寫作》(The Writer as Migrant)。2011年起在臺灣陸續出版中文詩集包括《錯過的時光》、《另一個空間》、《路上的家園》。
另外有四本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新郎》、《好兵》,和《落地》。
九部長篇小說:《池塘》、《等待》、《戰廢品》、《瘋狂》、《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背叛指南》、《折騰到底》、《放歌》。
短篇小說集《好兵》獲得1997年「美國筆會/海明威獎」。《新郎》一書獲得兩獎項:亞裔美國文學獎,及The Townsend Prize小說獎。長篇小說《等待》獲得了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和2000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為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美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並入圍了普立茲文學獎。該書迄今已譯成三十多國語言出版。《戰廢品》則入選2004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入圍2005年普立茲獎。
譯者簡介
黃燦然
1963年生於福建泉州,1990年開始為香港《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著有詩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靈魂》、《奇跡集》等;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和《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專欄結集《格拉斯的煙斗》等,譯有《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卡瓦菲斯詩集》、《巴列霍詩選》、《聶魯達詩選》;蘇珊.桑塔格《關於他人的痛苦》、《論攝影》、《同時》等;卡爾維諾《為什麼讀經典》(合譯)、《新千年文學備忘錄》;曼德爾施塔姆《曼德爾施塔姆隨筆選》(合譯)、J. M. 庫切《內心活動:文學評論集》、哈羅德.布魯姆《如何讀,為什麼讀》和哈金小說《瘋狂》等。
哈金(Ha Jin)
本名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五年。在校主攻英美文學,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4年獲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1985年,赴美留學,並於1992年獲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學位。2014年獲選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終身院士。現任教於美國波士頓大學。
著有三本詩集:《沉默之間》(Between Silence)、《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s)和《殘骸》(Wreckage)。論文集《在他鄉寫作》(The Writer as Migrant)。2011年起在臺灣陸續出版中文詩集包括《錯過的時光》、《另一個空間》、《路上的家園》。
另外有四本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新郎》、《好兵》,和《落地》。
九部長篇小說:《池塘》、《等待》、《戰廢品》、《瘋狂》、《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背叛指南》、《折騰到底》、《放歌》。
短篇小說集《好兵》獲得1997年「美國筆會/海明威獎」。《新郎》一書獲得兩獎項:亞裔美國文學獎,及The Townsend Prize小說獎。長篇小說《等待》獲得了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和2000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為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美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並入圍了普立茲文學獎。該書迄今已譯成三十多國語言出版。《戰廢品》則入選2004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入圍2005年普立茲獎。
譯者簡介
黃燦然
1963年生於福建泉州,1990年開始為香港《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著有詩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靈魂》、《奇跡集》等;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和《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專欄結集《格拉斯的煙斗》等,譯有《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卡瓦菲斯詩集》、《巴列霍詩選》、《聶魯達詩選》;蘇珊.桑塔格《關於他人的痛苦》、《論攝影》、《同時》等;卡爾維諾《為什麼讀經典》(合譯)、《新千年文學備忘錄》;曼德爾施塔姆《曼德爾施塔姆隨筆選》(合譯)、J. M. 庫切《內心活動:文學評論集》、哈羅德.布魯姆《如何讀,為什麼讀》和哈金小說《瘋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