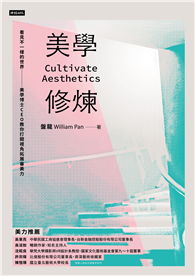盜墓筆記,本傳重啟;十年之後,再起征程!
從長白山帶回小哥之後,吳邪、胖子、悶油瓶這鐵三角三人組就跑到「雨村」去隱居了,日常種種田、做做小生意,釣釣魚……
歲月靜好,吳邪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逐漸從「邪帝」又變回「天真」,彷彿過往的冒險全部終結,他也把心事都放下,開始關注起柴米油鹽,然而新的事件,發生了!
事隔多年,吳邪再次收到三叔吳三省的消息,他一邊安心,三叔可能真的還好好活著,一邊又擔心,吳家傾三代人之力,難道都沒解決完問題?
不然三叔為何再度留下謎語要他去解,自己卻未曾現身?
三人組退隱之後,在「釣王篇」去了死水龍王廟,遇上身體鑲滿銅錢的凶猛神祕大魚,而這身穿鎧甲的魚,居然在地底水潭中再次出現了!這一切,究竟有什麼關聯?
‧‧由朱一龍主演,改編電視劇《重啟之極海聽雷》大受好評!‧‧
──
古有巨盜,以盜墓為業。
其徒有聽雨、聽風、聽雷、觀草色、觀泥痕等術。
雷響瞬間,洞穴及墓室共鳴,善聽雷者,可以此法聽出墓葬位置盜之。
──
「南京鼓樓東,北極閣氣象博物館221號儲物櫃,新年快樂。」
過年的時候,吳邪收到了失蹤已久的三叔發來的詭異簡訊,循著線索追查,卻發現三叔送了一塊地給他。
那塊地上廢棄的氣象站裡有個死人,身邊還藏著大量錄有雷聲的錄音帶。死者楊大廣是三叔的誰,研究氣象的嗎?到底誰會花十幾年時間,特地追著狂風暴雨去錄雷聲?
聽完所有錄音帶,吳邪對謎團仍百思不得其解;三叔若是沒死,為何不現身?直到那天,驟雨驚雷,他突然意識到,他在錄音帶裡,聽過一模一樣的雷聲!
雷聲有可能一樣嗎?還是說……雷聲裡蘊含的,其實是一段訊息?
吳邪跟胖子追查到楊大廣老家,卻看到了一座鑲嵌著無數青銅片的大山,底下是間廟。重複的雷聲、修仙的楊家、詭異的地底廟宇,以及聽雷的祕密……
撲朔迷離的謎團撲面而來,鐵三角的冒險旅程,也重新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