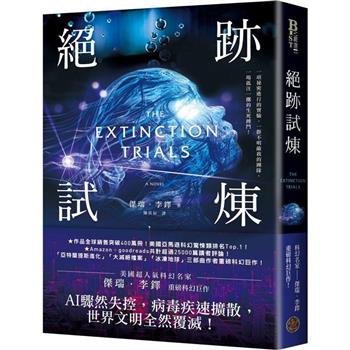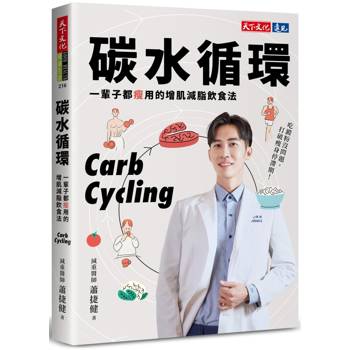我第一次見到父親是在刑事案件的法庭上。
父親以被告的身分站上證人台,兒子在後面的旁聽席瞪著他看。
這個場面實在稱不上感人的重逢,反而讓我充滿憤怒和厭惡,噁心想吐,胃液翻騰。
他被起訴的原因是強制猥褻繼女。
被害人當時還是個高中生。他趁著繼女睡覺時溜進她的房間,先綁住手腳、矇住眼睛,然後猥褻了她。這種惡行簡直齷齪到讓人不敢想像,聽檢察官朗讀起訴狀時,我的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
我竟然和這個男人有血緣關係。
真希望這不是真的。
──爸爸去哪裡了?
自從懂事以來,我不斷地追問這個殘酷的問題,讓媽媽非常頭痛。
有一段時間我很氣媽媽不肯回答問題,但那充其量只是叛逆期,大約在國中畢業的時候,我已經接受家裡只有兩個人的事實。
可是,在我大三那年的冬天,有刑警來找我媽媽。
這間公寓的隔音很差,我可以斷斷續續地聽見他們的對話。警方請我媽媽協助提供證據。嫌犯已經被逮捕。記錄顯示他會定期匯款給前妻……。我聽到這裡時不小心發出聲響,於是被趕了出去。
我本來覺得家裡經濟狀況很拮据,媽媽卻能供我讀大學。
每當我生日將近的時候,媽媽都會盛裝打扮出門。
等刑警走後,我問媽媽父親是不是被逮捕了,媽媽視線游移,然後點頭。當我得知警方在調查的是性侵案時,簡直驚愕到說不到話。
然後,二十一歲的我在法庭上看到了爸爸的樣貌,聽到了爸爸的聲音。
「起訴罪名及法條是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強制猥褻。請依照上述事實審理。」
法官先向被告說明緘默權,然後問道:
「檢察官朗讀的犯罪事實有哪裡不正確嗎?」
「我……」
父親聲音顫抖,我的雙手也在顫抖。
「我沒做過那種事。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他主張無罪的聲音空虛地迴盪在法庭裡。
*
我有時會突然想起大學時代的事。
譬如在家庭餐廳打工時的對話。
──宇久井,你知道烏鴉悖論嗎?
讀過心理系的女員工前輩每到休息時間就會和我分享她的知識和雜學,並且愉快地觀察我的反應。
我搖頭說不知道。
──「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對偶是什麼?
我回想著大學考試的內容,回答「不是黑色的東西都不是烏鴉」。如果是現在的我,可能會先問「對偶是什麼意思?」。
──你看,很奇妙吧?
我雖然不明白,還是隨口附和「是啊」。
──不用驗證烏鴉就可以證明「所有烏鴉都是黑色」這個命題,只要驗證世上所有不是黑色的東西,一樣能得出答案。
休息室裡有很多不是黑色的東西,其中並沒有烏鴉。
──這就是烏鴉悖論。
聽完前輩這番照本宣科的說明,我還是不明白這個悖論的矛盾之處在哪裡。
所謂「不是黑色的東西」太籠統了,就算做出明確定義,也不可能實際驗證所有符合這定義的東西……或許這就是重點吧。
不過,我對「烏鴉悖論」一詞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話題結束不是因為我表示聽懂了。
而是因為店長指出「對了,聽說有人在關西抓到白色的烏鴉呢」。我上網搜尋,很快就找到了報導,還發現其他地方也有人抓到。
我們看著白色烏鴉的照片討論得十分熱烈,前輩不悅地噘著嘴離開休息室,臨走前還說了一句神祕的宣言:「下次再找你做催眠術的實驗,先做好心理準備吧。」
如今我偶爾還是會想起那件事,不是因為我打工的地方發生過什麼大事,也不是因為我偷偷喜歡過那位前輩。
是因為我也成了黑色烏鴉的其中一員嗎?
又或者……
靠著皮革椅背,閉著眼睛。
我很喜歡在安靜的法庭裡等人進來的這段時間。
第一個走進法庭的會是誰?最後一個離開法庭的又會是誰?法院書記官這個職業,法律人士和旁聽迷當然知道,沒聽過的人想必也不少。
書記官的法袍是全黑的。
庭審開始前幾十分鐘,書記官才會打開門,在那之前法庭都是緊閉的。書記官會先帶著案件記錄和筆記型電腦從專用通道進入法庭,打開電燈和開庭燈,再打開旁聽席的門,然後準備器材,這樣才算完成了開庭準備。
接著我可以休息一下,但還是要豎起耳朵。
提著包巾的上出副檢事慢慢地走進來。我在座位上向他鞠躬。他的包巾裡裝著等一下要審理的案件的起訴書,以及預定提出的證據。有很多檢察官喜歡使用包巾,聽說這東西比外表看起來更好用。
上出武志坐在檢察官席,一邊用手帕擦汗,一邊對我說:
「你老是一臉想睡的模樣呢,樹鶯書記官。」
「上出先生今天還是一樣精神飽滿哪。」
因為我叫宇久井傑(Ugui Suguru),所以他叫我「樹鶯」(Uguisu)。轉得太硬了。
「外面熱得要命,我才走幾步路就滿身大汗。」
「您辛苦了。」
「這套法袍也很折磨人,應該響應『清涼商務』做成短袖款式才對。」
上出拉著開了兩顆扣子的襯衫衣襟鼓動搧風。隔著襯衫也能看出他的體格相當結實。
「一定會有人批評短袖不夠莊重。」
「中暑昏倒不是更麻煩嗎?」
「既然這樣,乾脆讓人在法袍底下全裸。」
「哈哈,那是暴露狂吧。」
上出豪邁地大笑。他五年前和我一樣是法院書記官,後來通過了副檢事考試──不用經過司法考試就能當上檢察官的特考──而進入檢察廳。很少有人像他這樣了解法院和檢察廳兩方的運作方式。
他的年紀超過四十五,比我大了快要兩輪。
「我一穿上法袍就會想到烏鴉在夏天一定很痛苦。」
「喔喔,這身打扮確實很像烏鴉,不過我都稱之為垃圾袋。」
法袍的材質是聚酯纖維,造型類似有袖子的斗篷,扣上前面的鈕扣就能嚴嚴實實地從領口遮到腳踝,確實很像套著黑色垃圾袋。
「這可是神聖的制服呢。」
「我倒覺得烏鴉也差不多。」
「因為烏鴉自古以來都被視為神明的使者嘛。」
「所以法官是神囉?」
「法官也要穿法袍就是了。」
「這是烏鴉社會的階級制度吧。」
有旁聽者進來了,所以我們不再隔著桌子聊天。總務課事先跟我說過,今天會有十位左右的更生保護機構志工來見習。憲法規定了審判公開的原則,因此法院不能拒絕旁聽。
我看看時間,離開庭大約還有十分鐘。上出今天來得很早,我一邊想著他剛才的閒聊大概是用來暖場的,一邊整理手邊的文件,他就走過來說:
「對了,宇久井書記官。」
「怎麼突然這麼嚴肅?」
他低聲說「關於今天的案件……」。
「是順手牽羊的竊盜案吧。」
我看著起訴書說道。正確說來,罪名還要再嚴重一點。
「烏間先生說過什麼嗎?」
上出提起了負責本案的法官名字──烏間信司。
「什麼?」
「像是起訴事實,或是被告的事。」
起訴書提供了兩條資訊,一條是被告的身分,譬如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戶籍、職業等等,另一條則是審理的內容,稱為起訴事實。
換個角度來說,起訴書只寫了這兩條資訊。
要等到審判期日,也就是法院開庭審理之後,法官才會知道被告被指控為罪犯的理由以及案發經過,所以在開庭之前,常看新聞的一般民眾可能都比法官更清楚案件內容。
「法官連證據都還沒看到,還不到產生疑問的時候啦。」
法官在審理過程中獲得的認知叫作「心證」。審判應該只依據心證來判斷控辯雙方的主張是否合理。
「那位順手牽羊大嬸之前也在南陽地方法院被判過有罪。」
「當時也是烏間庭長審理的嗎?」
「不是他。不過……」
上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像是在擔心什麼。
「難得看到您這麼不知所措。」
他口中的順手牽羊大嬸──仁保雅子──大約在一個月前遭到起訴。
起訴書被受理之後不會立刻開庭審理。起訴後,書記官要和相關人士聯絡協調,檢察官要整理準備提交的證據,辯護律師要和被告討論辯護的方向,然後才是第一次開庭。
案件開始審理之前,法官只能從起訴書中獲得案件的資訊。聽說有些法官為了排除預斷和偏見,連報紙都不會看。
「也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上出也很清楚刑事訴訟的原則,卻還是想先打聽法官的態度。
「……這個案子很棘手嗎?」
「只要烏鴉不啼叫,就不會有問題。」
「您可別去恐嚇庭長喔。」
有些人把烏間信司稱為「烏鴉」,理由恐怕不只是因為他的姓氏。法袍的顏色也是其中一點吧。
「當書記官真好,我緊張得都快要胃穿孔了。」
「我會幫忙祈禱不要旁生枝節的。」
「別只顧祈禱,你倒是幫我勸勸他啊。」
泊川律師不知何時已經坐在辯護人席了。我以前參加座談會時被一位資深律師批評過:法院職員應該秉持中立的原則,和檢察官太過親近不太妥當。
開庭時間快到了,我打內線電話到刑務官待命的房間,請他們把被告帶進法庭。
上出回到檢察官席,皺緊眉頭盯著文件。光從起訴書來看,我只覺得這是一件平凡無奇的竊案,他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烏鴉的啼叫……我好久沒聽到這句話了。
烏間在審案時動不動就會引起風波。書記官的工作是正確地記錄庭審過程,如果有反常的情況會很麻煩,這對我來說簡直是攸關生計的問題。
刑務官帶著被告走進來。
檢察官、律師、被告都到了,再來只要等法官到場就能開庭了。
但願這次庭審可以平安順利地結束。
【烏間法官審案很有戲劇性,但是負責訴訟指揮的法官怎麼能不顧規則呢?】
大約一個月前,某個知名的旁聽迷部落格貼出一篇文章,開頭寫了這麼一句話。作者沒有寫明他旁聽的是哪個案件,只節錄了烏間在審理時的一些發言,用批判的態度加以評論。
那篇文章鉅細靡遺地敘述了庭審的經過,作者想必費了不少心力查詢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規則的條文。
可是看到別人說烏間不顧刑事訴訟規則,以書記官身分和他一起開庭過好幾次的我實在難以苟同。
他是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找尋可走的小徑。
我覺得這樣描述更加貼切。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幻告的圖書 |
 |
幻告 出版社:尖端 出版日期:2024-03-07 規格:膠裝 / 單色 / 424頁 / 14.5cm×21cm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日本推理小說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日本推理/犯罪小說 |
$ 352 |
推理小說 |
$ 360 |
日本文學 |
$ 360 |
推理/驚悚小說 |
$ 36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幻告
張開眼的瞬間,他穿越到了五年前,法官宣判他父親有罪,罪名是猥褻妹妹的那一刻──
「我父親是無辜的嗎……?」
在超越時空的法庭爭取奇蹟。
前作《法庭遊戲》改編電影!律師、被告、死者 無法預測的三角謎團,由永瀨廉、杉咲花、北村匠海主演!何時才能,偵相大白?
‧日本「讀書Meter」最想讀的書排行榜第一名
(單行本部門 2022/5/4~2022/6/3期間統計)
‧書評家、書店店員大力推薦!
‧《法庭遊戲》作者最新作!
‧動人心弦的法律推理小說。
【主要角色】
宇久井傑 法院書記官
烏間信司 法官
千草藍 法官。傑大學時代的朋友
本橋宗二 上班族。傑大學時代的朋友
上出武志 檢察官
仁保雅子 偷竊慣犯
泊川佑志 仁保雅子的律師
篠原凜 竊盜案的被告
篠原佐穗 凜的母親
加納灯 篠原凜的律師
染谷隆久 傑的父親。正在刑務所服刑
【故事簡介】
擔任法院書記官的宇久井傑某天在法庭上昏倒,醒來時發現自己處於五年前父親被判有罪的那一場庭審。傑發覺父親可能是被冤枉的,為此一再穿越時空挖掘真相。
但是改變過去也使五年後的「現在」受到影響,傑失去了好友,還可能會面臨最壞的局面。
賭上未來穿越時空的傑最後會得到什麼樣的事實?
法律推理新星的最強力作!
作者簡介:
五十嵐律人
一九九○年出生於岩手縣。東北大學法學系畢業。
現任律師(Verybest法律事務所、第一東京律師協會)。
以《法庭遊戲》獲得第六十二屆梅菲斯特獎,成為作家。
著有《不可逆少年》、《原因において自由な物語》、《六法推理》、《真夜中法律事務所》。
章節試閱
我第一次見到父親是在刑事案件的法庭上。
父親以被告的身分站上證人台,兒子在後面的旁聽席瞪著他看。
這個場面實在稱不上感人的重逢,反而讓我充滿憤怒和厭惡,噁心想吐,胃液翻騰。
他被起訴的原因是強制猥褻繼女。
被害人當時還是個高中生。他趁著繼女睡覺時溜進她的房間,先綁住手腳、矇住眼睛,然後猥褻了她。這種惡行簡直齷齪到讓人不敢想像,聽檢察官朗讀起訴狀時,我的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
我竟然和這個男人有血緣關係。
真希望這不是真的。
──爸爸去哪裡了?
自從懂事以來,我不斷地追問這個殘酷的問題,讓媽媽非常...
父親以被告的身分站上證人台,兒子在後面的旁聽席瞪著他看。
這個場面實在稱不上感人的重逢,反而讓我充滿憤怒和厭惡,噁心想吐,胃液翻騰。
他被起訴的原因是強制猥褻繼女。
被害人當時還是個高中生。他趁著繼女睡覺時溜進她的房間,先綁住手腳、矇住眼睛,然後猥褻了她。這種惡行簡直齷齪到讓人不敢想像,聽檢察官朗讀起訴狀時,我的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
我竟然和這個男人有血緣關係。
真希望這不是真的。
──爸爸去哪裡了?
自從懂事以來,我不斷地追問這個殘酷的問題,讓媽媽非常...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