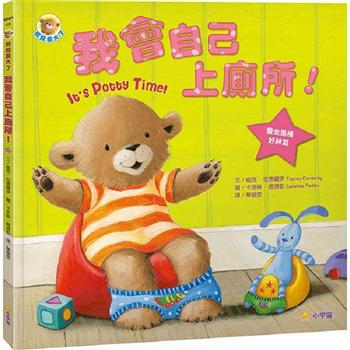●11萬粉絲引頸期待!耶魯大學高材生帶你一窺法國、日本、香港、美國不可言說的職場文化!
●圖文作家&Podcast主持人 Vito大叔、資深日本顧問 福澤喬、T1籃球大聯盟副會長 劉奕成 齊聲推薦
在法國,找工作時讓面試官一見鍾情,勝過擁有超完美履歷;
在日本,讀懂空氣是職場求生的必備技能;
在香港,加班加好加滿是日常,享受生活才是奢侈;
在美國,向上管理比展現實力更重要……
踏出巴黎高等商學院及耶魯大學校門後,作者Jeff C.一腳闖進外資金融圈的殘酷世界,遊走於法國、日本、香港、美國各地,見識到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也經歷了冷暖自知的人性考驗,深刻體悟到:路,不一定是人走出來的,也可能是野獸隨時會出沒的地方。人生處處是風險,置身詭譎多變的職場猶如野外求生,不能盲目地前進,唯有保持清醒,才能活到最後。
職場人生就像參加一場登高賽,跳脫舒適圈是成長必須付出的代價。從青春到世故,走過十年的探索之路,下一場未知的旅程才正要開始……
「我想將過去十年間發生的一切記錄下來,讓閱讀這些故事的人能夠體驗那些對我來說非常珍貴的瞬間:有歡笑、溫暖,也有寂寞,以及一點點的傷感。」—— Jeff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