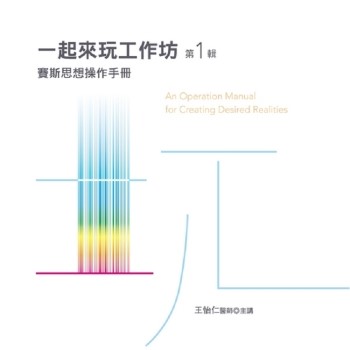第一章 等閒變卻故人心
-壹-
近來到了梅雨季,南方洪澇多發的時節,樓淵本該很忙,樓毓卻日日能在自己的丞相府裡瞧見他。
樓毓覺得納悶。
她坐在庭院裡的一大叢翅果連翹旁,細碎的白花如團團雲霞懸在頭頂搖搖欲墜,木盅裡兩隻蟋蟀正鬥得激烈,搏命廝殺。
「黑將軍,上──」樓毓拍腿,睜大眼睛看得起勁就喊了出來。
她再抬頭時,萬壽廊的拐角處顯露一片墨色的衣角,有人踏風而來。
她笑望著來人,問:「阿七,怎麼又有空來,你不忙嗎?」
樓淵步步走近,拎來兩罈子小酒,拔開木塞,繞過小石桌給樓毓滿上一杯。
「我過來看看你。」
偌大的丞相府裡,只有一個拿掃帚的老家僕從廊上經過,朝樓淵欠了欠身,又佝僂著背掃偏院去了。
花木深深,翠鳥停在樹梢頭吱吱叫,暖陽高照。
醇醇酒香撲鼻,樓毓伸出舌頭舔了舔,道:「你不忙著愁抗洪救災的事,過來看我?」
她狹長的眼角倏地往上一挑,立即警鈴大作:「莫不是──你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心中有愧?」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樓淵少年老成,冷峻的面容上恰到好處地鑲嵌著一雙冷清的眉眼,鋒利得像一柄剛出鞘的劍,泛著瑩潤又懾人的光。他手持青瓷杯,喝了口酒,一個攏袖抬手的動作,把情緒遮掩得滴水不漏。
「怎麼不說話,被我猜中了?」樓毓推開木盅,也不關心兩蟋蟀誰死誰活了,眼睛仔細盯著樓淵,想從他臉上看出一分端倪。
樓淵默不作聲。
樓毓瞧了他一會兒,覺得沒趣,問道:「阿七,你可知你長大後,變得最討人厭的一點是什麼嗎?」
樓淵眼潭無波無瀾。
樓毓兩隻魔爪襲上對方白玉臉龐,往旁邊一扯,強行揚起一個笑弧:「便是像現在這樣,將心思藏得深,連我竟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麼……」
「一點也不討喜了。」
樓毓常年習武,手握刀槍,指腹結了一層繭子,帶來粗糲又微涼的觸感。
樓淵拂開她的手:「我自幼便是如此不討喜。」
「非也。」樓毓搖頭,「你自幼便是個溫良如玉的小公子,長大後是個清朗俊俏的七公子,我可一直喜歡得緊。樓府上下那些人,欺你幼時羸弱,伶仃無依,當初虧待於你,那是他們眼瞎。」
杯中酒喝得不盡興,她端起罈子,猛灌了一口:「也就只有我樓毓,火眼金睛,識得良人。」
「阿毓,你如此放浪形骸,就不怕落人話柄嗎?」
樓毓大笑出聲,一拂袖,雙腳筆直搭上石桌,沒個正形:「在這相府裡,我是相爺,除了兩丫鬟、一老僕、一花匠、一廚子,就只剩些花花草草蟲魚鳥獸,它們還能去皇帝面前參我一本不成?」
樓淵道:「你活得太恣意了。」
他今日帶過來的是瓊液酒樓新推出的醉仙釀,後勁極大。樓毓囫圇吞咽了一壇,再被和煦的風一吹,額頭重重磕在他肩膀,醉醺醺道:「阿七,是你活得太壓抑了──」
樓淵心下一窒。
盅內的兩隻蟋蟀已經偃旗息鼓,兩敗俱傷,雙雙被咬死。
天剛入夜。
樓毓再醒來時,發現自己和衣躺在屋內的榻上。
兩旁的窗軒敞開,淅淅瀝瀝的斜雨飄進來,滋潤著兩盆鹿銜草。五月正是開花的季節,白瓣黃蕊,熱熱鬧鬧地擁擠在直直的莖稈上,被打溼的翠綠葉片反射出粼粼的冷光。
她呆呆望著某一處,不知在想什麼,坐了會兒醒神,才張口叫道:「人呢?人都哪兒去了?」又清了清嗓子,「大喵……小喵……快來伺候你們相爺寬衣就寢了……」
一陣倉促的腳步聲響起,兩個丫鬟端著熱水趕過來:「來了來了,爺,您酒還未醒,若頭暈就先躺著,別亂動。」
這相府上僅有的兩個婢女,是一對雙生子,姐妹倆長得如花似玉,清秀溫婉。獨獨名字有些難聽,大的叫大喵,小的叫小喵。
樓毓當初一聽就樂了:「有哪個不長心的爹娘會給自己的小嬌娃取這等小貓小狗的名字?」
大喵、小喵卻說:「我們爹爹說了,賤名好命。」
可見她們還挺滿意這名字,樓毓也就隨她們去了。
大喵擰乾熱氣騰騰的帕子,給樓毓擦了擦手,道:「爺,還不能就寢,宮裡紫容苑的冕公公捎來了口信,說寧夫人邀您去一趟。您拾掇拾掇,趕緊進宮吧。」
樓毓揉了揉眉心,心下反感,並不答應,反問:「樓淵何時走的?」
小喵細細說來:「您晌午喝醉了,在院子裡就走不動路,七公子陪您坐了許久。轉眼就到申時,樓府前來尋人,七公子把您抱回屋就隨他們走了,現在已經快戌時了……」
思量最近樓淵身上種種不尋常的跡象,樓毓自言自語:「最近可真怪,平日為家國民生忙得死去活來的七公子近來總往我府上跑,吃錯藥了不成?」
大喵掩嘴笑道:「京都幕良誰人不知,七公子與相爺您打小待在一處長大的,兄弟情深,他自然來相府來得頻繁些……」
樓毓玩味似的揣摩那四字,似笑非笑。
──兄弟情深嗎?
「爺,您不打算進宮了嗎?」大喵見樓毓遲遲沒有動靜,緊張地詢問。
樓毓懶洋洋地靠在榻上:「你差個人去回復寧夫人,就說外邊雨大,相爺不想溼了鞋面。」
大喵筆直跪下,勸道:「可……可寧夫人好歹是您的生母,您此番作為,傳出去了,會被那些愛嚼舌根的文人所恥笑的。」
「那便由他們笑去吧,爺從來不要什麼清名。」
兩個丫鬟再要勸,齊刷刷跪在榻前。
樓毓閉目小憩,只當什麼也不曾看見,不曾聽見。
又恢復了一室的寂靜,窗外雨滴敲打瓦礫的聲響越發清越動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
半炷香的時間過去,樓毓伸了個懶腰坐起,詫異地望向兩婢:「你們怎麼還跪在這兒?」
兩婢心中叫苦不迭,主子不叫起,她們便只能跪著。
大喵不知自己何處得罪於她。
這位年輕的相爺,雖不太講究規矩,卻也並不似表面那樣面善和易相處。
南詹建國三百餘年,樓毓是最年輕的丞相。
樓毓是上過戰場、殺過敵的。葉岐來犯時,鐵騎長槍,她於鵝毛大雪中橫掃千軍,把侵略者趕至氓水之濱。那些讓人聽了熱血沸騰的英勇事蹟,如今還在市井之中流傳。驚堂木一拍,還是說書人口中的佳話。
氓山一役,樓毓大勝而歸。
再加上她那位傾國傾城的生母寧夫人,在皇帝身旁吹一吹枕邊風,樓毓便由此封了相,賜了府邸。
可她脾性怪,讓人摸不透,府中沒人,也不愛和世家弟子結交。
兩婢貼身伺候,除了樓府的七公子樓淵,從不曾見相爺與誰親近過。
今兒就更怪,明明白天七公子來過,相爺心情應該不錯才對,卻料想錯了。大喵、小喵頭垂得更低。
「都起來吧,爺要進宮了。」
樓毓手指拂上半邊冰冷的鐵面具,自個兒站起來對著面銅鏡整了整衣衫,拿起牆角的竹骨傘出門。
她獨自一人沿著青籬巷往外走,長長的街道,夜雨裡兩旁燭火不熄。茶樓酒肆裡隱約傳出眾人的談笑,琴瑟聲飄蕩而出。
不緊不慢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南坊街的盡頭,便是厚重的宮門。
樓毓還未向守門的將士亮出腰牌,對方便已認出她。在京都幕良,那半邊鐵面具便是最好的身份證明。
他們恭恭敬敬地行禮,替她開門。
「相爺慢走。」
樓毓步調放慢,越靠近樓寧居住的紫容苑,便越慢。
在前院遊廊上徘徊的劉冕看見她的身影,著急地小跑過來:「哎喲,我的相爺,您怎麼才來?夫人都等您半晌了。」
樓毓道:「深夜進入後宮,不符合規矩,爺當然得好好思量,來還是不來。」
劉冕面上陪著假笑,卻不敢揭穿她。
宮裡無人不知,寧夫人極得孝熙帝寵愛,寧夫人說住在宮中不習慣,時不時掛念「兒子」,一早央求著皇帝給了樓毓特權,准許她隨時入宮。
說起樓毓的生母樓寧,也是南詹國的一位傳奇人物。
她本是第一世家樓家的養女,雖然沒有血統上的尊貴,但好歹也占著樓府三小姐的名分。當年世家間聯姻,樓寧被家中長輩安排遠嫁臨廣蘇家,做了蘇清讓的妻,生下樓毓。後來卻被蘇家拋棄,母女倆在民間流浪了五年,樓寧才帶著樓毓復又投奔娘家,回到京都幕良。
原本這婦人一輩子也就該如此耗盡了,可誰叫她生了一張禍國妖民的臉,被孝熙帝一眼相中。
孝熙帝約莫從未見過樓寧那樣的美人,一旦見過,便寤寐思服,輾轉反側,難以放下。
也不管美人已經嫁過人,美人的「兒子」都會耍長槍了,硬是一頂花轎把美人抬進了後宮。
樓寧二嫁進宮時,樓毓說:「娘,若您不願進宮……」
樓寧巧笑倩兮:「若我不願意,你待如何?」
樓毓放下長槍,在她膝前跪下,額頭點地:「若您不願意,孩兒萬死,也保您周全。」
清脆動人的笑聲在淒厲的秋風中如燭火被吹熄,像臨廣鄉笛荒蕪的腔調。
「萬死嗎?」樓寧喃喃,頭一次溫柔了神色,掌心撫上她的髮頂,「可我的毓兒,你只有一條命啊。」
樓毓心中一緊,雙手握成了拳頭。
「相爺……相爺……」劉冕打斷樓毓的回憶,「您趕快隨著小婢子走吧。」
樓毓跟在兩個宮女身後,走過曲曲折折的小道,樓寧的寢宮就在眼前。
兩側的月見草在微風夜雨中凋零,綿長悠揚的小調從前方飄來,樓毓停住腳步,駐足仔細聽了聽。
「相爺怎麼了?」宮女回過身詢問。
樓毓長身而立,撐傘站在雨中,翩翩的月白廣袖被吹翻淋溼,她問:「這是什麼聲音?」
「是寧夫人在唱歌。」
「她平素也這麼唱嗎?」
她竟然在深宮之中,肆無忌憚地哼著臨廣的民謠。是興之所至,還是懷念故人?倘若有心人惡意揣測,免不了又會惹來一身麻煩。
樓毓走得越近,那歌聲越清晰,攪渾著天青色的朦朧夜雨和白茫茫的薄霧。潺潺流水般平常的曲子,卻透著道不清的嫵媚和淒婉,無端聽得人心頭發堵。
樓毓順著那扇窗望過去,看見了倚在窗邊的樓寧。
她穿著件紅豔的單襦,是雨霧天灰濛濛景色中的一抹亮麗,秀髮未綰,如長瀑瀉下,披在肩頭,長及腳踝。一顰一蹙,都是風情,浩蕩的天與地都淪為了她的背景。
當真像存世的妖精。
樓毓踏進寢殿,跪下行禮:「拜見母親。」
樓寧摒退了左右的宮人,側臥在貴妃榻上,招呼著樓毓上前:「過來。」
燈燭照亮樓毓溼答答的衣襬,她每往前走一步,就留下一個漆黑的腳印。樓寧見此笑話道:「你這麼大人了,撐著傘還能把自個兒淋成這樣……」
纖長無骨的手指撫摸上樓毓蒼白的唇角。
「毓兒,把面具摘了,讓娘好好看看你。」
樓毓雙手一滯,順從又緩慢地摘掉半邊鐵面具,不過一瞬,便迎來響亮的一巴掌。
「啪!」
狠狠的一聲脆響。
樓毓的臉被打偏,左邊臉頰高高腫起,口中嘗到了血腥味。
「怎麼這麼不長記性,我是怎麼教你的?」
樓毓屈辱地低下頭,壓抑住情緒,複述道:「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面前是何人,皆不可摘下面具。」
「這次可記住了?」樓寧問。
「記住了。」樓毓咬牙道。
「不要信從任何人,不要依靠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哪怕是娘……也不可以嗎?」
「不可以。」
樓毓閉上雙眼,再睜開時眸中已無波瀾:「是,孩兒謹記。」
樓寧兩指捏住她的下巴,拿著燭臺湊近,明晃的火光灼熱無比,似下一刻,就要將人的眼珠子焚燒掉。
「你這張臉,像極了我,倘若不戴著半張面具遮一遮,女扮男裝騙得過誰?誰會信你是個男子?」
「不過,可惜了──」樓寧雪白的容顏上,梅花綻放般盛開出一點妖冶的笑,「即便我幫你扮成個男兒,你父親也不要你,你還得跟著我姓樓。」
樓毓眼中瞬息充血,通紅一片,好似被搖曳的火光逼出了淚。她匍匐在榻沿上,久久不曾動彈。
「恨嗎?」樓寧問。
「你若恨,今後便不要給任何人負你的機會。」
那扇梨花木門緊緊合上,樓毓呼吸到外面冷清的空氣,如同劫後餘生。
她逃似的走了,甚至一個踉蹌,差點左腿絆住右腿摔了一跤。
樓毓每一次從紫容苑出來,都如此狼狽。她牽掛樓寧,卻又怕見到樓寧。這個生她養她的女人,美麗而危險,時常會讓樓毓感到膽戰心驚。
樓毓本能地想要靠近她,卻又每一次被逼得不得不逃開。
小宮女在身後追:「相爺,相爺,您的傘忘了拿……」
樓毓接過竹骨傘,身後又響起熟悉的鄉音,樓寧在唱:「二十年風華歲月招搖過,到頭來,朝朝暮暮思郎君。金風玉露一相逢,不解相思意……」
漫天大雨,那歌聲滲透在每一滴雨中,敲打在心坎上,彷彿要讓人把心也全陷進去。
頭頂灰茫,雲海翻滾萬里。
-貳-
樓毓跌跌撞撞走了一路,到後來,竟在深宮裡迷失了方向,不知走到了哪一處園子。
斜前方走來幾個嬤嬤,樓毓正準備問一問路,卻聽見她們細細碎碎聊著天:「這些天咱們可有的忙了,繡貴人要親手幫二小姐置辦嫁妝,好大場面……」
「可不是,你也不看看二小姐嫁的是誰,幕良樓家七公子。百年世家,名望並不輸給帝王家……」
幾人聊得興起,一道聲音斜插進來。
「敢問一聲,你家二小姐要嫁的是誰?」樓毓突然冒出來,嚇得嬤嬤們一顫,她面上森冷的半邊面具,在寥寥夜火中更加顯得有幾分駭人。
「參見相爺。」
這幾個老嬤嬤是莊繡夫人入宮時自娘家帶來的家僕,她們口中的二小姐,便是莊繡夫人的妹妹,當朝太傅家的二女兒。
「莫非要我問第二遍?」見幾人不答話,樓毓陰惻惻地問。
老嬤嬤一哆嗦,悉數交代了清楚:「二小姐要嫁的,是樓府的七公子,樓淵。」
幾人只見面前白影一閃,如同鬼魅飄過,眨眼間丞相大人已經不見了蹤影。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樓毓棄了竹骨傘,朝著樓府飛奔而去的路上,想起樓淵近日來的種種異常行為,還有樓寧今日突然召她進宮,恐怕也是早就知曉了樓淵要娶親的事。
「你若恨,今後便不要給任何人負你的機會。」樓毓想,樓寧口中所說的,原來是這個意思。
她飛簷走壁,後來又不知在馬廄裡順手牽走了誰家的馬,狂奔而去。
趕到樓府,只花了片刻工夫。
樓毓從馬上飛身而下,渾身溼透,滿載煞氣而來:「叫樓淵給我滾出來!」
家僕嚇得趕緊去通報,樓毓卻是一秒也等不及了,自己朝院內走去。她曾在這樓府生活過十餘年,對裡面的一草一木都再清楚不過,徑直朝東南角方向的偏殿而去。
樓府的占地面積極廣,曾兩度擴建,僅次於皇宮。這一路,卻被懸掛在廊簷下的大紅燈籠和綢緞刺痛了雙眼。
七公子與太傅之女婚事在即,樓府已經在佈置了。
事情瞞得這樣緊,還是──只有她一人被蒙在鼓裡?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雲水千重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97 |
華文羅曼史 |
$ 224 |
華文羅曼史 |
$ 252 |
中文書 |
$ 252 |
文學作品 |
$ 253 |
古代小說 |
$ 253 |
愛情文藝 |
$ 253 |
言情小說 |
$ 27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雲水千重
一漂江湖我沉浮
風雲江湖VS朝堂權謀│會撩.會寵.會護妻│女丞相VS詐死太子
橫掃各大閱讀網獲9.1、9.8好評!
網評5本必讀「女扮男裝」古言小說之一!
經典!值得熬夜品讀!
「即便你扮成男兒,你父親也不要你。」
「即便你幫他、護他,他也不要你,還是要娶別人。」
「恨嗎?」
「你若恨,今後便不要給任何人負你的機會。」
誰是風雪夜歸人?
那是一個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想要活下去,就得拋棄一切軟弱的、怯懦的東西,
把自己一層層包裹起來,在外面形成一個堅硬的殼,
才不至於被刺傷,被人一刀致命……。
一出生,即被家族拋棄,從小女扮男裝,金戈鐵馬身披麒麟甲保家衛國,獨身面對朝堂上的爾虞我詐,是世人眼中最心狠手辣的相爺。
她也曾懷抱少女夢想,只願與小竹馬執手偕老,死生契闊,可一顆真心在權利面前終被負……
直到她的新婚,遇上了這個男人,一而再再而三把他的真心交付到她的手上,只想索取她的真心,因為他知道她怕了,不能再承受任何的背叛。可是當本該屬於他的江山和權利再一次站在他的面前時,這次他真能真心不相負嗎?
人世之理,自然之理,天地之理。宇宙洪荒,萬世不竭。
朝代百年,史載萬千,皆爲虛話。
若得其理,便可見未現之事。
日月在天,江山爲證。
若世間紛繁,那我便讓這昭明之名再次響徹人間!
作者簡介:
靳山
大魚文化人氣大神,擅寫古言,以婉轉細膩的筆觸撰寫出賺人熱淚的故事情節。
著有《聲聲喜歡》、《江先生,請回答》等作品,深受廣大讀者們的喜愛。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等閒變卻故人心
-壹-
近來到了梅雨季,南方洪澇多發的時節,樓淵本該很忙,樓毓卻日日能在自己的丞相府裡瞧見他。
樓毓覺得納悶。
她坐在庭院裡的一大叢翅果連翹旁,細碎的白花如團團雲霞懸在頭頂搖搖欲墜,木盅裡兩隻蟋蟀正鬥得激烈,搏命廝殺。
「黑將軍,上──」樓毓拍腿,睜大眼睛看得起勁就喊了出來。
她再抬頭時,萬壽廊的拐角處顯露一片墨色的衣角,有人踏風而來。
她笑望著來人,問:「阿七,怎麼又有空來,你不忙嗎?」
樓淵步步走近,拎來兩罈子小酒,拔開木塞,繞過小石桌給樓毓滿上一杯。
「我過來...
-壹-
近來到了梅雨季,南方洪澇多發的時節,樓淵本該很忙,樓毓卻日日能在自己的丞相府裡瞧見他。
樓毓覺得納悶。
她坐在庭院裡的一大叢翅果連翹旁,細碎的白花如團團雲霞懸在頭頂搖搖欲墜,木盅裡兩隻蟋蟀正鬥得激烈,搏命廝殺。
「黑將軍,上──」樓毓拍腿,睜大眼睛看得起勁就喊了出來。
她再抬頭時,萬壽廊的拐角處顯露一片墨色的衣角,有人踏風而來。
她笑望著來人,問:「阿七,怎麼又有空來,你不忙嗎?」
樓淵步步走近,拎來兩罈子小酒,拔開木塞,繞過小石桌給樓毓滿上一杯。
「我過來...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前言
誰是風雪夜歸人
小時候跟著外公外婆搖著蒲扇看花鼓戲,對《女駙馬》的印象深刻。電腦的網易雲歌單裡仍有《女駙馬》的插曲,偶爾還會翻出來聽聽,「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我也曾赴過瓊林宴,我也曾打馬御街前……」特別喜歡這幾句。
戲裡面說的是女扮男裝的馮素珍進京趕考,偶中狀元,被皇帝強招為駙馬,我自小記得這個情節。後來看的小說和電視劇多了,漸漸發現女扮男裝實在算不上是個新鮮的哏,但是在《雲水千重》這個故事裡,我還是選擇了這一元素──女扮男裝的女主。
那是一個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誰是風雪夜歸人
小時候跟著外公外婆搖著蒲扇看花鼓戲,對《女駙馬》的印象深刻。電腦的網易雲歌單裡仍有《女駙馬》的插曲,偶爾還會翻出來聽聽,「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我也曾赴過瓊林宴,我也曾打馬御街前……」特別喜歡這幾句。
戲裡面說的是女扮男裝的馮素珍進京趕考,偶中狀元,被皇帝強招為駙馬,我自小記得這個情節。後來看的小說和電視劇多了,漸漸發現女扮男裝實在算不上是個新鮮的哏,但是在《雲水千重》這個故事裡,我還是選擇了這一元素──女扮男裝的女主。
那是一個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誰是風雪夜歸人
第一章 等閒變卻故人心
第二章 昨夜星辰昨夜風
第三章 春風不度玉門關
第四章 玲瓏骰子安紅豆
第五章 滿船清夢壓星河
第六章 何當共剪西窗燭
番外一 金風玉露一相逢
番外二 想得山莊長夏裡
第一章 等閒變卻故人心
第二章 昨夜星辰昨夜風
第三章 春風不度玉門關
第四章 玲瓏骰子安紅豆
第五章 滿船清夢壓星河
第六章 何當共剪西窗燭
番外一 金風玉露一相逢
番外二 想得山莊長夏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