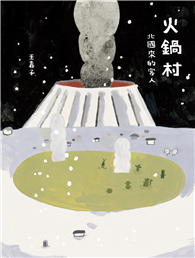跋
這邊與那邊
我對阿嬤最早的記憶,是在她家的客廳看著電視播放的《假面騎士》錄影帶。阿嬤坐在我旁邊,非常拘謹的。
每看一個單元,我都會轉頭問阿嬤:「在演什麼?」
她會試圖用國語告訴我一些聽起來也似懂非懂的話。例如要保護弱小的生命,要珍惜物品等等的。然後媽媽來接我了,媽媽會問起阿嬤我表現如何,她會說:「有乖。」
日後追憶,這段記憶若為真,那就是我幼稚園中班甚至更小的時候。
我們家住「這邊」,阿嬤與阿姨的家在「那邊」,這邊與那邊的距離,對小朋友來說也是走路可以到的距離。
那個時候,阿嬤還有頭髮,是常見的短髮燙捲,穿著針織背心、尼龍長褲。我記得她不常笑,但慈愛的感覺是確實的。那個時候,我還叫她阿嬤。
有時候我也會看見外公。大多是晚上,阿姨與舅舅們都在的時候。阿公因為一顆光亮的頭,以及總愛餵我吃冰淇淋,我稱他為冰淇淋阿公。我的印象裡,這樣的場合,散會的時候,他會跟著我們一起出來。告別後,騎著摩托車離開。
一兩年後,我上小學前,阿嬤出家了。記得我第一次被帶去探望她時,媽媽再三的提醒,阿嬤現在已經沒有頭髮了,以後也不可以叫阿嬤,要改叫師父了。
我們一家,因為父親工作的緣故搬去了新竹。「這邊」讓阿姨住了進去。而阿嬤與阿姨同住的房子,「那邊」成為新婚的小舅的新居。
好幾年的時間,逢年過節或是聚會,每當北上的時候,都是住在大舅的家中。我與兩位表妹小時候關係一直友好,若要問起我對全臺遊樂園的所有記憶,六福村也好、九族文化村也好,都是大舅帶我們去的。在臺北有個地方可以過夜,似乎代表著某種聯繫一直存在。
小舅是我心中最風趣而無距離的長輩,甚至沒有長輩的感覺。他的家,小時候的「那邊」,被他擺滿了各種模型,以及將一間房間打造成音響室。每回拜訪小舅,都會聽他介紹最新喜歡的專輯、電影,然後以高規格的影視播放給我們這些小孩子。我們會入迷的看,小舅自己也是,而他有時會被小舅媽揪出房間,回去大人們間的談話。
時移事遷,轉瞬間我已是少年。有回難得外公來到小舅家,留下了一張他與全部外孫的合照。那是我最後一張保留的,跟外公的合照,在「那邊」。
也許記錯了,但我記得,好像就是那回從小舅家離開,我在路上問了媽媽,到底為什麼外公不太常出現呢?他以前就沒有跟阿嬤住在一起嗎?我是在那晚,才知道家族的事。然後才漸漸漸漸地,知道師父的過往,以及要更久一點點,才知道更深的事。
拍下合照那晚的五六年後,外公過世了。
這個時候,我剛上大學,父親退休,我們全家又搬回了「這邊」。外公的死訊,據說是隔了一個禮拜才告知媽媽他們的。我參加了告別式,親身體驗自己在屋子以外,與他的關係是怎樣定義的。
後來,小舅搬走了,「那邊」的房子租給外人幾年。每回經過這裡,我都不免會抬頭看向窗戶。
大學畢業,退伍後,我去了法國。阿姨非常開心的把她律師事務所的法籍實習律師介紹給我認識。也是到了我要出國前,我與母親才知道她年輕時學過法文,而且在師大通過最高級的檢定的事。
在旅法的期間,師父與阿姨回到「那邊」。感覺像是回到了起點,卻註定成為她們的終點。
阿姨生病多年,師父逐漸年邁,搬進「那邊」的房子是她們那幾年難得愉快的事。回國的時候,阿姨會眼睛發亮的聽我跟妻子講關於法國的生活,像是我真的在某種程度上,為她實現了某種夢想。
時間繼續走著。
師父往生了,最後的時刻,無愧於一個修行之人。
一年多以後,阿姨也往生了。前一晚,我們才去醫院探望過。
「那邊」的房子再次租出去了。
我旅外多年,挫敗回國,與妻子流轉了一年。最後竟因緣既會,恰好房客退租,換成我們住進,「那邊」成為「這邊」,父母住的「這邊」則成了「那邊」。不變的是,三十多年過後,「這邊」與「那邊」時常相互探望,一起遛狗、吃飯,交換物品。
住進後半年,我出了第一本書《禮物》。我送走了我的愛犬旺,又迎接了皮蕾兩名愛犬。作品累積著寫,人生也一直前行。
《金月蓮》的撰寫中,我與許多回憶的時間共存。我所在的空間,他們都在此存在過。
這本小說教會了我,原來需要有那麼巨大的,幾乎全然虛構的意志,才能容納起生命中經歷起的真實情感。
在此,特別感謝母親。是她守護的多年的家族記憶而不佚失,又給予我如此溫暖的家庭情感。寫作此書,很大一部分,是以自己的方式守護著她珍惜的記憶,以及她記憶的姿態。
這記憶的姿態,把一切連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