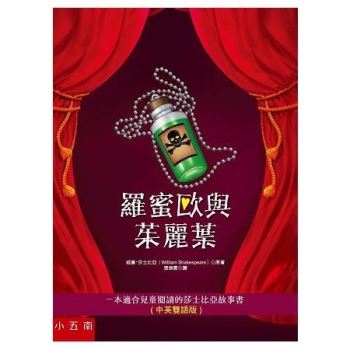第二章 兩國互市
馬車內,春桃用團扇輕輕給白卿言搧著風,低聲說:「瞧著高將軍像是大好了,大姑娘也能放心了。」
「嗯……」白卿言笑著應聲,「等錦繡回來瞧見高將軍,一定會高興的!」
「只可惜,二爺再也回不來了。」春枝低沉聲說了這麼一句,又反應過來怕惹白卿言傷心,轉頭撩開車窗輕紗朝外面瞧去,「大姑娘,您瞧……這麼熱的天,咱們大都城還這麼熱鬧人來人往的,這都是大姑娘治理有方的緣故。」
「我們春枝也學會拍馬屁了!」白卿言雖然這麼說著,視線也難免從春枝挑開的狹窄窗縫朝大街上的熙攘人群望去。
陡然,一個梳著大周男子髮髻,頭戴玉冠的男子從馬車旁走過,白卿言眸子瞇了起來……
薩爾可汗?!
「停車!」白卿言臉上笑容一沉。
「魏忠!」
魏忠應聲,連忙命車夫勒住韁繩一躍下了馬車,走至馬車車窗前:「大姑娘……」
白卿言挑開窗簾,低聲同魏忠說了幾句,魏忠立刻應聲:「是!大姑娘放心!」
白卿言將車窗放下,魏忠恭送馬車離開之後,也跟著離開。
「大姑娘……怎麼了這是?」春桃明顯瞧出自家大姑娘的神情不對,滿目的肅殺之氣。
她著實是沒有想到,薩爾可汗竟然已經混到了大都城……
南疆那邊兒有阿琦和阿瑜、錦繡他們,絕不可能讓薩爾可汗過來,那麼……就是薩爾可汗發現了那條錦桐發現的河,從那裡繞過來的。
白卿言手指有一下沒一下敲著案桌,同外面的馬夫道:「將馬車駕到暗巷。」
很快,馬夫將車駕到了暗巷。
「白家暗衛何在?」白卿言出聲。
很快,只見馬車窗簾晃動,幾道身影已經跪在馬車外:「大姑娘請吩咐!」
「星辰去了南疆,如今你們誰領隊?」白卿言抬手將馬車窗簾挑開一條縫隙。
「屬下尾宿!」
白卿言看著尾宿道:「帶一半人去追上魏公公,若是魏公公捉拿之人反抗,不必留命,就地斬殺!另一半人去皇夫的皇陵看看有沒有什麼異常。」
「是!」
「再派一個人立刻趕去韓城王府,讓韓城王即刻出發……告訴他防禦沿海一帶,不止要防東夷國,還要防著天鳳國從沿海進入!」
白卿言放下車窗簾子,這才同馬夫道:「回宮吧!」
馬車重新動了起來,春桃和春枝兩人乖巧坐於白卿言身旁不吭聲,不打擾白卿言垂眸靜思。
不動聲色來了大都城,這可真是……神通廣大啊!白卿言手心收緊,如今大周和燕國兩國賭國在即,天鳳國國君卻出現在大周的都城,薩爾可汗……是想做什麼呢?
白卿言回宮之後,先是派人快馬給遠在韓城的秦朗送了一封信,隨信還附上之前白錦桐送回來的地圖,讓秦朗防備一二,又給在南疆的弟弟妹妹們寫了一封信,將薩爾可汗到了大都城的事情告知弟弟妹妹們,讓他們也有一個準備。
在白卿言批閱奏摺之時,魏忠已經處理完薩爾可汗的事情,回到了宮中向白卿言覆命:「包括薩爾可汗在內的一行十三人,一個不漏全部投入大獄,不過瞧著薩爾可汗也未曾反抗的樣子,恐怕用不了多久,便會自行將身分抖出來求見陛下。」
魏忠的話音剛落,這邊兒小太監就來報,說是京兆尹求見。
白卿言唇角勾起輕笑一聲,道:「這不就已經著急將身分抖出來了!」
魏忠俯首:「陛下要宣嗎?」
「宣吧!」白卿言將摺子合上,示意春桃再拿一本摺子過來。
跪在白卿言身側的春桃連忙展開摺子送到白卿言的面前,規規矩矩跪在一側不吭聲。
京兆尹一進來,行大禮後道:「陛下,今日微臣奉魏公公之命抓入牢中之人,稱自己是天鳳國的國君,和陛下還是舊相識,將此物交給了微臣,說陛下一看便明白,微臣這才斗膽進宮面見陛下!」說著,京兆尹將玉蟬舉過頭頂。
魏忠瞧了眼還在垂眸批閱奏摺的白卿言,拎著衣裳下擺走至京兆尹的面前,接過玉蟬遞到白卿言的面前:「陛下……」
白卿言最後一字落筆,隨手將奏摺擱在一旁,視線落在魏忠手中的玉蟬上,這才將玉筆也擱置在硯臺上,接過玉蟬拿在手中仔細瞧了瞧,問魏忠說:「魏忠你抓人的時候被瞧見了?」
「老奴並未出面,確信並未被人瞧見。」魏忠連忙回道。
白卿言將玉蟬靠近案桌上的琉璃燈盞,湊近了些想仔細瞧著那玉蟬內裡的紋路,可這玉蟬通透的一如慕容衍贈她的那枚玉蟬般,通透的無半點雜質。
春桃瞧見這枚玉蟬,睜大了眼……
這玉蟬不是姑爺的嗎?怎麼會在什麼天鳳國國君薩爾可汗的手中?
他們家姑爺不是燕國的九王爺嗎?怎麼又冒出來一個天鳳國國君?
春桃滿肚子的官司,見白卿言看著玉蟬的認真模樣也未曾開口詢問。
白卿言確定這玉蟬便是薩爾可汗手中的那枚玉蟬之後,便問:「給你這枚玉蟬的人,說了讓你將此物交給朕之外,還說什麼了?」
京兆尹也是個聰明人,聽白卿言如此問,便確定來的果真是天鳳國的國君,便忙道:「回陛下,天鳳國國君說是想要求見陛下!」
她凝視著手中這枚玉蟬,同魏忠說:「魏忠,你隨京兆尹親自去一趟大獄,將這天鳳國國君迎出來,先讓他住進驛館,晾他一陣子……然後,派人將他們一行人看管好,不論有什麼異常舉動記得來報。」
「是!」魏忠領命,同京兆尹一同離去。
白卿言擺了擺手,春桃會意帶著春枝也退了出去。
大殿內只剩白卿言一人,她將一直隨身攜帶的玉蟬拿了出來,將兩枚玉蟬並列放在燈下,湊近仔細瞧著。
兩枚玉蟬幾乎一模一樣……
雖然,大周朝臣聽說玉蟬的故事,都覺得是無稽傳言。
甚至,當初白卿言同李之節說過,這玉蟬時光回溯之說,乃是當初那個沒有子嗣的天鳳國王后為了穩住政權的說辭,可……白卿言自己卻是實實在在重生之人。
她右手握著慕容衍贈她的玉蟬,只見那玉蟬在燭火映照之下,周身有瑩瑩閃爍的細碎金光,她眉頭一緊,湊近了些卻什麼都沒有了。
白卿言當初重生的時候,可沒有見過薩爾可汗手中拿著的這枚玉蟬。
她嘗試將兩枚玉蟬合併在一起,卻也沒有任何異象發生。
白卿言來來回回將兩枚玉蟬擺弄了半個時辰,突然醒過神來,覺得自己魔障了。
她竟然……想要找到玉蟬讓時光回溯的竅門。
這種事情可遇而不可求,她能重生回來已經是上天垂憐白家,她不該奢求更多。
若是真的如同那個傳說一般,每一次時光回溯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如今她的任何一個親人都不是她能夠捨棄的。
「大姑娘,暗衛尾宿前來覆命。」尾宿的聲音從大殿一側傳來。
白卿言視線瞧向圓柱之後的黑影:「說……」
「皇夫的陵墓安然無恙,屬下已派人守住驛館,一隻蒼蠅也不會放出來。」
「好,辛苦了……去吧!」
燈影晃動之後,大殿之中又只剩下白卿言一人。她將慕容衍贈的玉蟬放回荷包,又隨手將薩爾可汗的玉蟬擱在桌几一角,穩住心神拿過奏摺批閱。
魏忠將薩爾可汗一行人安頓在驛館之後,天已經黑了。
薩爾可汗坐在主位上,手緊緊攥著座椅扶手,薄唇緊抿著,神色晦暗難測,他沒想到白卿言不但沒有見他,瞧門口這守衛的架勢算是將他給軟禁了吧?
「魏公公……勞煩您,給大周皇帝帶一句話!」薩爾可汗抬頭,偏褐色的眸子宛若一潭幽水,勾了勾唇角道,「我這次親自來大都城,為的……是向大周示好,有意同大周結秦晉之好,還請大周皇帝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魏忠還是那副笑盈盈的模樣,頷首道:「天鳳國國君放心,這話……老奴一定會帶給陛下!自然了……老奴也要多嘴問天鳳國國君一句,既然是來示好求和,為何不正正經經等兩國互通國書之後,定下入大周的時間,再按照約定時間遣使前來?反而要用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徑,難免會讓人懷疑。」
「國書已經遞交大周,之所以提前過來,是因為……對大周皇帝思念甚深啊!」薩爾可汗這句話讓人分辨不出真假,目光冷靜又從容。
「這話,天鳳國國君需要老奴帶給陛下嗎?」魏忠問。
薩爾可汗笑著頷首:「那便有勞魏公公了。」
魏忠對薩爾可汗頷首,隨後退出正廳。
魏忠一走,薩爾可汗臉上再無笑意,皺眉轉而看向坐在他下首位置,一位穿著黑袍的銀髮老者:「大巫,你確定這另一枚玉蟬就在大周皇宮內?」
「我王……屬下以項上人頭擔保,這玉蟬絕不在大周皇夫陵寢。若是不在皇夫陵寢又能在哪裡呢?」天鳳國大巫聲線十分醇厚,徐徐說話,讓人覺得十分有說服力,「那玉蟬曾經是那位皇夫隨身攜帶的愛物,難道大周皇帝不會留下做一個念想?即便是當初隨那位皇夫一同下葬了,可……既然這位大周皇帝聽說了玉蟬的傳說,難道不會心動……派人將玉蟬取出來?」
薩爾可汗眉頭緊皺,想起白卿言過往的行事風格,眉目間的不悅緩緩舒展開來。
「我王不要忘了,當年的南疆之戰,大周皇帝的祖父、父親、叔父和大半弟弟們都折損在南疆,得到了玉蟬之後,她難道不會想方設法時光回溯,去扭轉戰局?”大巫起身恭敬朝薩爾可汗一拜,“如今我王已經將母玉蟬送到大周皇帝手中,她手中若有公玉蟬,自然會嘗試,嘗試不得法……也必然會來詢問我王的。」
薩爾可汗脊背挺直,手指屈起在桌几上敲了一下,道:「我們還是要做好再戰的準備,之前輕敵……如今知道大周的厲害,但夏季卻對我象軍極為有利,是戰是和……就端看大周皇帝的了。」
「如今大周和燕國賭國在即,想來……大周也不想同我們天鳳國對上。」天鳳國大巫道。
薩爾可汗垂下眸子,隨手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並未言語,倒是讓大巫和其他隨行的天鳳國官員捉摸不透薩爾可汗到底在想什麼。
魏忠從「軟禁」薩爾可汗一行人的驛館院子裡出來,穿過迴廊石林景林,魏忠碰到了正倚著假山上倚欄而坐的慕容衍,腳下步子一頓,恭敬同慕容衍行禮後,這才帶著人離開。
「主子,打聽清楚了,是天鳳國的國君!」月拾動作輕巧落在涼亭外,單膝跪地同慕容衍說。
「天鳳國……」慕容衍手中握著一把摺扇,在手心中點了點,「阿瀝私底下派人去聯繫東夷國,天鳳國的人又來了大周,倒是有意思。」
也不知道,這最後賭國,誰能贏。
不論最後是阿寶贏還是阿瀝贏,慕容衍要做的,就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燕國,並且在賭國之事有了定論之後,確保雙方能夠順利願賭服輸,不會引發戰爭。
*
魏忠回宮後,將薩爾可汗他們何時來的大都城稟報了白卿言,又將薩爾可汗的話原原本本說與白卿言聽,頗為擔心開口:“陛下,這天鳳國的國君來者不善,恐怕是謀算著陛下來的。”
「難不成,他還能捨了他的天鳳國,來咱們大周做皇夫嗎?」白卿言瞧著魏忠嚴肅的模樣輕笑一聲,用筆桿點了點桌角的玉蟬,「八成,是為了皇夫蕭容衍手中的那枚玉蟬。」
魏忠一想也是,怎麼說那薩爾可汗也是天鳳國的國君,難不成會將國君之位讓給別人來大周做皇夫,他們大姑娘更不會捨下大周去做天鳳國的皇后,也是他想的多了。
也是剛才薩爾可汗那話說的太過曖昧,引人遐想,又是說想要秦晉之好,又是說思念甚深,魏忠難免不會想到薩爾可汗對白卿言生了什麼妄念,說到底除了白卿言皇帝的身分之外,白卿言的容貌也是天下難有的清豔。
沈司空得了白卿言啟用韓城王的消息,且已在昨日命韓城王奔赴沿海,還將之前輔國君嘗試訓練的水師精銳交給韓城王,天不亮就在宮門口求見。
白卿言批閱奏摺至半夜才睡下沒多久,就聽到外面小太監低聲和魏忠說沈司空在外求見。
她睡眠一向淺,窗外細微的聲響便能將她驚醒。
「魏忠……」她坐起身來。
守夜的春桃聽到白卿言的聲音連忙上前,抬手撩開床帳:「大姑娘醒了……」
魏忠聞言連忙進來,隔著楠木山水畫屏,他隱約瞧見白卿言披著件外裳坐在床邊,連忙行禮:「陛下……可是吵到您了?」
“沈司空來了?”她一邊穿衣裳一邊問。
白卿言大約能猜到沈司空是為何而來,約莫是因為韓城王離開大都城去沿海之事。
「正是,說是天不亮就在宮外候著。」
「快去請進來!」白卿言又吩咐春枝,「去讓小廚房準備熱湯餅,一會兒端去書房。」
「是!」春枝伺候著白卿言穿好了鞋履,起身往外退。
伺候白卿言晨起的太監宮婢捧盆執壺,端著盥洗用具弓著腰魚貫而入,依序伺候著白卿言淨面,用細鹽漱口。春桃替白卿言更換朝服,心疼白卿言還未睡多大一會兒就起來了,可也知道自家大姑娘身為皇帝身繫天下百姓的福祉,只能擱在心裡心疼。
白卿言穿好衣裳,因著還未到早朝便未帶旒冠,到書房時,沈敬中也剛到沒多久,一見白卿言進來便跪下行禮:「微臣見過陛下,打擾陛下安眠了。」
「不礙事,一會兒也該早朝了。」白卿言虛扶了沈敬中一把,「沈司空坐,這麼早過來想來還未用早膳,與我一同用一些,我們邊吃邊說。」
「是!」沈敬中知道白卿言的性子,便沒有拒絕。
太監抬著案桌進來,擱在沈敬中的面前,上了熱湯餅。
「沈司空將就同我用一些……」白卿言對沈敬中做了一個請的姿勢,沈敬中對白卿言一拜,將自己內心的疑惑說了出來,語重心長道,「陛下,韓城王乃是大樑舊日的三皇子,一旦其手中掌握兵權,再生了異心,怕是會成心腹大患。」
「沈司空,此人我既然敢用,便有我敢用的道理,韓城王並非是一個貪生怕死庸碌無能之人,沈司空可不要被韓城王那看起來憨厚的外表給騙了!」
「陛下,微臣是怕陛下被韓城王憨厚的外在給騙了啊!」沈司空焦急不已。
此事沈司空得了消息,便去找呂太尉,可呂太尉聽完之後卻也沒有放在心上,只說白卿言識人之明早已見識過,不必太過憂心,白卿言敢用韓城王就必能制住韓城王。
沈司空被勸回去一夜輾轉反側,終於還是忍不住在天不亮的時候決定來找白卿言,在早朝之前將此事說與白卿言聽。
「沈司空,從我登基至今,沈司空從未如今日這般主動來同我討論關於朝政之事,今日沈司空來了,我很高興!」白卿言望著神色焦急的沈司空緩緩開口,「我從不做自己無把握之事,也從不用自己懷疑之人,沈司空……你我君臣相處的日子不算短,希望這一次沈司空能信我,也希望沈司空能拿出真本事來,不為我這個皇帝,只為這個朝廷,為……以稅賦奉養沈司空的百姓,希望沈司空能和韓城王一般,有所作為。」
沈敬中抬眸看著坐在正中間,面色平靜的白卿言,幾乎是被白卿言一針見血揭開了他未曾拿出真本事來輔佐白卿言這位皇帝的事實。
對於白卿言,沈敬中敬佩,甚至三番幾次被白卿言動搖,可……他卻從未如同呂太尉他們那般拼盡全力輔佐,坐在司空這個位置上,沈敬中心中是有愧的。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女帝 卷十三的圖書 |
 |
女帝卷十三【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千樺盡落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8-27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女帝 卷十三
天下一統之路正式展開!
白卿言不願百姓生靈塗炭,將士血流成河,
便在滅西涼之戰前與燕國商議妥當, 雙方將以「賭國」一統天下。
三年為期,
大周與燕國,誰家的國策能使百姓富強來定輸贏,輸者併入贏者為一國!
這勝敗之間,
將決定哪一國國君為珪璋,哪一國國君為土芥!
但是,天下一統之路,怎麼可能如此簡單與順利?
燕國和天鳳國不約而同的紛紛拉攏起了東夷國,只因……
燕國為取得優勢,在暗地裡活動,巴不得東夷和大周打起來,讓大周輸了賭國,
天鳳國為了拿回遺失在大周的國寶--玉蟬,更是明目張膽的找事,讓大周陷入困境,
即使一統之路遇險阻,
大周英勇的將士,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所肩負著的使命,
捨生取義,他們……即便是死,死前也一定要完成任務。
只因他們的犧牲,
是為了換來一個更為強大的大周,
換來一個再也沒有敵國侵擾的大周,
此一戰滅東夷之後,大周百姓將享萬世太平。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沒有想著能活著回去,他們想的是死前完成任務……
作者簡介:
千樺盡落
閱文集團超人氣作家。
其作品長期位於網文平台推薦榜前列。
作品風格清新,感情細膩,善於書寫關於女性成長與蛻變的傳奇故事。
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著有《終於嫁給岑先生》《傅先生,偏偏喜歡你》《女帝》等多部暢銷著作。
《女帝》已售出影視版權。
章節試閱
第二章 兩國互市
馬車內,春桃用團扇輕輕給白卿言搧著風,低聲說:「瞧著高將軍像是大好了,大姑娘也能放心了。」
「嗯……」白卿言笑著應聲,「等錦繡回來瞧見高將軍,一定會高興的!」
「只可惜,二爺再也回不來了。」春枝低沉聲說了這麼一句,又反應過來怕惹白卿言傷心,轉頭撩開車窗輕紗朝外面瞧去,「大姑娘,您瞧……這麼熱的天,咱們大都城還這麼熱鬧人來人往的,這都是大姑娘治理有方的緣故。」
「我們春枝也學會拍馬屁了!」白卿言雖然這麼說著,視線也難免從春枝挑開的狹窄窗縫朝大街上的熙攘人群望去。
陡然,一個梳著...
馬車內,春桃用團扇輕輕給白卿言搧著風,低聲說:「瞧著高將軍像是大好了,大姑娘也能放心了。」
「嗯……」白卿言笑著應聲,「等錦繡回來瞧見高將軍,一定會高興的!」
「只可惜,二爺再也回不來了。」春枝低沉聲說了這麼一句,又反應過來怕惹白卿言傷心,轉頭撩開車窗輕紗朝外面瞧去,「大姑娘,您瞧……這麼熱的天,咱們大都城還這麼熱鬧人來人往的,這都是大姑娘治理有方的緣故。」
「我們春枝也學會拍馬屁了!」白卿言雖然這麼說著,視線也難免從春枝挑開的狹窄窗縫朝大街上的熙攘人群望去。
陡然,一個梳著...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心懷天下
第二章 兩國互市
第三章 知難而退
第四章 死諫為國
第五章 深信不疑
第六章 逃無可逃
第七章 壯烈犧牲
第八章 御駕親征
第九章 收攏軍心
第十章 誓滅東夷
第二章 兩國互市
第三章 知難而退
第四章 死諫為國
第五章 深信不疑
第六章 逃無可逃
第七章 壯烈犧牲
第八章 御駕親征
第九章 收攏軍心
第十章 誓滅東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