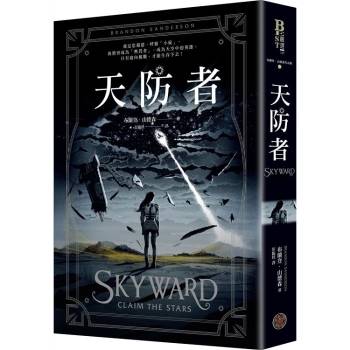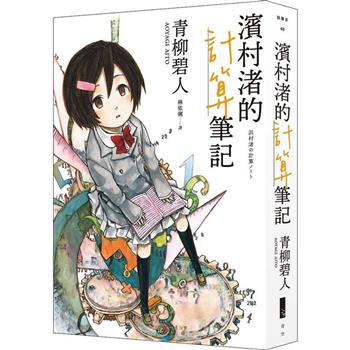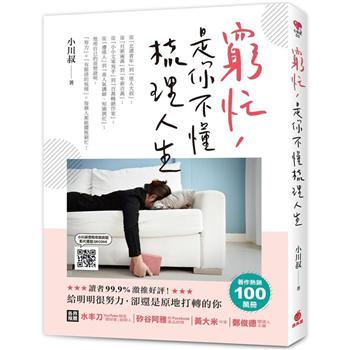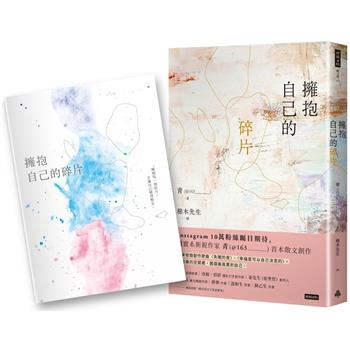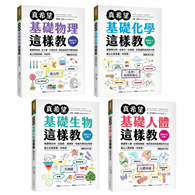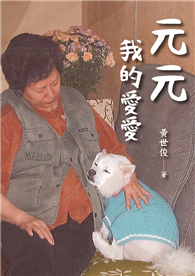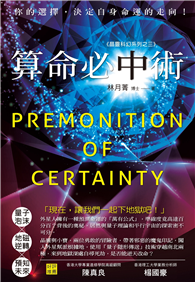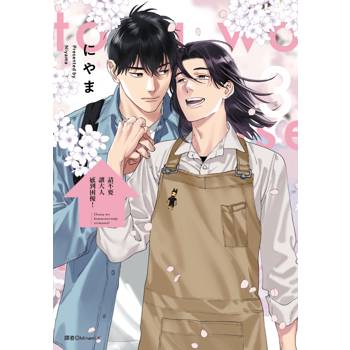無數樂團與音樂人的重要演出,
皆在公館「海邊的卡夫卡」發生!
同名紀錄片《後青春:再見搖滾》2025年春天全台搖滾獻映!
皆在公館「海邊的卡夫卡」發生!
同名紀錄片《後青春:再見搖滾》2025年春天全台搖滾獻映!
1976/阿凱、四分衛/陳如山、滅火器/楊大正、甜梅號/昆蟲白、旺福、鄭宜農、八十八顆芭樂籽、巴奈、Green! Eyes/老王、莊鵑瑛(小球)、高小糕、吳志寧、張維尼、黃子軒、余佩真、王榆鈞、丁佳慧、DSPS/曾稔文、黃玠、大象體操、LINION、康士坦的變化球、逃走鮑伯、OHAN……
公館「海邊的卡夫卡」live house二○○五年開幕後立即成為台北指標性的獨立音樂表演場地之一,本書採訪近四十組樂團、音樂人、藝術家,請大家暢談青春回憶錄,試圖挖掘不同世代、不同角度的公館「海邊的卡夫卡」,同時也盡可能蒐羅珍貴影像,全力為公館「海邊的卡夫卡」二○二三年一月吹響熄燈號之前的珍貴身影留下見證。
齊聲推薦
「1976」阿凱(「海邊的卡夫卡」主理人)
黃韻玲(音樂製作人、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董事長)
陳珊妮(創作歌手、音樂製作人)
馬世芳(作家、主持人)
朱頭皮(音樂創作人、歌手)
昆蟲白(創作歌手)
莊鵑瑛[小球](歌手、自由創作者)
黃士勛Finn(創作歌手、演員)
黃子軒(「黃子軒與山平快」團長)
余佩真(創作歌手、演員)
LINION(創作歌手)
曾稔文(「DSPS」樂團主唱)
劉中薇(作家、《未來媽媽》編劇)
吳洛纓(導演、編劇)
徐志怡(《我願意》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