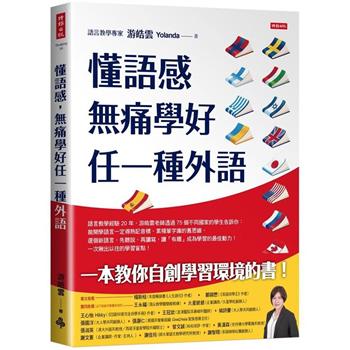從巴黎左岸到冬山河畔,
天龍女降落底層工場的人性碰撞
某一天,早上醒來……
我忽然像作家卡夫卡《變形記》的主人翁一樣:
「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昆蟲」。
……我沒有變成一隻蟲。我只是頓悟了自己是一個女工。
完全派不上用場的學歷。連個報廢了的瓦斯桶都不如!
這輩子第一次發現我所有的知識邏輯,完全不通,全數作廢。
一個我不懂的行業,一群我不認識的人,
一個我聽得懂卻沒法流利交談的語言,一個我不熟悉的環境。
我是唯一的女性。而且我是老闆。
努力,讓我覺得自己活著。認真的活著。
在羅東,守著寒冬,盼望春風……
如果到了羅東火車站,叫計程車,司機一聽到這個地址,通常都會愣住。如果是晚上,他們通常不肯載。
……經過最後一個紅綠燈,和十字路口的小雜貨店,就沒有煙火人家了。
我家在羅東有個瓦斯場。
我唸完大學,離開了台灣。弟弟妹妹也陸續成家立業,
二○二二年九月,爸爸走了。留下了這個分裝場。弟弟妹妹毫無興趣。員工都沒有走,客戶也都沒有離開。「我會回來。」這是我對父親的承諾。
我不想賣掉,也婉拒了幾個有興趣要承租的人。說穿了我只想維持現狀。
因為這是爸爸堅持撐到最後,一直做到他病倒了,辛苦了一輩子,養育了我們一家人的血汗工廠。
我不知道從哪裡接手。
我完全派不上用場的學歷。連個報廢了的瓦斯桶都不如!
於是只能從我最遙遠也最清楚的記憶開始:在工廠守歲過年……
捨不得的是這個破舊的瓦斯分裝場嗎?這裡沒有我任何甜蜜快樂的回憶,沒有一個讓我可以放鬆休息的角落,我對瓦斯分裝一竅不通,我對客戶毫無了解,我對羅東陌生無感,我到底捨不得什麼?
爸爸……
我捨不得的不是瓦斯場。熟悉又陌生的瓦斯場就像爸爸,一個相處了一輩子的陌生人。要等他走了,離開了,我才開始認識他,靠近他,我才敢走進他的世界。
要這樣的生離死別,才能讓我們相識相遇。
守住這個廠,守住爸爸在這個世界上,孤獨闖蕩了一輩子,拼了命留下的人生足跡,他耕耘了一輩子的一方角落。這是我唯一能替他做的。
從巴黎左岸到冬山河畔;從布魯塞爾到宜蘭羅東,所阻隔的豈只是地理上的千山萬水,真正難跨越的是心理距離與族群、語言和階級認同。
作者在此書探索了「我是誰」?「何處是我家」?這樣亙古至今的哲學性問題。透過繼承瓦斯場的艱辛,試圖與父親達成和解,卻最終,成為療癒自己,與自己和解的珍貴旅程。
【專文推薦】
李永萍│陳文茜
她追尋爸爸的足跡、也想重新理解自己的根源;雅倫透過繼承瓦斯場的艱辛,試圖與父親達成和解,卻最終,成為療癒自己,與自己和解的珍貴旅程。……她奇幻的斜槓人生,或許終將成為寫實的台灣啟示錄。──李永萍
她在中年之後,父亡之後,才每週開著父親的Mini Cooper小車,至父親留下的液化瓦斯分裝場。從台北至羅東的路上,似乎比台北至巴黎、布魯塞爾還遠。沿途經過礁溪、宜蘭、三星、冬山,……到羅東了。時間不是丈量距離惟一的尺度,包括你必須改變的心態,改變的待人方式,看人的角度,還有自己的定位。──陳文茜
作者簡介:
王雅倫
台灣台北人。比利時客家人。羅東新鮮人。瓦斯界素人。
嫁了一個拿不到台灣配偶身分的比利時人。
生了兩個等待進化成台灣人的外國人。
出生在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
居住在一個隨時都可能分裂消失的國家。
不吃素,但是對心靈雞湯過敏。
只要在乎,就會全力以赴。
沒有臉書,因為覺得人與人之間最好的距離,
就是相忘於江湖。
最喜歡的答案是,以上皆非。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王雅倫奇幻的斜槓人生
/李永萍
今年(二○二四年)開始,我和我的朋友們,主要是一起長大、共同定義著彼此人生。北一女和台大外文系的同學們,陸陸續續都過了六十歲生日。即便我們生活在多數人可以期待八十或九十歲壽數的二十一世紀,六十歲或許不再有沉重的暮年之氣,但畢竟是一道重要的人生關卡;值得反省沉思、覺醒與再覺醒。我們多數同齡的好友們,或是遺憾於過去的選擇、或是悲嘆於年輕時瑰麗的夢想難尋;然而卻有少數人──極少數──,會決定在此刻人生重開機,跳出舒適圈、改變自我數十年來的階級定義,展開意想不到的斜槓人生。
王雅倫就是這極少數的一員。
在她面臨父親過世,留下一座位於宜蘭羅東、財務不佳的瓦斯場分裝廠時,王雅倫不考慮變賣、不願意分租,固執地親自接手賣瓦斯。六十歲的她,是參與「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在職訓練」課程最老的學生,以及唯一的女生。
於是,王雅倫開啟了她在《文茜世界周報》歐洲撰述/作家以外的另一個斜槓人生──羅東墳墓坡中瓦斯場老闆/女工。
雅倫這本書記錄了她跨越階級、國界的奇特經驗與領悟之道。寫的是台灣宜蘭羅東的在地故事,卻非常有「異國風」。因為,二十歲即赴歐留學的她,法文說得比台語好,而她的破台語成了她在瓦斯場工作的障礙。她的員工、客戶無法當她為自己人,雖然賣瓦斯並不要求與人交心,然而一旦被視為「外人」、「外地人」、「外國人」,王雅倫在羅東就面臨被欺生、被欠債,甚至被威脅的處境。
在我們同學們生活的小宇宙中,英文比台語重要,法文比英文稀罕。雅倫從高中時期就被視為語言天份極高,是英文演講比賽的常勝軍。大學時,她的媽媽在蒙藏委員會工作,雅倫暑期去實習,回來竟也能說蒙古語。在法國法文流利程度一度被誤認為土生土長法國人的她,到了羅東,卻被譏嘲「講台語好好笑」,並被員工嗆聲說不想聽她的破台語。
從巴黎左岸到冬山河畔,從布魯塞爾到宜蘭羅東,所阻隔的豈只是地理上的千山萬水,真正難跨越的是心理距離與族群、語言和階級認同。
雅倫的書寫,表面上要回答一個反差力極強的問題:為什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北一女台大畢業生、擁有法國雙碩士學位的中產階級女士,要堅持在台灣鄉下賣瓦斯?而更深層次的是,她在此書探索了「我是誰」?「何處是我家」?這樣亙古至今的哲學性問題。
「雅倫說,2023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早上醒來……
我忽然像作家卡夫卡《變形記》的主人翁一樣:「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昆蟲」。
……我沒有變成一隻蟲。
我只是頓悟了自己是一個女工。
……
我的爸爸2022年中秋節,走了。留下了一個破舊不堪的瓦斯場。
搞了半天,我就是一個工人小孩。…… 」
王雅倫從小到大都很怕她的父親。有一段時間雅倫一旦從歐洲返台,她寧可窩在我家,也無法去跟獨居的父親同住。父女間的無法溝通,隨著王伯伯晚年重聽日益嚴重,一切就變得更困難了。
然而,在她父親離世、自己即將邁入六十歲的關卡,雅倫決定穿起父親的工人鞋子,一步步走著父親曾走過的路(雖然現在有了雪隧,路好走多了)。她追尋爸爸的足跡、也想重新理解自己的根源;雅倫透過繼承瓦斯場的艱辛,試圖與父親達成和解,卻最終,成為療癒自己,與自己和解的珍貴旅程。
做為好友的我,在讀這本書時,淚點很低,對雅倫在羅東遭遇的種種,感到心疼,也不捨她如此自苦。然而轉念一想,若將六十歲後的雅倫定位為「墳墓坡中瓦斯場準時上工的詩人」,這樣的意象,似也頗有十九世紀歐洲風格,不免就釋懷了。
王雅倫奇幻的斜槓人生,或許終將成為寫實的台灣啟示錄。
名人推薦:推薦序
王雅倫奇幻的斜槓人生
/李永萍
今年(二○二四年)開始,我和我的朋友們,主要是一起長大、共同定義著彼此人生。北一女和台大外文系的同學們,陸陸續續都過了六十歲生日。即便我們生活在多數人可以期待八十或九十歲壽數的二十一世紀,六十歲或許不再有沉重的暮年之氣,但畢竟是一道重要的人生關卡;值得反省沉思、覺醒與再覺醒。我們多數同齡的好友們,或是遺憾於過去的選擇、或是悲嘆於年輕時瑰麗的夢想難尋;然而卻有少數人──極少數──,會決定在此刻人生重開機,跳出舒適圈、改變自我數十年來的階級定義,...
章節試閱
北宜公路
如果到了羅東火車站,叫計程車,司機一聽到這個地址,通常都會愣住。如果是晚上,他們通常不肯載。
「沒有人晚上去那裡啦。」
沒錯。大家來羅東去的是熱鬧的羅東夜市。誰會在一個不是清明節的日子,專程要去漆黑死寂的……
如果是白天去呢?
我看得出司機的猶豫:我默數到三(通常不會超過三……)。他們算的更快:車程最少兩百元跑不掉。
點點頭,上車吧。
穿過熱鬧吵雜的市中心,街道兩旁喧嚷忙碌的商家,川流不息的人車,開始出現零星的水稻田,遠處是環繞著羅東層層疊疊的山脊線。住家商店變得零星稀少。
經過最後一個紅綠燈,和十字路口的小雜貨店,就沒有煙火人家了。
緊接著的是另一種風景。襯著羅東冬天的陰雨,灰灰蒼蒼的天地,遠方幾近墨黑的空靈山影,但是霸佔眼前視線的卻是唐突錯亂的擁擠:一大片五顏六色,各有方向,大小不一,但又緊緊挨著幾乎看不見空隙,也看不見盡頭的「墓仔埔」。
也算是一種另類的熱鬧繽紛。
只是頓時沒了熙攘的人聲。再多的顏色,也無聲無息的擁擠。
它們在顏色上唯一的交集,是那塊或橫或豎,黑底金字的墓碑。和各家各戶之間冒出來的,比墓碑還高的油綠綠的雜草,看似毫無章法,卻是清楚明白互不侵犯的楚河漢界。越往裡走,橫寫的墓碑越多,因為漸漸是佔地面積越來越大,建築越來越壯觀華麗的陰宅。大多沒有往生者的名號,沒有立碑的年月日,而是各個姓氏的「祖宗佳城」。簡單的像一塊大型廣告招牌。
福地市場也有豪門大戶。這裡絕對是陰宅裡的帝寶。除了它們沒有地址門號。
通常司機在這個時刻會回頭問我──即使他們有導航──「快到了嗎?」
「繼續走。」
我要去的是一個有地址門號的液態瓦斯分裝場。
但是我老是記不住分裝場的確實地址,因為從我有記憶以來,原來是深藏在一大片果樹農地裡的分裝場,隨著周圍福地陰宅面積的擴大,種植果樹的田地被變賣出售,道路的開拓延伸,路名的規劃變更……
有道是滄海變桑田,這裡倒是桑田變佳城。四十多年以來,唯一不變的,是這個漸漸被墳地四面包圍的瓦斯分裝場。
我記不得路名,但是我知道在哪裡轉彎,原來是田埂的小路口,有一棵一直都在的,高高的檳榔樹。
我很少自己開車來。小時候,總是坐著爸爸的車來工廠的。在北海岸的雪山隧道開通之前,只有一條山路可走,台北開往新店南邊山裡,經過坪林、礁溪的「九拐十八彎」──長大之後,才知道這就是險峻的北宜公路。
我們有機會和爸爸一起去羅東的時間,都是每年春節的年假期間,小時候哪知道這條路的危險,只記得彎彎曲曲令人頭暈想吐的山路,窗外雲霧繚繞間,遠遠近近的山巒,縱深綿密的山谷,和沿路上不時出現的,散落在彎道路邊的冥紙。我們也有撒冥紙的時候,爸媽分給我們姐弟三人每人一小疊紙片,我們興奮的搖下車窗,伸手使勁揮撒出去,然後看著那些金金亮亮的小紙片,瞬間隨著車速飛揚而起,再飄呀飄地遠遠的落在車後。一旦落地,山裡的濕氣或是雨水就讓它們再也飛不起來。我們這才回過頭來,往前看,抓緊手裡的一把新紙,準備再撒一把……再歡呼一次。
瓦斯場不能放鞭炮。北宜公路上滿天飛揚的冥紙,竟然成了我小時候,過年最鮮明的記憶。
那時的宜蘭還不是現在的觀光勝地。印象中這是一條從不塞車的路。所以任我們撒得滿天滿地的冥紙,並不干擾後面駕駛的視線──因為通常後面沒有車。前面呢?好像也沒車。印象中,我們是山路迴轉之間唯一的車。偶爾會看到遠處閃閃爍爍的車燈,在曲折的山路間或隱或現,然後毫無準備地在短短的直線車道上迎面而來,扭了一百八十度的脖子還沒轉回來,就已經擦身而過。
整座山裡又剩下我們。
偶爾爸爸的車速降得更慢,那肯定是下雨了,或者是山裡的霧太大太濃,伸手不見五指,更要小心翼翼。即使我們手上還有冥紙也不撒了,因為撒出去也看不見。我們一下子都安靜下來,瞪著什麼都看不見的前方。一種莫名所以的緊張。
直到忽然前方出現兩個小紅點,哇!太好了,這表示爸爸只要跟著前面的車燈走,就安全了。我們鬆了一口氣,可以放心的睡去。一覺醒來,就到羅東了。
一家五口擠在小小的車裡,這應該算是我們全家唯一的,過年的團圓時刻。
因為走完北宜公路,穿過果樹農地,來到分裝場,爸爸立刻馬不停蹄地跑上工作台,忙著和其他幾位工人把氣槽裡的瓦斯,灌進大小不一的瓦斯桶裡,再把滿滿的瓦斯桶滾上各個瓦斯行的卡車,讓他們趕著年夜飯前,再多送幾趟。除夕家家戶戶都要燒瓦斯,工作台上忙翻了,根本沒有我們小孩湊熱鬧的份兒。我們通常被安排去貼春聯。
有時候他們忙不過來,也會讓我們幫忙,我們就獲准到台子上去替瓦斯桶封口:用一個個泡在酒精罐子裡的紅塑膠薄片,包住灌好的瓦斯桶接口,等酒精揮發了塑膠薄片就會繃緊,保護瓦斯桶不漏氣。像是整個作業流程結束的一個紅色句點。
媽媽則忙著清理從台北帶來的年菜,在簡陋的工廠廚房裡忙乎起來,準備大家下工後的年夜飯。通常都要忙到很晚,我們等著等著,都歪歪斜斜地睡著了,又被叫起來吃年夜飯。上桌吃飯的不只我們家五個人,每年都有下工後來不及趕回家吃團圓飯的一兩位員工。吃完飯領了工錢,他們才騎著摩托車或開著卡車離開,通常都已經接近午夜了。這才終於輪到我們小孩領紅包。
然後整個工廠就只剩下我們一家人。
我們爬上工廠的通鋪,把壓歲錢放在一顆不認識的枕頭下,疲累壓過了陌生的氣味,就這樣一覺睡到大年初一。愛睡到什麼時候起來也沒人管。醒了。其實沒醒,黏糊著一張臉,不知道接下來要幹什麼的茫然。可以倒頭繼續昏睡,或者起床繼續發呆。小時候的無聊,卻是記憶裡最鮮明的黑白。
電話鈴響,爸爸接電話拜年時熱絡的恭喜發財。啊。大年初一。
最開心的應該是工廠的小狗,有記憶以來,這裡一直都有隻狗,就是最普通的土狗,牠和我們一樣,在昏睡與發呆之間,百無聊賴。癡心等待我們醒來,進入牠的視野時,剎那間爆發的興奮,牠汪汪汪的恭喜賀歲,追著我們滿地亂轉。於是我們都醒了。除了要說吉祥話,和吃一小棵媽媽準備好的長年菜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功課。
就逗逗狗,開著電視,在千篇一律熱鬧無聊的賀歲節目前,比賽磕瓜子,把吐出來的瓜子殼堆成一座小山丘。爸爸忙著打電話拜年,媽媽忙著整理除夕的剩菜,或者其他的雜事。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只有我們一家人。一直到初三開工。
原來這就是歲月靜好。
我不記得除了羅東瓦斯場以外,其他春節的樣子。
除夕
這個分裝場一直都在。
我唸完大學,離開了台灣。弟弟妹妹也陸續成家立業,我們全家再也沒有一起去羅東過年。二○○○年初,已經接近七十的爸爸沒有體力自己經營了,就把分裝場租給別人。萬萬沒想到十年前,因為各種原因,爸爸居然又決定把租出去的分裝場,收回來自己經營。
從此去羅東分裝場過年的,只剩下他一個人。
唯一的改變,是他不再辛苦地走迂迴曲折的北宜公路。但是也沒有人陪他走雪山隧道了。
這十年,我總是在除夕夜打電話到分裝場,心疼他一個人守著這個分裝場過年。坦白說,我的心疼很廉價,但是對於辛苦打拼了一輩子的爸爸來說,這個廠,無價。
二○二二年九月,爸爸走了。
留下了這個分裝場。弟弟妹妹毫無興趣。我人不在台灣,但是我狠不下心放棄。
員工都沒有走,客戶也都沒有離開。我只能回來。這才發現:爸爸不在了,這個老舊的分裝廠,在我眼裡,也是無價。
平日夜裡值班守廠的員工,好幾個月前就問我:「過年怎麼辦?」
這是爸爸身後的第一個春節,怎麼辦?
老實說,我還搞不清楚狀況。但是我也沒有太多選擇。
「我會回來守廠值班。」這是我的承諾。
於是我在二○二三年的春節前三天,隻身趕回台灣,開著爸爸的車,帶著睡袋和簡單的行李,新買的春聯,開車摸索著不熟悉的導航路線:我要去工廠過年。
一個人。
只有媽媽擔心的問:「妳一個人可以嗎?」
我不知道,但是我點點頭。
和四十多年前一樣,二○二三除夕前的分裝廠,仍然是一整年最忙的時候。即使現在的灌氣作業,已經全部自動化了,我還是幫不上忙。看著大家忙進忙出,我像一個看戲的傻子。
雖然名義上我是老闆:一個什麼都不懂,還是像小時候一樣,只會貼春聯的老闆。
我不想賣掉,也婉拒了幾個有興趣要承租的人。說穿了我只想維持現狀。因為這是爸爸堅持撐到最後,一直做到他病倒了,辛苦了一輩子,養育了我們一家人的血汗工廠。
我不知道從哪裡接手。於是只能從我最遙遠也最清楚的記憶開始:在工廠守歲過年。
除夕一大清早就到了工廠。鐵門都還沒拉開。迎接我的是兩條狗。他們即使被拴著,也興高采烈又叫又跳地歡迎我,好久不見,別來無恙?牠們起碼認得我,不覺得我的出現有什麼奇怪。
不像那些和爸爸結識了三四十年的瓦斯行老闆們,看到我的出現,收下了我準備的年節伴手禮,半信半疑的問:「妳真的要在這裡過年?一個人?」
隨著他們的表情──如果是嚼著檳榔皺著眉頭,問號的意思就是:妳什麼也不會,留下來有什麼用?
那我就回答:「爸爸怎麼過年,我就怎麼過年。」我雖然不懂,但是我沒有逃走。
如果是表情裡驚訝多於嫌棄,問號的意思是:妳一個人……不怕?
他們指的當然是「墓仔埔」。信也好,不信也罷。我搖搖頭:不怕。我從小就習慣了。
一直懷疑我真的會趕回台灣,值班留守分裝場的幾位老員工,終於鬆了一口氣。不僅是因為我回來看守分裝場,也是因為有人發年終獎金了。
「我們到底有沒有錢發年終獎金?」我很直白的問會計。
打電話叫瓦斯都是現金交易。每家瓦斯行的售價大同小異,中油賣給分裝場的價格也不是秘密,二○二三年一月的公告價每家分裝場應該都一樣。
他們告訴我,我們分裝場的價格是全羅東最低。爸爸為什麼把價格訂得這麼低,我無從得知。但這是我現在要面對的事實:工廠幾乎毫無利潤可言。
「嗯,現金是有啦,」會計小姐說:「但是有沒有賺錢不知道。」
這也不能怪她。因為爸爸從來都是自己收帳算帳,不假手他人。
瓦斯行來分裝場灌氣,理論上也應該付現金。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尤其是爸爸先是病了……走了,很多客戶積欠現款項,員工們既沒有能力催繳,也不敢不繼續供氣。如此這般,幾個月下來,已經累積了數百萬的呆帳。
二○二三年春節前夕,烏克蘭戰爭爆發已經接近一年,全世界的天然氣價格水漲船高,要說賣瓦斯不賺錢甚至賠錢,實在是天方夜譚。
偏偏天方夜譚就發生在眼前:我們家絕對是全世界,唯一不賺錢的瓦斯分裝場。
我不確定我有錢發年終獎金,更不知道爸爸以前是給多少年終獎金。
「老闆都給兩個月喔。」跟了爸爸最久的員工小康這麼說。
「至少發一個半月,」另一位工人阿寬這麼說:「不過大姐妳可以給更多啊。」
怎麼能怪他們各自表述呢?誰叫我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也罷。即使工廠的帳,亂七八糟,年還是要過的。
過完年再說吧。
我請他們體諒工廠目前的困難。我給了每個人一個月的年終獎金。
領了年終獎金,他們可以安心下班回家吃年夜飯了。
我把原來工廠裡拴著的兩隻狗,也放了。過年嘛,我不想拴住牠們。餵飽了,解開鎖,小黃和老黑頭也不回的跑了。
唯一沒有立刻離開的,是阿榮。他來分裝場工作還不到一年,會計小姐告訴我,不需要給他年終獎金。
我有權不給他年終獎金,但是如果我選擇不給,實在不是因為他還不滿一年。而是因為他才剛來三個月,工廠就收到宜蘭法院的判決書,要求每個月必須扣繳他的薪水,來歸還他到職之前所積欠的債務。但是執行扣款讓他原本的薪水少了幾千塊錢,他根本入不敷出,每個月都要求預先支薪。喔,不是每個月,他每個禮拜都要借錢。
阿榮一共積欠了將近八萬元的債款。八萬元不算多,但是阿榮的底薪只有兩萬七啊。
冬天是瓦斯工廠最忙的時候,我們需要人手,沒法立刻重新招聘,只能沿用阿榮。但是他天天向會計借錢,搞得會計小姐煩不勝煩,三不五時就打給還趕不回台灣的我:大姐,阿榮要預支五千元……為了不影響工廠運作和其他員工,我決定先全數替阿榮還清欠款,希望他好好專心工作。
沒想到阿榮,這一刻竟然理直氣壯地問我:「為什麼我沒有年終獎金?」
他的問題荒謬的好笑,但是我不能笑。
「你覺得我還應該給發你年終獎金?」
他嚼著檳榔,咧著一口沒了門牙的紅嘴:「我有很認真工作啊。」
我提醒他那八萬元是我付的。他搔搔頭:「對啦,謝謝大姐,我會還啦。」
每個月的薪水都不夠用,我問他準備怎麼還?
「啊就還啊。」
我嘆口氣:「這樣吧。你就住在附近,你過年這兩天來值班,白天算三千,夜裡算兩千,這樣可以抵掉一兩萬。剩下的只能每個月照扣。」
我不需要他來值班,只是替他想辦法還錢。這種加班費,我覺得自己簡直在做慈善。
「可是我要回家吃年夜飯。」他一臉驚訝,像一位被我逼著下海陪酒的良家婦女。
「隨便你。」感覺上像是我欠他錢。
坦白說,我寧可一個人,也不想和這個人一起在除夕夜留守工廠。
阿榮不置可否的離開了。還有幾家瓦斯行陸陸續續回分裝場補貨,一直忙著送到晚上,換好一整車灌滿的瓦斯桶,希望可以撐到初三。
晚上八點,我拉上鐵門。不知道兩隻老狗會不會回來。
沒有了白天裡來分秒不停的馬達聲,川流不息進進出出的貨車聲,還有搬動時瓦斯桶碰撞的金屬迴聲,整個工廠頓時安靜下來。只剩下偶爾傳來的狗吠聲,和一陣陣零星的蛙鳴。
我關掉室外的大燈,一下子伸手不見五指。遠處的山脊溶入黑夜,陰雨的除夕夜空看不見星星。
我反鎖上辦公室的門,泡上熱茶,沒有魚肉大餐,只有零食小吃。這是一個簡陋的辦公室,一張辦公桌,兩張老舊的沙發椅,一個小茶几,和拉上折疊屏風後面的一張床。我坐在爸爸的辦公桌前,看著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房間。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這一刻,大部分的人都在忙著圍爐,熱熱鬧鬧吃團圓飯。但是這些年,爸爸都是一個人在羅東過年。他一個人的時候,會期待我打電話來嗎?
我把手機關成靜音。
這何嘗不是一種隔離?不同的是,這是一個我自己選擇的隔離。新冠疫情這兩三年,為了回台灣看父母,我在比利時-上海-台北之間來來去去,前前後後一共被隔離了七個月。這兩三天實在是不足為道。而且不用量體溫,不用做核酸,不必快篩。
沒有了疫情的隔離,是一個安靜的歸零。
是句點。也是起點。
忙完了爸爸的後事。接手爸爸留下的,沒有交代的事。
我拉上屏風,打開睡袋和我的背包,驀地有種在某個山區營地裡搭棚過夜的感覺:只是我還搞不清山有多高,路有多難,就已經揹著登山背包上山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就像山裡一樣,即使隔著睡袋,也能感覺到羅東冬夜裡的陰冷潮濕。
沒有關係。我有登山者沒有的暖氣。還有熱水。這裡別的沒有,就是不缺瓦斯。
除夕的雨,像一道水濂,滴滴答答把我包圍起來,讓黑夜變得生動立體。沒有人聲鞭炮,也算是另一種熱鬧。
關了燈,脫掉外套,鑽進睡袋,感受著體溫和寒氣的尖銳衝撞。只能靜靜等著我的身體融化掉周圍的溼冷。這張床離牆只有一公尺,牆外就是工廠的外圍欄杆,和沿著欄杆,一條窄的無法同時錯車的小路。
小路的另一邊,就是白天也看不見盡頭的,各個姓氏的「祖宗佳城」。
躺在床上睡袋裡的我,和這些安靜的鄰居,不過就是咫尺之遙。
他們過年既不搓麻將,也不放鞭炮。我們互不打擾。
想了半天,終於想出我和他們最大的差別:我需要瓦斯,他們不需要。
沒有人會偷我的瓦斯。我於是安心的睡去。
北宜公路
如果到了羅東火車站,叫計程車,司機一聽到這個地址,通常都會愣住。如果是晚上,他們通常不肯載。
「沒有人晚上去那裡啦。」
沒錯。大家來羅東去的是熱鬧的羅東夜市。誰會在一個不是清明節的日子,專程要去漆黑死寂的……
如果是白天去呢?
我看得出司機的猶豫:我默數到三(通常不會超過三……)。他們算的更快:車程最少兩百元跑不掉。
點點頭,上車吧。
穿過熱鬧吵雜的市中心,街道兩旁喧嚷忙碌的商家,川流不息的人車,開始出現零星的水稻田,遠處是環繞著羅東層層疊疊的山脊線。住家商...
目錄
目錄
推薦序
李永萍
陳文茜
北宜公路
除夕
大年初一
值班
和平
六十萬(上)──情人節
春分──玉尊宮
錢的味道
廠長
一個多風的下午
階級意識
大仔
遲到
考試
六十萬(下)──答案:面子
她很那個……
作文比賽
千尋羅東
目錄
推薦序
李永萍
陳文茜
北宜公路
除夕
大年初一
值班
和平
六十萬(上)──情人節
春分──玉尊宮
錢的味道
廠長
一個多風的下午
階級意識
大仔
遲到
考試
六十萬(下)──答案:面子
她很那個……
作文比賽
千尋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