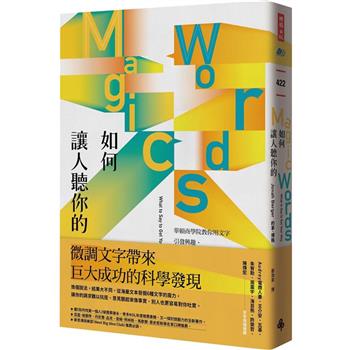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換取的孩子(紀念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80 |
日本文學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日本現代文學 |
$ 316 |
日本文學 |
$ 316 |
日本文學 |
$ 36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我」是不是一個已經被「換取」過的人?
最好的朋友,其中一個自殺了。
活下來的那個卻無法理解這個死亡的意義
『含帶誤差的重複。』
被換取過的我早已不再是我;或者,我終將以另一個我的形式存活?
來自森林的人本主義者──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獲獎三十週年紀念新版。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吳佩珍教授/專文導讀
「《換取的孩子》的序章,作為我此生寫出的篇幅稍長的短篇小說,它最為重要。」
──大江健三郎
「宮崎駿近似大江健三郎,關注著膨脹的自我中心與自身歷史問題意識的相互碰撞。」
──評論家,宇野常寬
沒有人能真正去體驗發生在別人身上的重大事件。
以謊言為糧的殘存的、僅有的、唯一的創作可能。
死,成了唯一的創作
一部感人的長篇小說,傾注心思在「尚未出生的人」身上開啟希望。
國際知名作家長江古義人的大舅子,電影導演塙吾良自殺了。作為他的好友和妹夫,長江古義人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為了逃避悲痛,他前往德國,在那裡他無意中獲得死亡的線索:黑幫突襲、性的醜聞、半個世紀前發生在四國的 令人震驚的「那件事」……古義人傾聽吾良在離世前寄給他的數十盒錄音帶,一步步解開作為在世生者的根本懸念。
本書是諾貝爾文學得主大江健三郎對伊丹十三的自殺而完成的小說新作。作為他的好友和妹夫,長達半世紀的交情,卻不瞭解好友為何自殺。書中共同經歷「那件事」之後,還是同一個人嗎?人為何會自殺,由此追溯並思考了友人悠長的往昔。每部作品都會觸及死亡,緬懷摯友同時,更是一場自我探索的旅程,將巨大的失落與重生的希望聯繫起來。被礜為大江晚期風格的至高代表作。
「換取的孩子」是中世紀歐洲流傳的民間傳說,當一個美麗的嬰兒出生時,一個像嬰兒惡魔一樣的仙女會用醜陋的孩子掉包。
小說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推翻已經在時間中固定下來的答案。
透過摯友的死亡,散發出極其清晰的光芒!
「年輕時,我與友人結為二人組合。不只是一個人,各式各樣的人。在我所有的小說裡都有奇怪的二人組合。作為身處人世且能進行回憶的人,我要將擁有與那些特別之人共同生活過的一切寫下來,直到人生接近終點。」
長達八年探索朋友之死與自身困境。大江健三郎坦言自己通過晚期工作而得以超越困難時刻,以「古義」為名,秉持勇敢前行的悲觀主義,去推翻時間中固定下來的答案,企圖醫治全人類的心靈創傷,以虛構的個人性經驗,作出人文主義的貢獻。
「用長遠的眼光來看,是有希望的。」
大江文學誕生晚期風格至高傑作──「奇怪的二人組」,故事由此開始。
作者簡介:
大江健三郎(1935-2023)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風格與傳統如川端康成等人的溫婉柔美不同,自創出一種曲折行進、氣勢洶洶的文體。
1935年生於日本四國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56年入東京大學法文系就讀,即嗜讀卡謬、沙特等作品,初期作品受其影響甚深,以存在主義為形式,呈現社會與個人的關係。1958年,以《飼養》一書榮獲芥川賞,確立他「學生作家」的文壇地位。
1963年,大江的妻子生下一個嚴重殘障的孩子,《萬延元年的足球》便是以此為本,這本代表作榮獲第三屆谷崎潤一郎大獎。1970年代,他又將文化人類學的理念逐步引進小說創作中,代表作為《個人的體驗》,該書除獲第十一屆新潮文學獎,並因此作英譯而將他推向國際作家的位置。
大江的小說主題充滿爭議,他將自己歸類為「怪誕現實主義」,他擅長將最強烈的恐懼和下意識願望穿插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合常理的想像瞬間改變現實。其寫作範圍涉獵寬廣且具人本關懷的精神,無論是政治、核能危機、死亡與再生、甚至包括宇宙論,皆呈現在他的創作中。
其著作《靜靜的生活》、《換取的孩子》、《憂容童子》、《再見,我的書!》、《兩百年的孩子》等書由時報出版。
譯者簡介:
劉慕沙
本名劉惠美,台灣省苗栗縣銅鑼人。1935年生。省立新竹女高畢業。曾任小學教員。著有《春心》短篇小說及散篇散文植從事日本文學譯作達三十年,除複行本芥川獎作品集 日本現代小說選等多冊外,於日本文學大家菊池寬、志賀直哉、石川達三、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島由紀夫、遠藤周作、曾野綾子、佐藤愛子、安部公房、源式雞太等名家之長短篇代表作,均有各別專集譯作,己結集成冊出版者達三十餘種。另有橫光利一、谷崎潤一郎、中河與一等散文集譯作。
序章 田龜的遊戲規則 1 古義人躺在書庫的行軍床上,豎耳諦聽耳機裡吾良的談話。 「……就是這麼回事,我就要移轉到那一邊去啦。」說著,咚──一聲巨響。一陣靜默之後,吾良繼續說:「可我並不是要跟你斷絕音訊,所以還特地準備了田龜的系統吶。不過,以你那一邊的時間來說,現在已經太遲了。晚安!」 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中,古義人感到一種彷彿自耳朵到眼底被撕裂的痛楚。就那樣一動不動躺了一晌後,他將田龜放回書櫥裡想法子入睡。也出於感冒藥的作用,他得以小睡了一下,卻被某種動靜擾醒,只見書庫傾斜的天花板那盞日光燈底下站著妻...
譯者序 關於《換取的孩子》
推薦序 死,成了唯一的創作──讀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
序章 田龜的遊戲規則
第一章 百日Quarantine(一)
第二章 「人,這種脆弱的東西」
第三章 恐怖行動與痛風
第四章 百日Quarantine(二)
第五章 鱉的嘗試
第六章 窺視者
終章 毛里斯‧仙達克的繪本
附錄 降靈會:一次殘暴而精準的演出──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的哀傷與荒涼 吳繼文
新版導讀 大江健三郎與長江古義人的距離――「奇妙的二人組」序曲《換取的孩子》 文│吳佩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