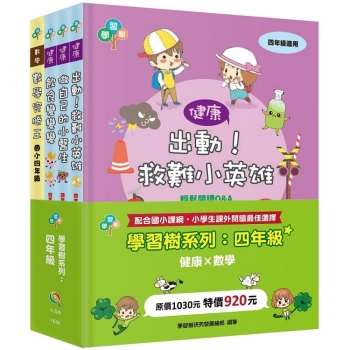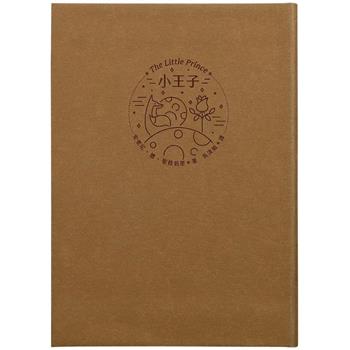第一章 看熱鬧的不嫌事大
快活樓位於長安西市口兒,正對群賢坊。老闆姓胡,名子曰,江湖人稱及時雨。手持一套鍋鏟,悶燉燒烹皆不在話下。尤其是瓦罐葫蘆頭 ,堪稱長安一絕。無論才子佳人,還是販夫走卒,吃了之後,皆連挑大拇指。除品嘗瓦罐葫蘆頭一飽口福之外,在快活樓吃飯,還有白賺了一項福利,就是聽胡子曰講古。
眼下時逢貞觀之治,四海昇平,民間殷實富足,長安城內平時連打架的混混都沒幾個,實在缺乏熱鬧可看。而康平坊、長樂坊那種銷金窟,又不是人人都花費得起。所以,聽掌櫃胡子曰講古,就成了街坊鄰居們最喜歡的樂趣。
而那及時雨胡子曰,也不是一個吝嗇人。只要你進了快活樓的門兒,哪怕不吃葫蘆頭,點一碗白開水坐上三個時辰,他也照樣吩咐夥計笑臉相迎。通常每日將早晨收購來的各種下水都收拾完畢,裝罐下鍋。胡子曰便會洗乾淨了手,捧上一壺茶,慢吞吞來到快活樓二層靠近圍欄的專座。而早已閒得腳底長毛的左鄰右舍們,就會爭先恐後地開口,催促胡子曰講昔日大唐健兒東征西討,盪平天下的故事。
那胡子曰也不推辭,抿上幾口熱茶,便口若懸河。從胡國公(秦瓊)陣前連挑突厥十二上將,到衛國公(李靖)雪夜襲定襄,說得活靈活現,令聽者無不如同身臨其境。偶爾有陌生酒客質疑故事的真實性,及時雨胡子曰便撇撇嘴,傲然解開自己的外衣,露出毛茸茸的胸口,以及前胸上那大大小小疤痕。一共二十四處,最長一處足足有半尺寬。最小一處則宛若踩扁的酒盞。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來自刀傷和破甲錐。
陌生酒客看到傷疤,肯定果斷閉嘴,臨走,往往還要多拍出幾文賞錢,算是請胡子曰喝酒。不為別的,就衝著胡子曰這一身為國而戰的見證。
每當這時,胡子曰也不矯情。收了錢後,再趁興說一段兒英國公李勣白道破虜庭,生擒突厥可汗的過程。整個酒樓,立刻就充滿了快活的笑聲。偶爾也有那不開眼的倔種,見不得胡子曰如此囂張。便會故意出言挑釁道,既然你胡某人身經百戰,為何連一官半職都沒混上,要在西市口洗葫蘆頭?
胡子曰不屑地看此人一眼,傲然道:胡某又不是為了富貴才從軍,亦受不了那份做官的拘束。至於這葫蘆頭,在胡某手中之時雖然污穢,入你口中之時卻乾乾淨淨。胡某不偷不搶,憑手藝賺這份乾淨錢財,又有什麼丟人?
話說到這個份上,即便嘴巴再刁鑽的人,也不可能繼續找茬生事了。畢竟在這快活樓裡吃葫蘆頭的,大多都是憑手藝和力氣吃飯的尋常百姓,有誰要非說胡子曰操持了一份賤業,恐怕會犯了眾怒。況且樓裡吃酒的客人當中,還有不少是胡子曰的鐵桿崇拜者。他們可不像胡子曰本人那樣好脾氣。惹急了他們,難免會落個灰頭土臉。
最近這幾天,快活樓的生意特別的好,幾乎每日都是賓客盈門。原因無他,大唐健兒在龜茲,捷報頻傳。先是契苾何力將軍,在龜茲擊敗乙毗咄可汗,打得後者落荒而逃。緊跟著,執失思力將軍,又在松州,用武力「說服」契丹二十餘部,令他們的酋長爭相來長安朝拜天可汗。尋常市井百姓,記得住衛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徐世績),胡國公秦瓊,哪裡知道執失思力和契苾何力兩位是哪個?耐不住心中好奇,難免想要找個見識廣博的人打聽究竟。而放眼西市群賢坊這一帶,除了官府衙門中大老爺們,還有誰能比大俠胡子曰見識更廣博?花兩文通寶要上一碗葫蘆頭和一角新釀綠蟻,一邊吃喝,一邊聽胡子曰介紹執失思力和契苾何力兩位將軍以往的英雄事蹟,又何樂而不為?
當聽到那胡子曰說,執失思力當年追隨突利可汗犯境,跟鎮軍大將軍程知節大戰數場,難分勝負,眾酒客們忍不住就直吸冷氣。又聽那胡子曰說,契苾何力百騎殺透吐谷渾人的重圍,救下薛萬鈞和薛萬徹,揚長而去。眾酒客又渾身血脈賁張,比喝了茱萸羊雜湯還要痛快。
這天,大夥正聽得過癮之際,耳畔卻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的的,的的,的的……」,緊跟著,三名背插角旗的信使,策馬從長街上呼嘯而過。還沒等眾人看得清其模樣,就不見了蹤影。
「估計是契苾何力將軍,又拿下了一座龜茲人的城池!」眾酒客立即顧不上再聽胡子曰說故事,望著信使的去向低聲議論。話音剛落,耳畔已經又傳來第二波馬蹄聲,「的的,的的,的的……」,隨即,又是三名背插角旗的信使,從大夥眼前急掠而去。
「莫非是生擒了龜茲可汗?」眾酒客愣了愣,刹那間,振奮莫名。
雖然大唐滅了龜茲,朝廷也不會多發一文錢到他們頭上。可是,作為唐人,他們至少覺得與有榮焉?更何況,龜茲被滅,接下來肯定會有祝捷、獻俘等一系列大型慶典。大夥會有許多熱鬧可看不說,身邊也將要陡增許多賺錢的機會,誰不感覺精神振奮?
「恐怕不是龜茲,信使背上插的角旗,三紅一黑,三紅代表是緊急軍情,一黑表明軍情來自正北方。」偏偏胡子曰的鐵桿崇拜者當中,有個人喜歡潑冷水,忽然站起身,皺著眉頭說道。
眾酒客頓時被掃了興,紛紛轉過頭,低聲向說話者斥責:「別胡說,北面的突厥人早就降了,能有什麼軍情!」
「就跟你曾經從軍多年一般?人家胡大俠都沒開口呢,哪有你一個小毛孩子顯擺的份兒!」
「誰家的野孩子,毛長齊了嗎?」
「滾,滾,烏鴉嘴,真晦氣!」
說話者是個少年,也就十七八歲模樣。沒想到大夥因為自己年紀小,就認定了自己在信口雌黃,頓時被憋得面紅耳赤。
「姜簡,你能認出信使背後的角旗所示含義?誰教的你?」胡子曰的確是個當大哥的料,見少年人被氣得眼淚都要流了出來,主動站起身,利用詢問的方式替他解圍。
「我姐夫教的!四門學裡的劉教習也教過。」被稱作姜簡的少年,素來敬服胡子曰。聽對方問,立刻顧不得委屈,拱拱手,啞著嗓子回應,「北方乃是玄武,黑色。而龜茲在西方,信使應該用白色角旗。信使背後有一根黑色旗,意味著敵情在北。而另外三杆紅色旗,則代表著消息的緊急程度,軍中規矩,日行三百里一杆紅旗,六百里加急以上,才是三杆。」
「你姐夫韓,韓秀才真的這麼教過?」酒客當中,有幾個是老主顧,知道少年的根底,拱了拱手,鄭重詢問。其餘酒客聞聽,立刻齊齊閉上了嘴巴。看向少年姜簡的目光裡,卻陡增許多困惑。這年頭,秀才地位遠在進士之上。凡高中秀才者,至少是六品官起步。而四門學,則是太學的一個分支,裡邊專門收錄官員子弟。少年姜簡的姐夫是秀才,自身又是太學生,照理,不該出現於快活樓這種專門給販夫走卒添肚子的下等酒館才對。怎麼此人,非但不嫌葫蘆頭骯髒,並且成了胡子曰的小跟班兒?
「我姐夫當然這麼教過,姐夫奉旨出使後突厥之前,專門教過我,如何辨認信差身後的標識。」少年姜簡這輩子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大俠胡子曰,另外一個,就是自家姐夫韓華。聽眾人問,立刻滿臉驕傲地高聲補充。
眾酒客們聞聽,立刻不敢再質疑姜簡的判斷了。一個個將頭看向長街,滿臉困惑,卻無論如何都猜不出,這年頭,北方還有什麼不開眼的勢力,敢冒犯大唐天威?
而那姜簡,終究是少年心性。見酒客們不再質疑自己,心裡的委屈也就散了。又叫了一壺好茶,一邊與周圍幾個年紀差不多的同伴分享茶水,一邊繼續聽胡子曰講執失思力和契苾何力的英雄事蹟。
胡子曰卻有些心不在焉,一邊講,一邊不停地抬頭向外張望。就等著下一波信使出現,好仔細分辨,其背後的角旗,是否如姜簡所說的那樣,一黑三紅。
還沒等看到結果,樓梯口,忽然衝上來一個小小的身影。三步兩步就來到了姜簡的桌案前,高聲叫嚷:「子明,子明,你居然還在這湊熱鬧。趕緊回家,你姐姐暈倒了!」
「什麼?」姜簡被嚇了一跳,縱身跳起來,拉住了報信人的胳膊,「小駱,你別嚇唬我?我姐身體好好的,怎麼可能暈倒!」
「剛剛,剛才禮部來了一個老頭,說,說突厥別部叛亂。你,你姐夫被什麼鼻子可汗給害死了!」那報信的少年小駱也是個愣頭青,想都不想,就直言相告。
「啊……」姜簡如遭霹靂,目瞪口呆。愣愣半晌,一把推開前來報信的小駱,縱身越出窗外。隨即跳上一匹自己寄放在門前的白馬,風馳電掣而去。
第二章鬧市相逢且按劍
「好身手!」
「好馬!」
酒客們常年居住在天子腳下,算是有名的「識貨」。立刻對少年的身手及其胯下的坐騎讚不絕口。但是,對於少年一家的遭遇,眾人的心裡頭卻湧不起多少同情。四門學乃是國子監 下設的六大分院之一,位於大唐皇宮斜對面的務本坊。能進出該院的學子,其父親官職至少都得是正七品。所以,無論學堂的位置,還是裡邊的學子身份,都距離快活樓太遠了一些。
至於秀才韓華,那更是愛吃葫蘆頭的酒客們,平素裡不可能接觸到的大人物。眼下他為國捐軀也好,捨生取義也罷,都在「凡夫俗子」心中,盪不起太多漣漪。
倒是那「膽兒肥」造反,殘害了大唐使者韓華等人的突厥別部可汗,引起了酒客們更多的關注。所以,沒等樓下的馬蹄聲去遠,眾人就開始交頭接耳探究起了此賊的來歷?
「鼻子可汗?這是哪一位啊,跟前些年被英國公抓回來給皇上跳舞的那位頡利可汗,是什麼關係?」
「突厥別部在哪?剛才那姓姜的小傢伙說是在北面,那北面可大了去了……」
「這當口造反,那鼻子可汗不是作死嗎?都不用衛國公和英國公兩位老爺子親自出馬。皇上隨便派一員裨將,就能誅了他全族!」
「誅什麼族啊,別說得那樣血淋淋的!皇上不愛殺人,只會誅心。將他抓回來,全家脫得光光的,給皇上跳舞……」
大夥你一言,我一語,如是種種,說得極為解氣,然而,卻始終沒整明白,那鼻子可汗的名號,到底是牛鼻子還是馬鼻子?更弄不明白,突厥別部到底在哪?
在場唯一一個,有可能為大夥解惑的人,就是快活樓掌櫃兼主廚胡子曰。畢竟,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當年曾經追隨英國公李勣(徐世績),趁著大雪天將突厥頡利可汗全家給掀了被窩。
可當酒客們將目光都轉向了胡子曰,並試圖掏幾文錢請他分說明白的時候。一向講究和氣生財的胡子曰,卻冷著臉向所有人拱了下手,就自顧自的回了後廚。緊跟著,後廚方向,就傳來的「咣、咣」的剁牲畜腸子聲。
「胡老哥今天是撞了什麼邪?怎麼拿捏起來了?」
「不想說就不說唄,甩臉色給誰看呢?」
酒客們被掃了興,嘴裡立刻開始低聲抱怨。總算念在彼此都是熟面孔,而那胡子曰平時做生意從不短斤少兩的份上,沒有立刻鬧將起來。然而,卻也沒有了繼續喝酒的興致,結帳的結帳,打包的打包,帶著五分不解和三分怒意,各自散去。
「大舅,大舅,誰惹您生氣了?」幾個胡子曰的鐵桿崇拜者,卻沒有跟隨酒客們一道散去,而是小心翼翼地進了後廚,圍在了正在剁羊腸的胡子曰身邊,低聲詢問究竟。問話者,乃是胡子曰的親外甥杜七藝。襄陽人士,他父母都在前年不幸染瘟疫亡故,所以帶著妹妹一道,來長安投奔胡子曰。
那胡子曰沒兒子,便拿杜七藝當親兒子看待,不僅不讓杜七藝跟自己一起幹處理牲口腸子的骯髒活,還挖門子盜洞,走通了營州別駕王薔的關係,將杜七藝塞進了京兆府的官學就讀。那府學畢業生的前途,固然比不得四門,太學和國子三大學堂,卻可以直接參加進士考試。一旦金榜題名,便能魚躍龍門。官職至少縣令起步。所以,聽到杜七藝發問,胡子曰即便心裡頭再堵得難受,也耐著性子回應道:「沒人惹我,我只是惱恨那車鼻可汗囂張。若是當年的瓦崗赤甲衛還在……」說到一半兒,他又覺得此話多餘。舉起刀,狠狠朝著案板剁了幾下,迅速改口,「不說這些沒用的。你平時跟姜簡關係好,一會兒替我去他家看看。他和他姐姐,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悲憤之下,千萬別惹出什麼禍事來。」
「嗯,我一會兒就去!」杜七藝聽得滿頭霧水,先答應一聲,然後又繼續安慰,「大舅您也別生氣了。咱們大唐兵多將廣,肯定很快會收拾了那車鼻可汗……」
「你不懂!」不待杜七藝把話說完,胡子曰就搖著頭打斷,「你們都不懂,皇上已經……,唉,算了,不說了。你趕緊去看著姜簡,讓他凡事看長遠。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快去,快去。至於你們幾個……」
扭頭看了看另外幾名平時像跟班兒一樣,圍著自己聽故事,外加時不時討教幾下武藝的長安少年和杜七藝的妹妹杜紅線,他嘆息補充:「都散了吧。接下來我還得去後院洗腸子呢。不小心濺你們一身,何苦來哉?」
說罷,也不管少年們央求還是抗議,邁開腳步,就去了後院井口旁。與大小夥計們一道,將已經在木桶裡頭浸泡了半個多時辰的羊腸子、馬腸子、驢腸子,一根接一根翻過來,用冷水反覆沖洗。做好之後的葫蘆頭香氣撲鼻,但帶著屎的牲畜腸子的味道,那可是不敢恭維。眾少年家境都不賴,如何受得如此「薰陶」。紛紛捂著鼻子倉皇後退,轉眼間就散了個乾乾淨淨。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大唐遊俠兒 卷一 烽火狼煙的圖書 |
 |
大唐遊俠兒 卷一 烽火狼煙 作者:酒徒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12-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唐遊俠兒 卷一 烽火狼煙
2024年酒徒全新歷史長篇巨作
唐代少年少女的大漠冒險之旅
草原上的規矩,向來是一狼死,一狼立。
時逢貞觀之治,四海升平,民間殷實富足,長安城內平時連打架的混混都沒幾個,實在缺乏熱鬧可看。而康平坊、長樂坊那種銷金窟,又不是人人都花費得起。所以,聽快活樓掌櫃胡子曰講古,就成了街坊鄰居們最喜歡的樂趣。一日,酒樓之中大夥正聽得過癮之際,耳畔卻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少年姜簡聽蹄認旗直言北方有變,卻未曾想到竟然是自家遭逢巨變,姊夫韓華奉旨出使突厥卻為車鼻可汗所害,姊姊姜蓉聞訊昏厥。
事後姜蓉請求面聖卻遭攔阻,姜簡為探求姊夫韓華真正死因,隻身前往漠北試圖找機會接近車鼻可汗。半路上,與急欲逃離大唐的史笸籮同行,不料卻被人販子拐騙,準備賣往大食。史笸籮實際上是車鼻可汗的三子阿史那沙缽羅,其父為了取信大唐朝廷,特地派遣他至長安讀書作為質子。車鼻可汗殺死韓華之時,還沒來得及派人接回。史笸籮接到消息後連夜倉皇出逃,不幸才剛離開中原地界,便落入了人販子的陷阱之中,只好聯手姜簡準備伺機脫逃。
作者簡介:
酒徒
內蒙古赤峰人,男,1974年生,東南大學動力工程系畢業,現旅居墨爾本。其作品擅長運用真實史事,從小處下筆,著眼處往往是前人未曾觸及的視野,以小人物的故事做為開端,結合傳統俠義、愛情傳奇等諸多元素,建構出當時歷史環境的整體風貌,寫實刻畫場景,細膩透寫人物,在歷史小說中推陳出新,有歷史小說裡的金庸如此的讚譽。目前為中國歷史小說界的翹楚,也是中國作家協會首度納入的網路作家。曾擔任網路文學導師,走進大學校園演講,培育新一代的文學作家不遺餘力。
著有《亂世宏圖》、《大漢光武》、《大明長歌》(以上為時報出版)等數十部作品。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看熱鬧的不嫌事大
快活樓位於長安西市口兒,正對群賢坊。老闆姓胡,名子曰,江湖人稱及時雨。手持一套鍋鏟,悶燉燒烹皆不在話下。尤其是瓦罐葫蘆頭 ,堪稱長安一絕。無論才子佳人,還是販夫走卒,吃了之後,皆連挑大拇指。除品嘗瓦罐葫蘆頭一飽口福之外,在快活樓吃飯,還有白賺了一項福利,就是聽胡子曰講古。
眼下時逢貞觀之治,四海昇平,民間殷實富足,長安城內平時連打架的混混都沒幾個,實在缺乏熱鬧可看。而康平坊、長樂坊那種銷金窟,又不是人人都花費得起。所以,聽掌櫃胡子曰講古,就成了街坊鄰居們最喜歡的樂趣。...
快活樓位於長安西市口兒,正對群賢坊。老闆姓胡,名子曰,江湖人稱及時雨。手持一套鍋鏟,悶燉燒烹皆不在話下。尤其是瓦罐葫蘆頭 ,堪稱長安一絕。無論才子佳人,還是販夫走卒,吃了之後,皆連挑大拇指。除品嘗瓦罐葫蘆頭一飽口福之外,在快活樓吃飯,還有白賺了一項福利,就是聽胡子曰講古。
眼下時逢貞觀之治,四海昇平,民間殷實富足,長安城內平時連打架的混混都沒幾個,實在缺乏熱鬧可看。而康平坊、長樂坊那種銷金窟,又不是人人都花費得起。所以,聽掌櫃胡子曰講古,就成了街坊鄰居們最喜歡的樂趣。...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看熱鬧的不嫌事大
第二章 鬧市相逢且按劍
第三章 家族與大局
第四章 我只要血債血償
第五章 朝廷有朝廷的難處
第六章 軟肋
第七章 九孔玲瓏心
第八章 血親復仇
第九章 我不當大哥好多年
第十章 雖千萬人吾往矣
第十一章 知道
第十二章 送上門的兩頭肥羊
第十三章 大善人蘇涼
第十四章 狼窩乳虎
第十五章 故事裡和故事外
第十六章 匕首與火焰
第十七章 魔高一丈
第十八章 插翅難逃
第十九章 生死一線
第二十章 狼子野心
第二十一章 心中的光
第二十二章 朋友
第二十三章 籠中雀
第二十四章 意外 ...
第二章 鬧市相逢且按劍
第三章 家族與大局
第四章 我只要血債血償
第五章 朝廷有朝廷的難處
第六章 軟肋
第七章 九孔玲瓏心
第八章 血親復仇
第九章 我不當大哥好多年
第十章 雖千萬人吾往矣
第十一章 知道
第十二章 送上門的兩頭肥羊
第十三章 大善人蘇涼
第十四章 狼窩乳虎
第十五章 故事裡和故事外
第十六章 匕首與火焰
第十七章 魔高一丈
第十八章 插翅難逃
第十九章 生死一線
第二十章 狼子野心
第二十一章 心中的光
第二十二章 朋友
第二十三章 籠中雀
第二十四章 意外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