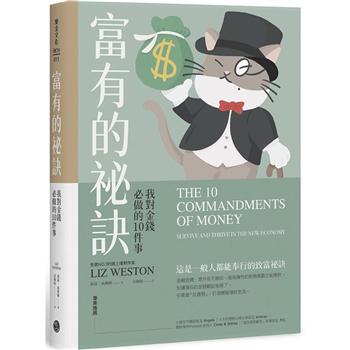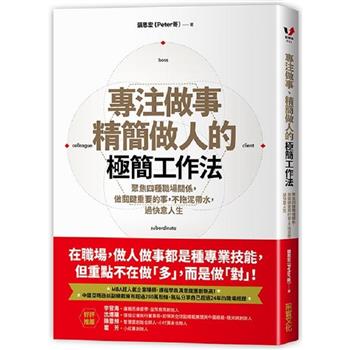時隔七年,
期待已久的村上春樹最新長篇小說!
塵封已久的故事再次開始述說,
帶你進入村上春樹沉靜深邃的祕密世界
我多麼強烈地想要進到那座城,
想去那裡見真正的妳……
夏天的黃昏,十六歲的妳對十七歲的我說起那座城的故事,城被高牆團團圍住,牆只有一個門,由一個頑強的守門人守護著。在那裡的妳既不作夢,也不流淚。然而,住在那裡的妳才是真正的妳,此時此地的妳只是像替身那樣的存在。
因為我真的非常想見妳,便決定出發去那裡尋找在圖書館工作的妳。這是個一本書也沒有的圖書館,架子上排列的只有「古夢」,而我在這個圖書館被賦予了「夢讀」這樣的任務,也就是負責閱讀古夢。
城與牆、神祕圖書館、蛋形的古夢,還有妳……村上春樹在這部小說中,再次構造出了一個完好終結的奇異故事,帶你進入一個沉靜深邃的祕密世界。
│只要想去就行了。
不過發自內心地期望,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在那段期間可能必須拋棄各種東西。
對你來說,很重要的東西噢。
然而不要放棄。因為無論要花多少時間,城都不會消失。
我在疫情在日本開始猛烈爆發的三月初,正好開始寫這部作品,花了將近三年時間完成。在那之間幾乎沒有外出,也沒有長期旅行,我就在那相當異樣,而且頗為緊繃的環境之下,每天持續寫著這部小說(簡直像「夢讀」在圖書館讀「古夢」那樣)。那樣的狀況可能意味著什麼,或者什麼也不意味。不過應該有意味著什麼吧。我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村上春樹
作者簡介:
村上春樹
1949年生於日本京都府。早稻田大學戲劇系畢業。
1979年以《聽風的歌》獲得「群像新人賞」,新穎的文風被譽為日本「八○年代文學旗手」,1987年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出版,奠定村上在日本多年不墜的名聲,除了暢銷,也屢獲「野間文藝賞」、「谷崎潤一郎賞」等文壇肯定,三部曲《發條鳥年代記》更受到「讀賣文學賞」的高度肯定。此外,並獲得桐山獎、卡夫卡獎、耶路撒冷獎和安徒生文學獎。除了暢銷,村上獨特的都市感及寫作風格也成了世界年輕人認同的標誌。
作品中譯本至今已有60幾本,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及採訪報導等。
長篇小說有《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尋羊冒險記》、《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國境之南、太陽之西》、《發條鳥年代記》三部曲、《人造衛星情人》、《海邊的卡夫卡》、《黑夜之後》、《1Q84 Book1》、《1Q84 Book2》、《1Q84 Book3》、《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刺殺騎士團長》、《城與不確定的牆》。
短篇小說有《開往中國的慢船》、《遇見100%的女孩》、《螢火蟲》、《迴轉木馬的終端》、《麵包店再襲擊》、《電視人》、《夜之蜘蛛猴》、《萊辛頓的幽靈》、《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東京奇譚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第一人稱單數》。
紀行文集、海外滯居記、散文、隨筆及其他有《遠方的鼓聲》、《雨天炎天》、《邊境‧近境》、《終於悲哀的外國語》、《尋找漩渦貓的方法》、《雪梨!》、《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象工廠的HAPPY END》、《羊男的聖誕節》、《蘭格漢斯島的午後》、《懷念的一九八○年代》、《日出國的工場》、《爵士群像》、《地下鐵事件》、《約束的場所》、《爵士群像2》、《村上收音機》、《村上朝日堂》系列三本、《給我搖擺,其餘免談》、《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村上春樹雜文集》、《村上收音機2:大蕪菁、難挑的酪梨》、《村上收音機3:喜歡吃沙拉的獅子》、《身為職業小說家》、《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棄貓 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村上T 我愛的那些T恤》、《村上私藏 懷舊美好的古典樂唱片》、《村上私藏 懷舊美好的古典樂唱片2》。
譯者簡介:
賴明珠
1947年生於台灣苗栗,中興大學農經系畢業,日本千葉大學深造。回國從事廣告企畫撰文,喜歡文學、藝術、電影欣賞及旅行,並選擇性翻譯日文作品,包括村上春樹的多本著作。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閱讀的過程中,我心裡充滿幸福。那是不被任何人打擾的純淨幸福。謝謝這本書帶給我這種感受。
——吉本芭娜娜(作家)
一切都始於「妳」的消失。城裡的「妳」失去了與「我」之間的記憶。然而我依然追尋著真正的「妳」,執著於這場垂直移動。無論在黑暗中挖掘多深,「妳」都不會回來;無論攀上多高的牆,所見的也只有虛空。
——小川洋子(作家)
沒有任何停滯,平順浸透到體內的淺顯而節奏感極佳的文字,高明到近乎藝術的句讀使用……累積而成的技術造就這個淺白卻又難解的故事,逼近「講述無法以言語描述的事物」此一文學的核心。
——小川哲(作家)
名人推薦:閱讀的過程中,我心裡充滿幸福。那是不被任何人打擾的純淨幸福。謝謝這本書帶給我這種感受。
——吉本芭娜娜(作家)
一切都始於「妳」的消失。城裡的「妳」失去了與「我」之間的記憶。然而我依然追尋著真正的「妳」,執著於這場垂直移動。無論在黑暗中挖掘多深,「妳」都不會回來;無論攀上多高的牆,所見的也只有虛空。
——小川洋子(作家)
沒有任何停滯,平順浸透到體內的淺顯而節奏感極佳的文字,高明到近乎藝術的句讀使用……累積而成的技術造就這個淺白卻又難解的故事,逼近「講述無法以言語描述的事物」此一文...
章節試閱
1
妳告訴我那座城的事。
那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我們聞著青草鮮美的氣味,沿著河往上游走。越過幾處攔沙壩形成的小流瀑,偶爾停下腳步,看看小水潭裡游泳的銀色小魚群。兩個人從剛才就已經開始打赤腳。澄清的水涼涼地洗著腳踝。河底細細的沙軟軟地包著兩個人的腳--就像夢中柔軟的雲一樣。我十七歲,妳小我一歲。
妳將紅色低跟涼鞋隨意塞進黃色塑膠單肩包,在我稍前方,不斷從一個沙洲走向下一個沙洲。濡溼的草葉黏在濡溼的小腿肚上,形成美麗的綠色逗點。我則把穿舊的白色運動鞋提在手上。
妳好像走累的樣子,隨意就在夏草中坐了下來,什麼也沒說,抬頭望著天。兩隻小鳥並排快速飛過天空,發出尖銳的啼聲。沉默中,黃昏泛藍的餘暉開始包圍我們。我在妳身邊坐下時,心情變得有點不可思議。簡直像有幾千條眼睛看不見的絲線,把妳的身體和我的心細密地綁在一起似的。妳的眼睛瞬間一眨,或嘴唇輕微一牽動,都讓我心神動搖。
在那樣的時刻,無論妳我都沒有名字。只是十七歲和十六歲的夏天黃昏,河邊草地上色彩鮮明的想念--就只是這樣。不久後,我們頭上可能會逐漸開始有星星閃爍,但星星也沒有名字。在沒有名字的世界,河邊的草地上,我們並排坐著。
「城被高牆團團圍住。」妳開始說。從沉默的深處找到話題。就像隻身潛入深海裡尋找珍珠的人那樣。「不是多大的城。但也沒有小到能一眼望穿。」
這是妳第二次提到那座城。就這樣,城的周圍有了高牆。
隨著妳繼續說,那座城就有了一條美麗的河與三座石砌的橋(東橋、舊橋、西橋),有圖書館和瞭望臺,有廢棄的鑄造工廠和樸素的集合住宅。夏天將近黃昏的淡淡光線中,我和妳,並肩眺望那座城。有時從遙遠的山丘瞇細眼睛看,有時從近得可以觸摸的距離睜大眼睛看。
「真正的我生活的地方,是在被高牆圍繞的那座城裡。」妳說。
「那麼,現在坐在我面前的妳,不是真正的妳嗎?」我當然就這樣問。
「對,現在這裡的我,不是真正的我。只是替身而已。只不過像是移動的影子那樣的東西。」
我想了一下。像移動的影子那樣的東西?不過這意見我決定現在暫時保留。
「那麼,在那座城裡真正的妳在做什麼?」
「我在圖書館上班。」妳以安靜的聲音回答。「工作時間從傍晚五點左右到晚間十點左右。」
「左右?」
「在那裡所有的時刻都是大概的。中央廣場雖然有高高的鐘塔,但那鐘卻沒有指針。」
我腦子裡想像沒有指針的鐘塔。「那麼,那圖書館是誰都可以進去的嗎?」
「不。不是誰都可以隨意進去,要有特別資格才能進去。不過你可以進去。因為你有那個資格。」
「是什麼樣的特別資格?」
妳微微一笑,卻沒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只要去到那裡,我就可以見到真正的妳,對嗎?」
「如果你能找到那座城的話,而且如果……」
說到這裡,妳閉上嘴,臉頰泛起淡淡的紅暈。但我可以聽到妳沒說出口的心聲。
而且如果你是真的,需要真正的我的話……這是當時妳刻意不說出口的話。我伸出手臂輕輕環抱妳的肩。妳穿著無袖的淺綠色洋裝,臉頰靠著我的肩膀。然而那個夏天傍晚我環抱著肩的,並不是真正的妳。正如妳說的,那只是妳的影子替身而已。
真正的妳,是在被高牆圍繞的城裡。那裡有川柳茂盛的美麗沙洲,有幾處小高丘,到處可見生著獨角的安靜獸群。大家住在老舊的集合住宅裡,生活簡樸但沒有任何不便。成群的獸愛吃城裡自然生長的樹葉和樹果,但在積雪的漫長冬季,大部分都熬不過嚴寒與飢餓而喪生。
我多麼強烈地想要進到那座城,想去那裡見真正的妳。
「城被高牆圍繞著,非常難進去。」妳說。「要出去就更難了。」
「要怎麼樣才能進去?」
「只要想去就行了。不過發自內心地期望,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在那段期間可能必須拋棄各種東西。對你來說,很重要的東西噢。不過不要放棄。因為無論要花多少時間,城都不會消失。」
我想像在那座城裡遇到真正的妳。腦海裡浮現出城外美麗而茂盛的廣大蘋果林,河上的三座石橋,想像看不見蹤影的夜啼鳥的叫聲。還有真正的妳工作的古老小圖書館。
「那裡一直都有為你保留的位置。」妳說。
「為我保留的位置?」
「是啊。城裡只有一個空職。正好適合你。」
那究竟是什麼樣的職位呢?
「你會成為『夢讀』噢。」妳小聲說。好像在告知一件重要的祕密似的。
我聽了,不禁笑出來。「嘿,我連自己做過的夢都記不住。這樣的人要當個『夢讀』,恐怕很難吧。」
「不,『夢讀』不需要自己做夢。只要在圖書館的書庫裡,讀那裡收藏的許多『古夢』就行了。不過那並不是誰都能做的事。」
「可是我能做是嗎?」
妳點頭。「對,你能做。你有那個資格。而且在那裡的我會協助你做那件工作。每天夜晚陪在你身邊。」
「我是『夢讀』,每天晚上在城裡圖書館的書庫,讀許多『古夢』。而且身邊總是有妳陪伴。真正的妳。」我把得知的事重複說出。
在我的臂彎中,穿著綠色洋裝的妳,裸露的肩膀微微搖動。然後忽然僵住。「是啊,不過有一點希望你能記住。就算我在那座城裡遇見你,在那裡的我,也完全不會記得任何有關你的事。」
為什麼?
「你不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對,我現在這樣輕輕摟著的肩膀,只是妳的替身而已。真正的妳住在那座城裡。有高高的牆團團圍住的,那座遙遠的神祕城市裡。
然而在我掌中的妳,肩膀非常光滑而溫暖,我只覺得就像真正的妳的肩膀一樣。
2
在這真實的世界,我和妳住在稍微有一點距離的地方。雖然不太遠,但也不太近,不能心血來潮想見面就馬上去見。得要轉兩次電車,花一個半小時,才能到妳住的地方。而且我們住的城市都沒有圍著高牆,所以當然來去都是自由自在的。我住在海附近的郊外安靜的住宅區,妳住在大得多的都心鬧區。那年夏天,我高中三年級,妳二年級。我上的是本地的公立高中,妳上的是妳那裡的私立女中。因為一些緣故,我們實際見面一個月頂多一兩次而已。幾乎是輪流的,我會去走訪妳住的城市,妳會來我住的地方玩。當我去拜訪妳的城市時,我們會到妳家附近的小公園,或公共的植物園。要進植物園必須買入場券,不過園內溫室旁有一家通常人不多的咖啡店,成了我們最喜歡去的地方。在那裡我們可以點咖啡和蘋果塔(小小奢侈一下),兩個人還可以私下講悄悄話。
妳來我住的地方時,我們大多兩個人在河邊或海邊散步。妳家在都會中心,附近沒有河,當然也沒有海,所以妳來我這邊時,首先就會想看看河或海。這裡大量天然的水——吸引了妳的心。
「看到水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就覺得很舒坦。」妳說。「我喜歡聽水發出的聲音。」
自從去年秋天在一個機緣下認識之後,我們親密地交往了大約八個月。每次見面,都會盡量避開別人的眼光,在隱蔽的地方互相擁抱,悄悄親吻。不過並沒有進入更深的關係。一個原因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另一個現實上的因素是,找不到結成親密關係的適當場所。不過其實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我們更珍惜單獨相處的時間,專心談兩個人的私事吧。因為過去我跟妳都從來沒有遇到過能夠這麼自由又自然地,把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原原本本說出口的對象。能夠遇見這樣的對象,感覺簡直就像奇蹟似的。因此每月見到一次或兩次時,我們總是忘記時間的經過只顧交談。無論講多久,話題都講不完。到了該分手的時候,在車站的剪票口告別時,每次都覺得還有很多重要的事忘記說。
當然我的身體並不是沒有欲求。十七歲的健康男生,站在胸部美麗隆起的十六歲女孩面前,更何況手還環抱住那柔美的身體時,沒有性的欲求是不可能的。但我本能地感覺到,那可以留到很久以後。現在我必須做的事,是一個月見妳一兩次,兩個人一起長途散步,一邊坦白地談談各種事情。互相告知親密的話題,對彼此增進了解,然後到某個樹蔭下互相擁抱、親吻——在這樣美好的時光中,我並不想匆忙地帶進其他要素。我怕那樣一來,會破壞當下的什麼重要大事,此後再也無法恢復成原狀。身體的事情等以後再說吧。我這樣想。或者直覺這樣告訴我。
不過,那時候兩個人面對面,額頭靠在一起,到底談了些什麼?到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大概是因為談了太多事情,沒辦法一一想起來。不過自從妳談到那高牆圍繞的特殊的城之後,那就占了我們談話的主要部分。
主要是由妳述說那座城的構造,我對那提出實際的疑問,由妳回答的這種形式,決定城的具體細節,並記錄下來。那座城本來就是由妳所造的,或者從以前本來就已經存在於妳內部的東西。不過那能發展成眼睛看得到、語言能描寫出來的東西,我想我也出了不少力氣。由妳述說,由我留下紀錄。就像古代的哲學家和宗教家背後都分別跟隨著忠實細心的記錄者,或是被稱為信徒的人那樣。我也擔任認真的書記、忠實的信徒,備有隨時記錄的專用小筆記本。那年夏天,我們兩人全心投入這份共同作業。
3
秋天,那些獸的身體,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寒冷季節,全身已覆蓋光輝的金色體毛準備過冬,額頭上生出尖銳的白色獨角。牠們以冷冷的河水洗著四蹄,伸長脖子咬著紅色的樹果,嚼著金雀花的葉子。
好個美麗的季節。
站在沿牆設立的瞭望臺上,我等待著黃昏夕暮的角笛。太陽西沉的稍前時刻,角笛一長三短地吹響起來。這是個慣例。柔軟的角笛聲,滑過夕暮餘暉中的石板路。角笛聲響可能數百年(或更漫長的歲月)之間,都不變地重複著。家家戶戶的石壁縫隙裡,或沿著廣場的圍牆排列的石像之中,也深深浸入了那音色。
當角笛的聲音響遍城中,整群獸就同時抬起頭,望向太古的記憶。有些停止咬噬樹葉,有些停止喀茲喀茲敲打著道路的蹄聲,有些從最後的夕陽裡午睡醒來,分別朝相同的角度抬頭仰望。
一切在一瞬之間,像雕像般被固定下來。在動的東西,只有牠們那被微風吹動的金色柔軟體毛。不過,牠們到底在看著什麼?那些獸,頭都轉向一個方向,固定看著天邊,動也不動一下。就那樣側耳靜聽著角笛的聲響。
當角笛的最後聲響被吸進空中消失時,有些獸併攏前腳站起,有些獸伸展身體調整姿勢,幾乎同時開始走動起來。一時的禁錮解除了,於是整條街都被群獸踏出的蹄聲所充滿。
群獸的行列隨著曲折的石板路往前進。並沒有由誰來帶隊,也沒有由誰在領導。這些獸就只是低垂著眼睛,稍微左右搖擺著肩膀,走下沉默的河邊。雖然如此,獸與獸之間,看來似乎仍然具有難以消除的緊密連結。
經過幾次觀察,就會逐漸發現獸群所經過的路線和速度好像有嚴密的規則。牠們在途中一邊到處讓新的夥伴加入群體,一邊越過曲線和緩的舊拱橋,走到有銳利尖塔的廣場(正如妳所說的,那裡鐘塔的時鐘,兩根指針已經遺失了)。在那裡,會讓走下沙洲吃著綠草的一小群獸加入。接著沿河邊的道路朝上游前進,循往北延伸的乾涸運河穿過工業區,讓一群正在森林間尋找樹果吃的獸也加入陣容。然後轉變方向朝西走,鑽過鑄造工廠有屋頂的穿廊,往北朝山丘走上長長的階梯。
環繞著城的圍牆只有一道門。負責那道門的開關,就是守門人的任務。門上縱橫釘著厚鐵板,形成厚重而堅固的門。但是守門人可以輕易推開和關閉那扇門。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則不許碰那道門。
守門人身體非常健壯,而且是一個非常忠於自己職責的高大男人。尖形的頭剃得乾乾淨淨,容顏經常保持光滑潔淨。他每天早晨燒一大鍋熱水,用大而銳利的剃刀仔細地剃頭、刮臉。看不出年齡多少。早晚吹響角笛,聚集獸群是他的職務之一。他會站上守門人小屋前兩公尺高左右的高臺,朝天空吹響角笛。這位生得粗魯、外表近乎卑賤的男人,到底是從哪裡吹出如此柔和而優美的聲音呢?每次聽見角笛聲,我都覺得不可思議。
到了傍晚把成群的獸一隻不剩地放出牆外之後,他又再度把沉重的門關閉起來,最後把大鎖套上,發出喀嚓一聲乾脆冰冷的聲音。
北門外有特別為獸而設的場所。獸在那裡睡覺、交尾、生產小獸。那裡有森林、有樹叢,也有小河流過。而且那裡也有牆圍繞著。雖然只不過是高度一公尺多一點的矮牆,但不知道為什麼,那些獸都無法翻越那道牆。也或許是無意翻越。
門兩側的牆,設有六棟瞭望臺。瞭望臺附有古老的木製螺旋階梯,誰都能登上那裡。從瞭望臺可以一眼望穿獸群的居住場所,不過平常誰也不會上去。城裡的居民對獸群的生活似乎毫不關心。
不過只有初春的一星期之間,大家會為了觀看獸群激烈的爭鬥模樣,而刻意登上牆裡的瞭望臺。獸群在這段時期,會變成從平常的姿態難以想像的粗暴,雄獸會為了追求或爭奪雌獸,廢寢忘食,拚死爭鬥。一邊發出呻吟吼叫聲,一邊試圖以尖端銳利的獨角,猛烈地刺穿競爭對手的喉嚨或腹部。
只有在這交尾期的一星期之間,獸不會進城裡來。因為守門人顧慮到城裡眾人的安全,為了防止發生危險,會把門關上(因此在這期間,晨昏的角笛也停止吹響)。不少獸在爭鬥中深深負傷,甚至也有獸喪失生命。而在流淌到地面的鮮血中,新的秩序和新的生命也於焉誕生。就像初春時節柳樹一口氣發出新綠的嫩芽那樣。
獸群以我們所無法窺知的獨特生命循環和秩序生存著。一切都規規矩矩地反覆循環,以牠們自己的鮮血換來秩序。那粗野激烈的一星期過後,柔軟溫和的四月的雨把鮮血洗清時,那些獸又再度恢復寧靜溫和的模樣。
不過,我並沒有以自己的眼睛實際目睹那樣的光景。只是從妳這裡聽過而已。
秋天裡,那些獸分別在各自所在的地方蹲坐著,金色的毛在夕陽下閃著光輝,牠們在無言中持續等待著角笛的聲響被吸進天邊。那頭數恐怕不下千頭。
城的一天就這樣結束了。日子過去,季節移轉。不過無論日子或季節終究只是短暫的。城本來的時間,還是在別的地方。
4
我和妳都不會造訪彼此的家。既沒見過對方的家人,也沒介紹給彼此的朋友認識。簡單來說,我們不想被別人——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人——打擾。我和妳,只要共度屬於兩人的時光就十分滿足了,不想再增加其他任何的什麼。此外,光從物理上的觀點來看,也沒有附加任何東西的餘地。前面也說過,我們之間要說的話堆積如山,兩人能在一起的時間卻很有限。
妳幾乎不談自己的家人。關於妳的家人,我所知道的只有少數幾件零星的事情。父親原本是地方上的公務員,在妳十一歲的時候,因為發生某件疏失而不得不辭職,目前在補習班當職員。至於是怎麼樣的「疏失」則不清楚。不過,似乎是讓妳不願說出口的那類問題。妳的生母在妳三歲時因內臟的癌症而過世,妳對她幾乎沒有記憶,也不記得她的容貌了。妳五歲時父親再婚,第二年妹妹出生。所以現在的母親對妳來說是繼母,但比起對父親,妳對母親「可能還稍微親近一點」。這是有一次妳稍微提到的,就像寫在書頁角落的小字,沒有深意的注解那樣。關於小六歲的妹妹,除了「妹妹對貓毛過敏,所以我們家不能養貓」之外,就沒有多說別的。
妳小時候打從心裡自然而然覺得親近的,只有外婆。妳一有機會就搭電車到鄰區的外婆家去,學校放假的時期也會在那邊住幾天。外婆無條件地疼愛妳,也會從她微薄的收入中掏出錢來買一些小東西給妳。但每次去見外婆時,都會看到繼母露出不滿的表情,雖然她口頭上並沒說什麼,但妳也逐漸少往外婆家去了。這位外婆幾年前也因心臟病忽然去世。
這些事情妳都斷斷續續一點一滴地告訴我。就像從舊大衣口袋裡,一點一點掏出些破舊的東西那樣。
還有一件事,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每次妳提到家人時,不知道為什麼總是盯著自己的手掌看。就像為了理出話題的頭緒,必須看著眼前的手相(或什麼)細細解讀才行似的。
1
妳告訴我那座城的事。
那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我們聞著青草鮮美的氣味,沿著河往上游走。越過幾處攔沙壩形成的小流瀑,偶爾停下腳步,看看小水潭裡游泳的銀色小魚群。兩個人從剛才就已經開始打赤腳。澄清的水涼涼地洗著腳踝。河底細細的沙軟軟地包著兩個人的腳--就像夢中柔軟的雲一樣。我十七歲,妳小我一歲。
妳將紅色低跟涼鞋隨意塞進黃色塑膠單肩包,在我稍前方,不斷從一個沙洲走向下一個沙洲。濡溼的草葉黏在濡溼的小腿肚上,形成美麗的綠色逗點。我則把穿舊的白色運動鞋提在手上。
妳好像走累的樣子,隨意就在夏草中坐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