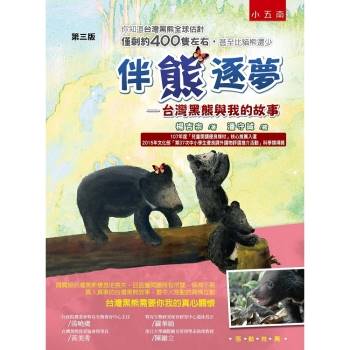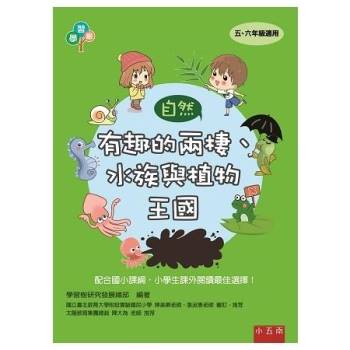名人推薦:
自己的勝利 言叔夏
這幾年常收到鴻祐寄來的出版社贈書。疫情期間他口考後,我們就維持斷續的聯繫。常是公事:關於邀序或掛名推薦之類的往返。因我事忙,而且有死線焦慮,常相當不好意思地推辭了這些邀請。他寄書來也寄得不動聲色,好像只是每月寄來一張明信片,告訴你他還有在上班(欸)。也甚少再知道他還有沒有繼續寫小說:因他在寫作這件事本身,好像從來不是張揚的人。鮮少會如某些寫作者,在作品之前,先把某些顯性的物件擺放出來(這話說得不盡精準。或者該說,在作品現身的同時,你很快會一眼看到那並置的、明顯的「什麼」──)。他不是這個路數。他的小說常是有意識地保持一層和世界之間冷淡乾硬的透明薄膜。那如同昆蟲脫蛻的隱翅,世界新陳代謝後所殘留的剩餘,被拿來綴補成一種觀察道具。如同〈烏鴉與猛獁〉裡,視網膜破掉後的主角,透過那殘餘的蛛網看出去的世界。我常想那是為什麼呢?在這個寫作經常挾帶某種演出性的時代,這種退後有時會讓人浮現夜市裡撈金魚的攤位前,當其他小孩都緊盯著水池裡的金魚,有個小孩卻一直很在意手中破掉的紙網,該怎麼重複補葺,才能永遠不會再破。他可能一直坐在那個攤位前,整晚修補著他的網子,而最終忘記了那些池裡的金魚嗎?那張網,變成他小說裡外最重要的指涉物,既是形式的,也是內容物的。
收在《烏鴉與猛獁》裡的八篇小說,圍繞著一種生命的破洞而開展,作者顯然有意識地在情節的困境與困境之間,鍛造某種關乎救贖的脆弱性。這些角色多是一代青年側像的某種速寫或描繪,漫漶一種虛無氣息。其中某些篇章甚至會讓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中國作家胡遷的〈大象席地而坐〉,那座現實中並不存在的花蓮市動物園:虛無的中國青年在某種人生的困境裡,來到花蓮,吃過了東大門夜市,喝過了瑞穗牧場鮮奶(他還跟團去了太魯閣,疑似走了砂卡礑步道──)。小說的最末,他終於來到那座虛構的動物園,為了見一面那隻傳說中一直坐在原地的大象(「這件事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大的一個問題了。」),卻反過來被牠一腳給踩死了。動物園裡的「大象席地而坐」作為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會被這個問題指路或反噬?我無法回答。但《烏鴉與猛獁》的同名短篇裡,也有一座幾近虛構的動物園:自稱社畜(因而牠總是被豢養)的臺灣青年,每天都在辦公室電腦裡偷偷搜尋臺灣各地的動物園。他沒寫出任何關於動物園的提案,就因為車禍腿傷而回到老家,無法再繼續上班。而他的動物園提案,則其實來自他視網膜破洞前的一個夢:「我在偌大的動物園裡迷路,一直找不到離開的方法。」這座夢中的動物園,彷彿透過視網膜的破洞,像襪子的洞口般反折出夢境的內裡──將作為現實反面的夢境,推出夢外,變成現實裡真實存在的夢魘。
這些難解的現實,層層疊疊,構成了小說裡敘事者的邊界。在可為與不可為之間,小說裡的角色多半嘗試摸索出一條自己的法則,做最小程度的、只有自己知道的抵抗。他們就如同〈鄰居〉裡因為家暴陰影而加入佛教團體的瓊枝,為了找回「自己的勝利」──「她的勝利條件,是不服從,是小小的抵抗,是不給予那些別人希望她表達的:譬如驚駭、哭、無助的眼神。」這會是他形式上的一個端倪嗎?總的來說,這八個短篇似乎都戮力於把握一種收束的節制感,在理應(或容易)戲劇性的地方戛然而止。那似乎也不見得應歸納為一種技巧的展演,而更接近一種對情緒演出的潔癖或倔強。它所指涉的對象物大抵是一種空白──創傷彷彿只是生命中的某種鑲嵌,被填補進一個老早即存在彼處的空缺,而從這空缺中長出的義肢或金屬手指,日復一日地,代替我們活下去。書中最具象的一篇,或正是以八仙塵爆作為背景的〈脛骨之海〉。樂園爆炸時,青年的時間被中止了。他成為一個需要重新練習走直線、使用輔助器行走的男人。他的母親告訴他:「你人還活著就好,錢也沒關係。我們可以重新開始──」;然而,「重新開始」是可能的嗎?如同塵爆所摧毀的人生,一旦被截斷,該如何從那接銜起來的「中間」開始活下去?小說裡的青年後來成為一個外送員。有些殘忍的片段,以屏息口吻,寫那遮掩在長褲底下、套在一雙愛迪達球鞋上的義肢,幾乎可聽見機械轉軸喀啦喀啦的聲響。但微妙的是,正是在這樣一個以煙火作為創傷事件的故事裡,儘管有著技術上難以忽略的痕跡,他仍讓這篇小說終止於創傷事件後,一場自己為自己燃放的煙火。他是想活下去的罷?
我想起剛到東海任教的那段時間,可能我太常在課堂放些來源不明的可疑電影,於是有人就提議不如課後我們自己借教室來舉辦快閃電影院。鴻祐也是其中之一。大概也曾在人文大樓的深夜五樓裡,一起看過不知哪裡傳來的一部四小時〈大象席地而坐〉?夜間長片散場時,最讓人不知所措的,大概是夜仍深長,更顯得現實的世界無處可去。我們去了一個四小時外的世界度過了他人漫長的一生,像穿過誰的視網膜破洞,回到了螢幕以外的世界,卻發現這裡的黑夜還沒有結束。現在回想起來,那種「還沒有結束」,正是烏鴉與猛獁開始出沒的時間。它沒有終點,只能以寫作與之驅逐。就如同小說裡那座沒有盡頭的夢中動物園,無論如何也走不出去。但如果它足夠幸運,在遙遠的未來,「還沒有結束」這句詛咒般的話語,或許也能夠在書寫的行動裡被抽換詞意,改寫成一句反語:「還沒有結束」,就是一種「重新開始」;重新成就一張關於動物園的地圖。那或許,就是他給他自己指路的開始。
消失的故事與復原競爭 何致和
──趙鴻祐《烏鴉與猛獁》的創新啟程
近年來,臺灣短篇小說集的出版呈現蓬勃發展,其中湧現了許多新銳作家的作品。這股現象的背後,或許與文學獎的普及、各類文藝機構提供的寫作補助,以及有越來越多的創作研究所的學生完成學業取得藝術碩士畢業有關。將得獎作品結集出版,或直接發表畢業創作,已成為新人作家踏入文壇的一種常見途徑。
鴻祐也不例外,選擇以短篇小說集《烏鴉與猛獁》作為他的第一本書。儘管他並非創作研究所科班出身,但他就讀的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提供多元化的畢業方式,允許學生以文學創作作為碩士論文,不過仍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二○二二年,在言叔夏老師的邀請下,我與吳明益老師共同擔任鴻祐畢業創作──短篇小說集《深穴海馬迴之歌》的審查口試委員。那是我第一次完整閱讀他的創作,當時就對他作品的深度與獨特性留下了深刻印象。
兩年後,當出版社編輯來信告訴我鴻祐即將出版他的第一本書,並邀請我為他寫一篇推薦文,理由是我曾擔任過他的口試委員,還提到這本小說集是「由鴻祐的碩士論文做部分修改增寫而成」。那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主要原因是,我在口試時已經讀過他的作品,感覺頗佳。其次,我認為這些作品我都讀過了,只要稍微再重溫一下,就能寫出我對這些作品的看法,應該不會花太多時間。
但當我拿到出版社提供的書稿時,越看越覺得奇怪,為什麼這些作品完全沒有我曾讀過的印象?難道是我記憶力衰退了?我懷疑地找出趙鴻祐當年的畢業作品,比對後才發現,這哪裡是「部分修改增寫」?兩年前的畢業作品只剩下一篇,其他的都不見了。這本小說集中的八篇作品,有七篇是我從未讀過的全新創作。
這個發現讓我既欣喜,又感到巨大的壓力。高興的是,鴻祐為了創作成長,竟能捨棄已完成且具出版水準的畢業作品,選擇創作全新內容,這樣的決心令人敬佩。另一方面,這也讓我感到壓力,因為這些全新的作品需要重新細讀,才能寫出像樣的推薦文。而我的時間有限,擔心匆忙閱讀會讓文章流於膚淺,辜負了編輯和作者的期望。
兩年前,鴻祐的畢業作品曾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他偏好描寫具有私密與神祕感的空間,擅長透過意象隱喻與心理描寫營造情境氛圍,故事經常聚焦於認同與孤寂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在《烏鴉與猛獁》的作品中,這些特色依然可見,但表現手法與視野已有顯著突破。兩年前,他的創作功力已足以讓同輩寫作者難以追趕,如今他更是大幅超越了自己。讀完這本小說集,我才深刻體會到鴻祐對創作的熱情與信念,這部作品絕非他碩士作品的簡單延續,而是一次創作上的蛻變與突破,展現了令人讚嘆的企圖心。
例如,作品集中的〈脛骨之海〉以二○一五年八仙樂園塵爆事件為背景。雖然他並非第一個書寫此事件的作者,但選擇在事件發生九年後重訪這段歷史創傷,體現了對議題的深刻反思。鴻祐以小說將塵爆與太陽花學運並置,將個體與集體的創傷相連,直面社會對痛苦的選擇性記憶。故事以第三人稱視角細膩描繪受害者的苦難,揭示了「競爭性復原」的荒謬:在社會眼中,有人因傷痛被塑造成英雄,有人卻遭受冷嘲熱諷,甚至在復原過程中也要面對無形的比較與壓力。透過這篇作品,鴻祐呈現出更為成熟的創作視野與社會洞察。他以小說為媒介,勇於揭示偏見與不公,並以冷靜卻深刻的筆觸質問社會對傷痛的選擇性記憶,讓小說成為對現實的有力提問,也體現了他在創作深度上的突破與成長。
又如〈水造的路徑〉,探討自然與人為災難對生命的改變,同樣聚焦於傷痛與復原的主題。小說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主角為中心,描寫其同時活在過去與現在災難中的狀態。在山難事件中,他意外與昔日的霸凌者及另一場災難的倖存者阿村相遇,複雜的人物關係與事件交織成一張情感與記憶的網絡。但鴻祐的重點不在於梳理事件本身,而是探索倖存者如何面對創傷與內心的矛盾。小說還巧妙融入現實議題,如臺灣行人安全,從日常層面反映倖存者被擾亂的心境,進一步深化情感層次。透過開放式結局,故事拋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倖存者該如何真正解開時間的糾纏,找到通往和解與重生的道路?這篇作品展現了作者對生命議題更深入的思考與更細膩的處理手法,觸及了傷痛與復原的本質。
綜觀《烏鴉與猛獁》這部小說集,可發現鴻祐以細膩筆觸,專注於描繪社會邊緣群體的內心世界,聚焦於那些因缺乏支持系統而被主流價值觀排斥的人物。面對生活壓力與內心創傷,他們做出看似偏激的選擇,這些行為看似衝動或自毀,實則深刻反映了他們的無助與掙扎。作者不以道德眼光評判,而以同理心揭示角色的複雜情感與生命困境,小說巧妙地將這些人物置於「中間地帶」──既屬於社會的一部分,又因現代社會的急遽轉型而與主流保持疏離。這個地帶既是他們內心世界的投射,也是其所處的尷尬位置。透過多樣的敘事視角,鴻祐成功讓這些被忽視的個體得以呈現,寫出他們內在的韌性與對生命的渴望,喚起讀者對弱勢群體的更深層反思。
細讀過這些全新的故事,我發現鴻祐的文字更為細膩了,對人物內心的揣摩也更加深刻,情節的安排變得比過去還要縝密緊實。每篇作品的故事和主題各有不同,卻又彼此呼應,如同一幅完整的拼圖。透過這些作品,我不僅感受到他在敘事技巧上的成熟,也看見了他對生命和現實細微之處的觀察和思索。這些發現讓我慶幸鴻祐沒有拘泥於口試時的畢業作品,而是選擇以嶄新的作品集來向讀者展示自己。這樣的創作態度,無疑展現出一位作家對自我要求的嚴格,以及對藝術的不懈追求。作為他的口試委員,我感到欣慰和光榮,也對他的將來充滿期待──期待他的作品能夠觸動更多讀者,期待他在創作道路上繼續突破自我,為我們帶來更多值得細讀與珍藏的作品。
媒體推薦:
這八個短篇似乎都戮力於把握一種收束的節制感,在理應(或容易)戲劇性的地方戛然而止。那似乎也不見得應歸納為一種技巧的展演,而更接近一種對情緒演出的潔癖或倔強。它所指涉的對象物大抵是一種空白──創傷彷彿只是生命中的某種鑲嵌,被填補進一個老早即存在彼處的空缺,而從這空缺中長出的義肢或金屬手指,日復一日地,代替我們活下去。──言叔夏
小說巧妙地將這些人物置於「中間地帶」──既屬於社會的一部分,又因現代社會的急遽轉型而與主流保持疏離。這個地帶既是他們內心世界的投射,也是其所處的尷尬位置。透過多樣的敘事視角,鴻祐成功讓這些被忽視的個體得以呈現,寫出他們內在的韌性與對生命的渴望,喚起讀者對弱勢群體的更深層反思。──何致和
若要肉慾式形容這本小說,我想,是拆封包膜後,在冷不防的閱讀間,指腹被書頁輕劃,血滴涓,微痛頻仍的肢體末端異化感。鴻祐的修辭,具備奇特的乾燥曖昧,那是身為文壇新人確保有「鉛華洗盡」的素直文字,灰冷,沉謐。
此質地與後青春,成長式母題彼此摩挲,如寒冬褪衣所生之靜電,引人刺痛。作者專注的角色,或可稱為「餘境者」,其歷經物理、心理、家庭職場、社會事件切割刺穿過的「以後」。諸多段落能見他對局部動作描繪的慾望,那是劫境方休,角色徘徊在乾燥,凍瑟,充斥消毒氣味的空間(病院或實驗室)裡,孤寂操演著精細步驟的復健療程。
鴻祐的書寫是他自身定義的「拋」。從伏低的預備位置拾起事件,舉起符號,修補過,瞄準讀者。在運動行進後,有些事物,能抵達很遠很遠的地方。
──白樵
《烏鴉與猛獁》最難能可貴的,是敢於在創傷闖入、尋常世界遭懸置的事件視界處,拒絕以廉價的憐憫,化約情感/經驗的複雜性,並能在節制而冷峻的敘說中,指認被拋擲入世的此有,真誠的困惑──「所以到底什麼是『生命』吶?」全書首篇發出的詰問,迴盪在故事中,被災難、社會或他人惡意所壓輾之「倖存者們」的耳際;小說卻不輕易使答案塌縮為一,而是一次次延異自身、抵抗意義的固化,直到這個問題,終於也成為讀者難以擺脫的幻聽。──張桓溢
《烏鴉與猛獁》起首於幻夢,終結於大火,鴻祐念茲在茲的核心,彷彿就是深度的安靜,蒼茫的「沒有」。小說家以清朗的文字,演述生命的創傷:小至視網膜的破洞,脛足的毀損,乃至整個社區的覆滅。正是因為這些苦難,使身體不再是身體,動物也不只是動物──甚至,人也不是人:人在流變,人在消亡,人在逃離他自身。本書是一部小型的「痛史」,鴻祐透過小說捕捉「成為日常」的創傷,並提出追問:「受傷」這件事為什麼是重要的?──陳柏言
這是一本給新世代社畜的格林童話。小說家如同穿著彩衣的吹笛人,引領讀者走入他的故事之中。故事撲朔迷離,幾番轉折,眾人忘記來時路,一心跟著美妙的笛音前進,走向陌生之地。
小說主角是被資本社會牢籠折磨到失去熱情的社畜,也是從天災人禍裡逃過一劫,卻發現「活著比死亡更辛苦」的倖存者。這些人活不出尊嚴,但對於人生卻異常清醒。他們淡薄冷峻,話語尖銳。但他們更懂得熬煮時間,以求報復。不看到最後,誰也不會知曉,致命的一箭到底是誰偷放的。
──劉思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