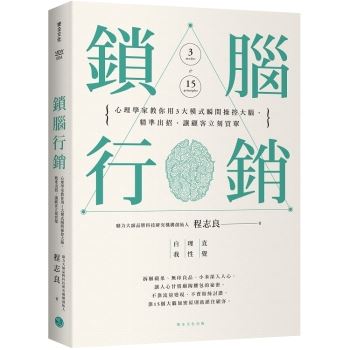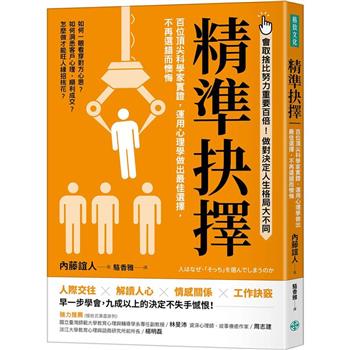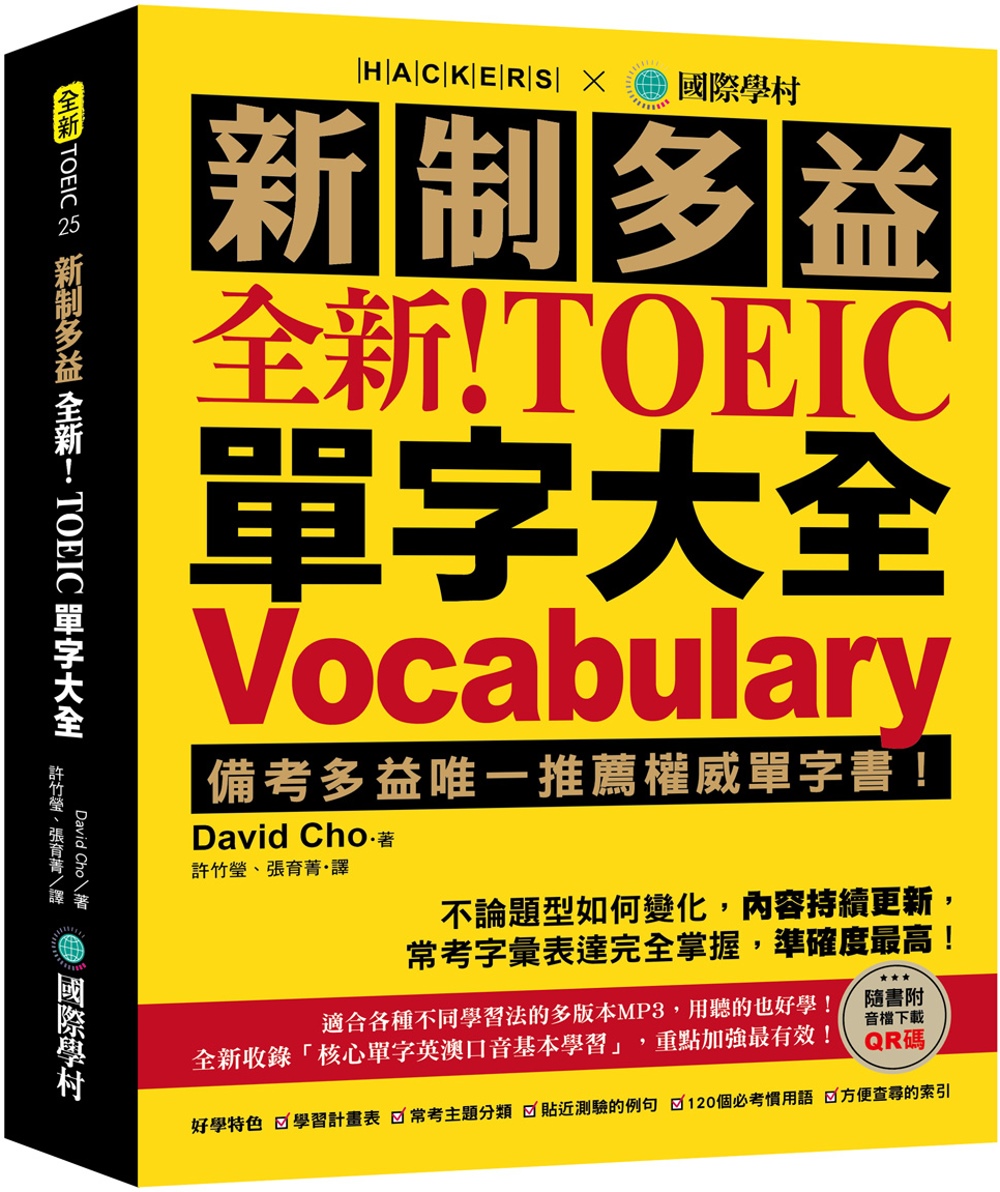第十二章 人間之感
看著跪倒在地的秦風烈,鳴鸞宮弟子都是一愣。
片刻後,有人驚呼出聲,鳴鸞宮弟子瞬間意識到敗局已定,四處逃散而去。
花向晚抬眼揚聲:「慢著。」
音落,一道結界無生地在周邊瞬間升騰而起,一個個弟子撞到結界之上,發現走投無路。
現下高階修士已經逃開,這些弟子慌張得不知所措,他們所有人提劍站在不遠處,勉力支撐著自己不要恐懼,咬牙看著高處的花向晚和謝長寂。
「花少主。」唯有秦雲裳,她一手撐劍,吊兒郎當地站起來,打量著花向晚的狀態,恭敬道:「恭喜花少主步入渡劫。」
「你們鳴鸞宮就是這麼恭喜我的?」花向晚笑起來,盯著秦雲裳:「在我渡劫之時,舉宮之力,來殘害我宗弟子?」
「此事鳴鸞宮的確有愧,但我等都是他人棋子,」秦雲裳回頭看了身後弟子一圈,「是來是走,都由不得我們選擇,還望花少主憐憫我等身不由己,給條生路。」
「我給妳生路,」花向晚盯著秦雲裳,「憑什麼?」
聽到這話,秦雲裳回頭注視著身後弟子。
這些弟子看上去十分緊張,他們看著秦雲裳,目光裡帶著幾分祈求。
秦雲裳明白他們的心意,她回過頭,抬眼看向花向晚,雙手舉劍放在身前,揚聲開口:「鳴鸞宮,降!」
這話一出,眾人心中舒了口氣,鳴鸞宮弟子一個個跟上,雙手握劍,跪在地上,微微低頭。
晨風下,黃沙捲著血腥氣飄散而過,花向晚看著地面上的弟子屍體,她神色微斂,片刻後,輕聲道:「靈南,帶人將鳴鸞宮弟子押入地牢,打掃戰場。靈北,將傷患帶回宮中安置,清點傷患。薛子丹,」花向晚回眸看向正在一旁給弟子看診的青年,薛子丹抬頭,就聽對方朝著宮內揚了揚下巴,「跟我走。」
說著,花向晚轉眸看向謝長寂,他面上有些蒼白,花向晚遲疑片刻,伸手幫他把劍收回劍鞘,低頭拉住他,輕聲道:「我們先回去。」
「嗯。」
謝長寂應聲,任她拉著進了合歡宮宮城,走進廣場,入眼是在風中獵獵的招魂幡。
花向晚仰頭看著這些招魂幡,過去她每一次看,都很平靜,因為她知道這些招魂幡所指引的前路,然而這一次,握著手邊這個人,她卻頭一次生出了幾分茫然,這份茫然中,又生出了幾分勃勃生機,讓她對這未知的未來,有了幾分期許。
她領著謝長寂走到後院,薛子丹也跟了過來,抬手將黑袍從頭上放下來,便直接開口:「叫我來做什麼?現在這麼多事兒……」
「給他看看。」花向晚直接指向旁邊謝長寂。
薛子丹唐時瞪大了眼:「妳把我叫過來,就是給他看診?」
說完,不等花向晚回覆,他直接轉身:「我不看。」
「薛子丹。」花向晚語帶警告,「看不看?」
薛子丹腳步一頓,遲疑片刻後,他深吸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搖頭晃腦,面上全是痛苦:「花向晚啊花向晚,妳這是在折磨我。」
說著,他折回房間,坐到謝長寂對面,不耐煩道:「伸出手來。」
謝長寂不動,薛子丹驚疑地回頭:「你被天雷劈聾了?」
「無需你看。」謝長寂開口。
薛子丹頓時樂起來,他趕緊起身,只是剛站起來,又被花向晚按下去,花向晚的劍架在他脖子上,抬頭看謝長寂,微微一笑:「謝長寂?」
謝長寂不說話,過了片刻後,在花向晚無聲的「調解」下,他不情不願地伸出手。
薛子丹給他一把脈,立刻給了判斷:「腎虛。」
「庸醫,換人。」
「你好好看。」花向晚一巴掌拍在薛子丹腦袋上,「少給我胡說八道。」
薛子丹被打了一下,終於老實幾分,緊皺著眉頭給謝長寂診了會兒脈,又用靈息探查了一下他的情況,幾番確認後,臉色終於鄭重起來,皺起眉頭:「你……其他還是小傷,稍作休養即可,但分神重創,境界大跌,怕是要重新修煉好一段時間了。」
修士到化神期,便會修出可以離體的元神,被稱為「分神」,分神一般是魂體,特殊功法之下,亦可成為實體。
這一點不需要薛子丹提醒,謝長寂瞭解得比他清楚,點頭道:「我知道。」
「你的分神怎麼會被重創?」花向晚在旁邊聽著,有些不解:「秦風烈這麼強?」
「不是。」謝長寂搖頭,沒說原因,只否認:「他傷不到我的分神。」
「那……」
「他替妳擋了天劫,」薛子丹看謝長寂沒說,一面提筆寫著方子,一面嘲諷道:「天劫這東西,誰敢擋天道就是加倍的罰。他怕妳被劈死,用分神替妳擋了,這份情意可真是讓我動容。」
說著,薛子丹甩出一份方子,丟給花向晚:「分神這東西我沒法治,自己好好修煉吧,身體沒事兒,好好養,我先走了,外面人多著呢。」
「我同你一起。」花向晚見薛子丹要走,立刻起身,她回頭看了謝長寂一眼:「你既然沒有大事,先好好休息,我處理完事就回來。」
說著,花向晚便同薛子丹一起出去。
謝長寂抬眸看向兩人,想說什麼,最終還是將目光轉到一旁的茶壺上,翻開茶杯,給自己倒了杯冷茶。
花向晚送薛子丹走到長廊,薛子丹轉頭看她,知道她不會無緣無故跟過來,直接道:「說吧,要問什麼?」
「方才我渡劫時發生了什麼?」花向晚微微皺眉:「我渡劫完畢,便感覺魔氣橫生,出來便看見謝長寂……」
「他差點入魔了。」薛子丹冷靜開口,給出結論,「要不是妳趕出來阻他那一劍,他今天就立地成魔了。」
說著,薛子丹靠在長廊長柱上,輕笑出聲:「我早說過,他可不是什麼好人。就看這把劍妳用不用了。」
花向晚不說話,她聽著薛子丹的言語,緩了片刻後,她輕聲道:「薛子丹,我若想活下來,有辦法嗎?」
聽到這話,薛子丹動作一頓。
他愣愣抬頭,不明白花向晚的意思:「妳什麼意思?」
「要做的事我會做,答應你們的我也會做到,」花向晚轉頭看向庭院,目光平靜,「但我想爭一爭。」
說著,她看向薛子丹,目光中帶著幾分祈求:「我想活。」
薛子丹看著花向晚,他張口,想說點什麼,但緩了半天,卻一句話都說不出口。
好久後,他有些慌亂地移開眼睛:「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那就拜託你。」花向晚笑起來:「計畫照舊,但這一次,請你給我一線生機。」
聽著花向晚的話,薛子丹有些難受,他勉力笑了笑,只道:「當初我問妳是不是決心如此,妳非和我強……走到現在了,妳求我又有什麼用?」
「子丹……」
「行了我知道。」薛子丹打斷她,他深吸一口氣,胡亂道:「如有辦法我不會讓妳死。」
「多謝。」花向晚放下心來,點點頭:「宮裡其他人還需要你,我先去做事了。」
「好。」薛子丹心慌意亂,胡亂回聲。
花向晚轉身往回,薛子丹抬眼看著她的背影,忍不住出聲:「阿晚。」
花向晚回頭看他,薛子丹盯著花向晚,遲疑許久,只問:「是因為謝長寂嗎?」
花向晚想了想,只道:「我只是突然覺得,相比於死,活著,才是更大的勇氣。以前我沒有,現下,我想試一試。」
薛子丹不說話,花向晚見他久不出聲,抬眼看他:「怎麼了?」
薛子丹想了想,垂下眼眸,只道:「就是覺得有些不甘心,兩百年前比不過,兩百年後還是比不過。」
聽到這話,花向晚一愣,薛子丹擺手,似是有些煩悶:「走了。」
說著,薛子丹轉身離開,花向晚見他離去,便轉身去了大殿。
她先從靈北那邊大致瞭解一下情況,隨後就去見了秦雲裳。
秦雲裳被單獨安置在客院,正在包紮傷口,看見花向晚過來,她一挑眉頭,眼中帶著幾分豔羨:「就這麼渡劫了?」
「不然呢?我可忍了兩百年。」花向晚端著茶杯坐到椅子上,看著秦雲裳包紮好的肩頭,把衣服拉上,調笑起來:「和狐眠裝模作樣打了半天,妳還真受傷了?」
「不受點傷說不過去。」秦雲裳繫好腰帶:「謝長寂怎麼樣?」
「還行吧,」花向晚漫不經心,「鳴鸞宮那邊怎麼辦?妳出手還我出手?」
鳴鸞宮畢竟是秦雲裳的宗門,她終究要問問秦雲裳的意思。
秦雲裳想了想,只道:「我去說服趙南、陳順他們投誠,」說著,她抬眼看向花向晚,「秦雲衣妳幫我殺了,我當上宮主,妳就是魔主。」
「好。」花向晚也是這個打算,她直起身來,強調道:「等一會兒妳就走吧,幫我盯住秦雲衣,我要那兩塊血令完完整整回到我手裡。」
「明白。」
和秦雲裳商量好,花向晚沒多做停留,讓人把秦雲裳送走之後,又去逐一看了傷患,等到夜裡,終於回來。
回到屋中,謝長寂正在桌邊打坐,他一身素衣,面前的香爐燃著令人靜心的冷香。
花向晚站在門口,端詳著這個男人。
他生得有些書生氣,但氣質清冷,讓他整個人多了幾分劍一般的銳意。
明明是差一點就入魔的人,偏生就生了副仙風道骨的樣子,哪怕是殺人入魔,如果不瞭解前因後果,乍一看,都會覺得是謫仙入世,除魔衛道,他絕不會有半點錯處。
她靜靜地端詳著他,他察覺她久久不動的目光,緩慢睜眼。
其實明明有那麼多話,想問他,亦想告訴她。
然而在那雙清明眼靜靜看著她的那一刹,她卻什麼都說不出口。
他沒有點燈,月光灑落在屋中,他滿身清輝,平靜出聲:「恭喜。」
花向晚雙手抱胸,斜靠在門邊:「渡劫這麼大的事兒,你就說聲恭喜,不給點甜頭?」
「想要什麼?」
謝長寂問得平淡,可花向晚知道,無論她說什麼,他都會應許。
她一時不敢胡亂開口,盯著面前的人看了片刻,只問:「我在天劫裡看到你和昆長老蘇掌門說你要離開天劍宗。」
天劫乃天道對修士的考驗,天道悉知一切,所以內容並非幻境,或許是真的。
謝長寂知道她問什麼,倒也沒有遮掩,只道:「是。」
「我還看到你說……無論正道邪道,都希望我能好好活著。」
謝長寂動作一頓,他沒想到這居然會出現在她的天劫幻境中。
「妳的心結是什麼?」他微微皺眉,不解。
花向晚有幾分不好意思,她轉過頭,看著庭院:「我的心結……本身是,我不想活。」
聽到這話,謝長寂瞳孔緊縮,他眼底暗紅湧現,他捏起拳頭,死死克制著自己,盯著花向晚:「然後呢?」
「因為不想活,所以我無所謂牽掛,也沒有畏懼。所以我怕你。」花向晚說著,輕笑起來:「不是怕你殺了,你殺我,或者帶我回死生之界囚禁我,又或者是要取走魊靈,都不過是破壞我的計畫。我雖然有擔憂,但我並不害怕。我唯一只怕一件事——」
花向晚轉過頭,看著謝長寂:「我怕有牽掛。」
「所以呢?」謝長寂看著她:「妳同我說這些,想做什麼?」
花向晚不言,她看著他,一時竟不知該如何開口。
惶恐在謝長寂心中蔓延,他盯著她,撐著自己起身:「妳想讓我走?讓我放下?這樣妳就不欠我什麼,就沒有牽掛了?」
他說著,語氣激動起來,他從未這樣失控過,他一貫內斂,克制,平靜。
可生死彷彿觸及他的逆鱗,他死死盯著花向晚:「然後呢?然後妳要做什麼?妳要拿妳的命做什麼?」
說著,謝長寂笑起來,語氣中帶著幾分嘲諷:「復活沈逸塵?」
花向晚一愣,謝長寂看著她的表情,銳利的疼刮在他心上。
他死死捏著拳頭,卻還是道:「我可以的。」
「什麼?」花向晚聽不明白。
謝長寂沙啞出聲:「妳想要復活沈逸塵,我就幫妳復活他,如果要以命換命,那也讓我來。妳不必覺得虧欠我什麼,就當我是來還債,這樣也不可以嗎?」
「謝長寂……」花向晚聽著他的話,看著面前這個完全陌生的青年,微微皺眉,「你不欠我什麼,不需要還債。」
謝長寂沒應聲,花向晚解釋著:「沈逸塵不是你殺的,合歡宮出事也與你無關,其實……你對我很好。」
「可是,」謝長寂看著地面,有些愣神,「若我連虧欠都沒有,那妳我之間,又還剩什麼?」
花向晚愣愣地看著他,謝長寂抬眼,目光裡帶著幾分茫然:「晚晚,我們差了兩百年。」
妳往前走了兩百年,而謝長寂,卻長長久久,停留在兩百年前。
妳的人生裡早已沒了謝長寂,妳有新的悲歡離合,大起大落,妳有新的戀人,新的世界。
可謝長寂,卻永遠停留在死生之界,只有花向晚。
如果連虧欠都沒有,謝長寂與妳,又有何牽連?
又要拿什麼理由,牽絆妳,陪伴妳,守在妳身邊?
「我什麼都不求,也什麼都不要,如果一命抵一命,那我復活沈逸塵,他陪著妳也好。」
謝長寂說著,有些混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只是逼著自己,巨大的惶恐瀰漫在胸口,比什麼都重要,比什麼都疼。
「只要妳活著,都好,都很好。」
「那你呢?」花向晚看著明顯病態的人,微微皺起眉頭:「我和沈逸塵在一起,你不痛苦嗎?」
謝長寂動作頓住,死死抓著袖子,他根本不想這個畫面,只是不斷回想著當年。
他挑起她的蓋頭,她在星空下偷偷親吻他,她一遍一遍告訴他,我喜歡你,一直喜歡。
這些畫面讓他稍稍冷靜,他像是食用毒藥去緩解疼痛的癮君子,愉悅遮掩了血淋淋的一切,他的目光帶著幾分溫和。
「晚晚陪著我。」他抬起頭,笑著看著她:「晚晚喜歡謝長寂,我便足夠了。」
這話讓花向晚驚住。
她第一次意識到,謝長寂這高山白雪一樣的皮囊下,遮掩著多少屍骨血肉。
「那我呢?」她追問,「晚晚陪著妳,我呢?」
謝長寂說不出話,花向晚不解:「還是說,你愛的是兩百年前的晚晚,不是我?」
怎麼可能只是兩百年前的晚晚呢?
如果她與兩百年前不是一個人,如果愛的不是如今的她,她的生死,與他又有什麼關係?
可是他怎麼敢承認呢?
「謝長寂,」花向晚走到他面前,仰頭看著他,「我活著,活著站在你面前,為什麼不想和我廝守,而是惦念兩百年前的我?」
謝長寂聽著她的話,垂下眼眸,他的目光落在她脖頸紅線之上,知道那裡掛著什麼。
他艱澀地開口:「不敢奢求。」
花向晚聽著他的話,忍不住笑起來:「如果我讓你敢呢?」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劍尋千山【第二部】問心之劫(下卷/完結篇)的圖書 |
 |
劍尋千山【第二部】問心之劫(下卷/完結篇) 作者:墨書白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4-08-0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23 |
中文書 |
$ 324 |
中國歷史小說 |
$ 324 |
大眾文學 |
$ 324 |
言情小說 |
$ 369 |
華文羅曼史 |
$ 369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劍尋千山【第二部】問心之劫(下卷/完結篇)
★《山河枕》、《長風渡》、《長公主》殿堂級作者 墨書白,修真仙俠力作!
★冷酷劍修×媚人宮主,橫跨百年的追妻火葬場!
──精彩完結,收錄三萬字番外!
★網路積分30億,影視版權已售出。
集齊魔主血令,新一代魔主即將誕生。
而花向晚一直暗藏於體內的力量也被揭穿──兩百年前被封印的魊靈就在她身上。
魊靈出,蒼生陷。
兩百年前,謝長寂選擇了蒼生。
兩百年後,謝長寂再次面臨選擇。
謝長寂在西境大戰中,受魊靈侵襲,蠱惑之聲縈繞不去。
「謝長寂,你可知花向晚為何會選擇你?」
「去看看那合歡宮冰川下,封印著的人……」
他腳步踉蹌來到冰川,揮動長劍,看清了冰川下花向晚深深埋藏的祕密……
為了達成宿願,花向晚與碧血魔主達成交易──她將與碧血魔主成婚。
她要讓所有人償還血債,她要讓所有故去之人──歸來!
作者簡介:
墨書白
晉江超級積分作者,晉江文學城2019年年度最具影響力作者,著有《山河枕》、《長風渡》、《長公主》、《假貴族》等十餘部長篇小說暢銷作品。
文筆細膩,注重構建文字畫面感,多關注於個人成長與世界的平衡相處等議題,擅長以小人物寫大情懷。
自創作以來,連續三年入選晉江年度盤點,作品常登晉江收入金榜及各大榜單前列。
人氣作品《山河枕》、《長風渡》收藏數均超過二十萬,收入在晉江首頁金榜記錄保持前二十,分別售出影視版權、簡體版權、繁體版權、泰文版權、有聲小說版權、廣播劇版權等。
著有:《長公主》(高寶書版)、《長風渡》(高寶書版)、《圍堵可愛的他》、《燦爛的她》、《山河枕》(高寶書版)等暢銷書。
章節試閱
第十二章 人間之感
看著跪倒在地的秦風烈,鳴鸞宮弟子都是一愣。
片刻後,有人驚呼出聲,鳴鸞宮弟子瞬間意識到敗局已定,四處逃散而去。
花向晚抬眼揚聲:「慢著。」
音落,一道結界無生地在周邊瞬間升騰而起,一個個弟子撞到結界之上,發現走投無路。
現下高階修士已經逃開,這些弟子慌張得不知所措,他們所有人提劍站在不遠處,勉力支撐著自己不要恐懼,咬牙看著高處的花向晚和謝長寂。
「花少主。」唯有秦雲裳,她一手撐劍,吊兒郎當地站起來,打量著花向晚的狀態,恭敬道:「恭喜花少主步入渡劫。」
「你們鳴鸞宮就是這麼恭...
看著跪倒在地的秦風烈,鳴鸞宮弟子都是一愣。
片刻後,有人驚呼出聲,鳴鸞宮弟子瞬間意識到敗局已定,四處逃散而去。
花向晚抬眼揚聲:「慢著。」
音落,一道結界無生地在周邊瞬間升騰而起,一個個弟子撞到結界之上,發現走投無路。
現下高階修士已經逃開,這些弟子慌張得不知所措,他們所有人提劍站在不遠處,勉力支撐著自己不要恐懼,咬牙看著高處的花向晚和謝長寂。
「花少主。」唯有秦雲裳,她一手撐劍,吊兒郎當地站起來,打量著花向晚的狀態,恭敬道:「恭喜花少主步入渡劫。」
「你們鳴鸞宮就是這麼恭...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十二章 人間之威
第十三章 鳴鸞變
第十四章 當年
第十五章 魅惑
第十六章 屠魔
第十七章 入魔
第十八章 復生
第十九章 相思
第二十章 愛魄
結局
番外、餘生百年
番外、沈逸塵
番外、秦雲裳
第十三章 鳴鸞變
第十四章 當年
第十五章 魅惑
第十六章 屠魔
第十七章 入魔
第十八章 復生
第十九章 相思
第二十章 愛魄
結局
番外、餘生百年
番外、沈逸塵
番外、秦雲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