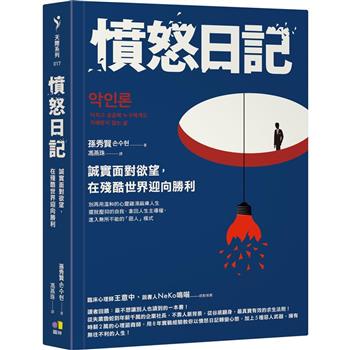第十章 瘟疫
扶冬清楚地記得,徐述白離開那日是七月初七。
昭化十三年七月初七,離洗襟臺建成還有兩日。
扶冬沒有等回徐述白,等來的卻是一個驚天噩耗。
洗襟臺塌了,許多登臺的士子,建造洗襟臺的工匠,還有平頭百姓死在了洗襟臺下。
彷彿剎那間天就變了,陵川崇陽縣一帶哀鴻遍野,朝廷震動,昭化帝帶著朝臣親自趕來柏楊山,下令徹查坍塌原因。
第一個被查出來的就是木料問題,工部郎中何忠良與州尹魏升以次充好的消息震驚四野,人還在柏楊山下就被昭化帝下令斬了首,販售給他們次等鐵梨木的徐途畏罪自盡,一家二十七口,一個活口都沒留。
飄香莊也亂了。
莊上的嬤嬤草木皆兵——在洗襟臺出事前,何忠良、徐途一干人等可是莊上的常客——她們唯恐大禍殃及己身,一個接著一個把莊中妓子賣了出去,連夜出逃。
好在何忠良這些人尋歡作樂的地方不止飄香莊一處,洗襟臺之禍千頭萬緒,官府查不到這些下九流的妓子身上,於是扶冬就在這一片兵荒馬亂中離開飄香莊,到了大戶人家的宅院。
她最終沒能如徐述白期望的那般留存自身潔淨,而是回歸了輾轉承歡,風塵打滾的宿命。她在那些宅院裡被百般嬌寵,又被漸漸厭棄,最後如同物件兒一般,待價而沽,轉手下家。
只是偶爾在月光都照不透的深夜,她還會想起當初徐述白對她說的話。
那個青澀又年輕的書生,最開始說話的時候,總是漲紅了臉:「不是這樣的,有的買賣可以做,有的買賣不能做。」
什麼買賣不能做呢?經過這幾年,扶冬多多少少想明白了。
那幾瞬的璀璨浮華如果是靠出賣自己獲得的,最後不過水中月罷了。
人之所以是一個人,正因為她不是一個可以待價而沽的物件。
想明白這一點後,扶冬就存了一個念頭,她要為自己贖身,然後去洗襟臺下,為徐述白收屍。
她不知道他明明說要上京最後為何死在了洗襟臺下——在樓臺坍塌的半年後,她在喪生的士子名錄中找到了他的名。
扶冬去柏楊山為徐述白收屍時,已經是嘉寧二年的春天了,說是收屍,實則在一場防止瘟疫的大火過後,留下的只有逝者的遺物。
扶冬看到徐述白的遺物,一下子就愣住了。
這是一個秀才牌符,上頭刻著他的名,他的籍貫,他的秀才功名。
與當初徐述白送給她的那個一模一樣。
扶冬很快反應過來,官府的交給她的牌符是假的,真正的牌符在她這裡。
回想起彼時徐述白離開陵川前的種種,扶冬剎那間覺得背脊發寒——
「這個洗襟臺,不登也罷!」
「我上京為的就是洗襟臺!是要敲登聞鼓告御狀的!」
「這個案子牽涉重大,刻不容緩。」
「知道得太多,一個不慎只怕招來殺身之禍,妳只當是什麼都沒聽說,待事態平息前,別告訴任何人妳認識我。」
徐述白是個說一不二的人,他既說了不願登臺,必然不會反悔。
也就是說,徐述白消失在了上京的路上,而他死在洗襟臺下的消息,是有心人刻意偽造出來的假象。
扶冬道:「我得了真假牌符,知道事情不簡單,誰也沒透露,一個人回了住處。回過頭來想,或許這事從頭就透露著古怪。徐途這個人旁人不知道,我卻清楚得很,他素來貪名逐利,貪生怕死,當時洗襟臺塌,他不逃也就罷了,怎麼會畏罪自盡呢?就算自盡,為何要拖上一家二十七口全部陪葬呢?而最重要的一點,卻是我一直忽略的。」
「什麼?」青唯問。
「做官。」江辭舟說道。
「是,做官。」扶冬頷首:「江公子是貴胄子弟,熟悉朝廷中的那一套,想必一眼就能看出這其中蹊蹺。而我彼時不過飄香莊的一名妓子,聽那些恩客說先生不久後要去京裡做官,並沒有放在心上。
「後來仔細求教打聽,在京中做官,如果不是世家出生能得蔭補,必然要舉子以上出身,先生彼時不過一名秀才,便是登了洗襟臺,有何忠良、魏升這樣的人物保舉,不過是仕途會順當許多,如何這麼快就有京官做?」
「還是說,朝中有更厲害的人物,能越過種種規矩儀制,將一名秀才提拔上來,任由他先做官,再慢慢考學?」
扶冬查明白這一點,便找到當初莊上的嬤嬤,跟她打聽。
嬤嬤離了莊子,過得很不好,短短幾年重疾纏身,已到了就木之際,或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吧,她說:「妳問那個書生啊。那個書生,是個好孩子。嬤嬤活了這些歲數,見的好人太少,他算一個。不過我勸妳,莫要找他了,他不可能活著,徐途得罪的人物,那可厲害著哩。」
「是誰?」扶冬問。
嬤嬤道:「我也不知道,只是有回聽他們提起,像是那個何什麼……哦,何忠良,他的遠親。叫老何大人還是小何大人來著?說他厲害得很,能給書生官做。」
宮中何姓的大臣不少,但是被稱作老何大人與小何大人的只有兩位——
當朝中書令何拾青,與工部郎中何鴻雲。
青唯道:「如果嬤嬤說的是真的,徐途通過次等鐵梨木的買賣,真正搭上的人是何拾青與何鴻雲,那麼一切就說得通了。
「利用木料差價,貪墨銀錢的是二何。何忠良、魏升只是為二何與徐途牽線的橋梁。二何允諾徐途,事成之後,讓徐述白上京做官,沒想到洗襟臺塌,木料的內幕暴露,二何唯恐被大禍殃及,於是滅口殺害徐途一家,讓魏升、何忠良做了頂罪羔羊。
「還有徐述白,他本來要登洗襟臺,後來忽然反悔,或許正是因為從徐途口中得知二何替換木料的內情,想要上京告御狀。但這事被二何洞悉,派人找到徐述白,加害於他,做成人已死在洗襟臺下的假象。」
扶冬道:「姑娘說的是,我也是這麼懷疑的。」
「我流落半生,被人視作足下塵,風中絮,只有先生一人以真意待我,且不論情之一字,當初先生教我詩書,便是希望我能立身磊落,而今我孑然一人,無親無故,既知道先生為那高門權貴所害,此事斷不可以就這麼揭過去。」
「我沒有先生那般志向高潔,想要以一己之力揭發何家父子的大罪,但我至少要知道先生人在哪裡,是否被害。」
扶冬跟著一戶酒商學來釀酒的手藝,冒用一個寡婦的身分來了京城。打聽到京中貴胄子弟常去東來順擺席吃酒,她盤下折枝居,開了酒舍,借著去東來順送酒,刻意接近何鴻雲。
何鴻雲有個私人莊子,五年前扶夏病重,莊上已許久沒來過可人的美人兒了。扶冬貌美,加之這二十年魅惑人的功夫不是白學的,他有所需,她有所求,兩人一拍即合,她於是一夜之間從折枝居消失無蹤,更名為扶冬,搖身一變,成了祝寧莊上新到的花魁。
扶冬說到這裡,已是淚水漣漣,「該說的,奴家知無不言,已經全說了,姑娘手裡既有這支雙飛燕玉簪,想必定是有了先生的下落,還望……」她抿抿唇,竟是伏身與青唯行了個大禮,「還望姑娘無論如何都告訴我……」
青唯連忙將扶冬扶起。
她將薛長興留給她的玉簪與扶冬的斷簪一併拿出,實話說道:「對不住,這支玉簪是一個前輩留給我的,我並沒有徐先生的消息,在妳提起他之前,我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個人。不過妳放心,等我找到前輩,我一定第一時間跟他打聽徐先生的下落。」
扶冬聽了這話,並沒有失望,她抹乾淚,很淺地笑了一下,「有人找到這支玉簪,對我來說已經是很好的消息了。該說對不住的是奴家,那日在折枝居,奴家並不知道何鴻雲為何要對付姑娘。佯作刺殺姑娘,是為了獲取何鴻雲進一步的信任,望姑娘千萬見諒。」
青唯沒多在意,把兩支玉簪一併還給扶冬:「物歸原主,妳留著當個念想。」
扶冬看著玉簪,眼淚又落下來,她很快抬袖拭乾,低聲說了句:「多謝。」取出一支錦盒,將簪子收好。
江辭舟見她心緒平復,問道:「妳接近何鴻雲這些日子,可有查到什麼?」
扶冬仔細想了想,搖頭道:「沒有。有樁事說來古怪,我雖懷疑利用木料差價,真正貪墨銀錢的是何家父子,但是五年前,洗襟臺修建之初,無論是何拾青還是何鴻雲都不在陵川。何拾青在京中養病,何鴻雲接到聖命,去寧州治疫了。他治疫治得好,聽說因為這,事後來還升了官……」
五年前,去寧州治疫?
江辭舟眼下查扶夏,不正是為了五年前的瘟疫案?
青唯她正待細問,屋外忽然傳來腳步聲。
閣樓小院的巡衛每一炷香便會巡視一圈,半個時辰一過,還會到院舍內部檢視。
定是那些巡衛又到了!
扶冬警覺,掀了燈罩,立刻要掐斷燭火。
江辭舟攔住她:「別滅!」
適才還點著燈,眼下守衛剛到,燈就滅了,豈不是此地無銀?
可這屋子雖大,卻一覽無遺,他們活生生兩個人,究竟該怎麼藏?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青雲臺【第一部】洗襟無垢(中卷)的圖書 |
 |
青雲臺【第一部】洗襟無垢(中卷) 作者:沉筱之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4-09-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青雲臺【第一部】洗襟無垢(中卷)
樓臺塌,煙塵起,掩埋了真相,
破迷障,尋線索,只願還天下大白……
★人氣作家 沉筱之 經典口碑力作
★聰慧堅韌.溫小野×溫潤清貴.謝容與
──虛情假意,兩廂試探,到後來成了她一路風雨的皈依
★網路積分27億,影視版權已售出,火熱籌備中!
溫小野和江辭舟查出當年瘟疫案與洗襟臺之中有關聯,
瘟疫案囤積藥材用的銀子,就是當初替換洗襟臺木料省下的銀子,
而當年負責瘟疫案之人是如今工部水部司郎中──何鴻雲,
不料何鴻雲卻用江辭舟的心疾來對付他,溫小野也身受重傷……
先帝將修築洗襟臺一事交由小昭王謝容與,名匠溫阡被他請來督工,
只是他沒想到,木料早已被替換成次品,
那支撐著樓臺的木樁被他一聲令下拆除,以致樓臺倒塌、屍橫遍野,
至此他有了心疾,戴上面具,做了五年的「江辭舟」……
崔弘義是當年瘟疫案唯一活下來的人,此時以囚犯之身押解上京。
溫小野與謝容與為了保住他而劫囚車時,被何鴻雲以及手下人阻攔,
何鴻雲再以溫小野「劫獄」的罪由想將她拿下,
他們該如何脫身?
作者簡介:
沉筱之
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行文流暢,文風凝練,繾綣深刻,引人深思。
已出版作品:《青雲臺》(高寶書版)、《恰逢雨連天》、《公子無色》等。
新浪微博:@沉筱之。
章節試閱
第十章 瘟疫
扶冬清楚地記得,徐述白離開那日是七月初七。
昭化十三年七月初七,離洗襟臺建成還有兩日。
扶冬沒有等回徐述白,等來的卻是一個驚天噩耗。
洗襟臺塌了,許多登臺的士子,建造洗襟臺的工匠,還有平頭百姓死在了洗襟臺下。
彷彿剎那間天就變了,陵川崇陽縣一帶哀鴻遍野,朝廷震動,昭化帝帶著朝臣親自趕來柏楊山,下令徹查坍塌原因。
第一個被查出來的就是木料問題,工部郎中何忠良與州尹魏升以次充好的消息震驚四野,人還在柏楊山下就被昭化帝下令斬了首,販售給他們次等鐵梨木的徐途畏罪自盡,一家二十七口,一個活口都...
扶冬清楚地記得,徐述白離開那日是七月初七。
昭化十三年七月初七,離洗襟臺建成還有兩日。
扶冬沒有等回徐述白,等來的卻是一個驚天噩耗。
洗襟臺塌了,許多登臺的士子,建造洗襟臺的工匠,還有平頭百姓死在了洗襟臺下。
彷彿剎那間天就變了,陵川崇陽縣一帶哀鴻遍野,朝廷震動,昭化帝帶著朝臣親自趕來柏楊山,下令徹查坍塌原因。
第一個被查出來的就是木料問題,工部郎中何忠良與州尹魏升以次充好的消息震驚四野,人還在柏楊山下就被昭化帝下令斬了首,販售給他們次等鐵梨木的徐途畏罪自盡,一家二十七口,一個活口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十章 瘟疫
第十一章 涉險
第十二章 夢魘
第十三章 小野
第十四章 帳本
第十五章 詩會
第十六章 押解
第十七章 替罪
第十八章 塵煙
第十九章 證物
第十一章 涉險
第十二章 夢魘
第十三章 小野
第十四章 帳本
第十五章 詩會
第十六章 押解
第十七章 替罪
第十八章 塵煙
第十九章 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