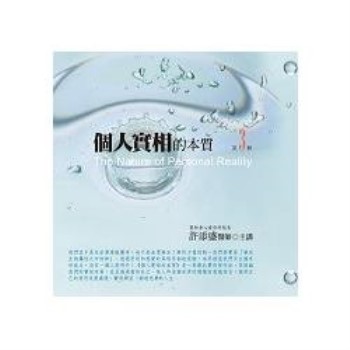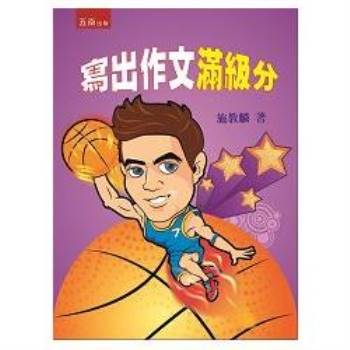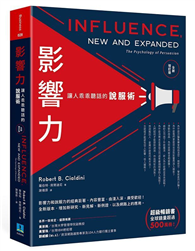人類史上最迫切需要讀《1984》的時代——
就是現在
歐威爾的作品讓我們看到,語言如何被用來操縱與控制。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 附【1984-雙重思想:驚世語錄】一表
■ 歐威爾逝世75週年全新中文全譯本,還原歐威爾冷峻精煉的寫作風格
■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陳榮彬推薦
★英美中學生必讀的文學經典
★《時代周刊》「最好的100本英語小說」
★蘭登書屋「100本20世紀最佳英語小說」
★超過62種語言譯本,全球銷量5千萬冊以上
◆
2016年,因為川普贏得大選,FB祖克柏斥資數十億美元啟動旗下平台進行「事實查核」;
2025年,川普二度就職美國總統之前,Meta祖克柏宣布結束「美國事實查核計畫」。
祖克柏:「我們將裁撤事實查核人員,他們的政治偏見太深,破壞的信任比他們建立的還多……」
祖克柏知道自己為何這麼說,但是他相信自己的話嗎?
這是祖克柏否定祖克柏的時代,
是「真相可塑」的時代——
我們需要《一九八四》讓自己保持清醒。
《一九八四》出版於1949年,今日與赫胥黎《美麗新世界》、薩米爾欽《我們》並列反烏托邦文學三大經典,當中以《一九八四》最貼近我們今日所處的「後真相時代」,曾經在2017年因川普提出荒謬的「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概念而在美國造成新一波閱讀風潮,銷售暴增9500%。
《一九八四》的敘事核心之一在於揭示極權政權如何透過控制思想、語言和歷史,徹底剝奪個人的自由與真相,而歐威爾在當中提出的「雙重思想」(Doublethink),是「老大哥」的終極手段,貫穿了整個故事。
⇆「雙重思想」的特徵是:同時堅持兩個互相矛盾的信念,並試圖使這些矛盾合理化。
⇆具備「雙重思想」的人,真的相信兩種不同的觀點;被「雙重思想」控制的人,可以隨時說謊,但不認為自己在說謊,並且轉眼就忘掉自己剛才說謊,立刻奉新的謊言為真理。
這種能力需要相信黑色是白色,常見於忠誠至上的人身上。
培養「雙重思想」的能力,你沒了自由,但你會是最幸福的人——
在他們決定你是敵人之前。
◆
國家主張民主價值,卻同時極力壓制異議;
政府一邊讚揚透明政治,卻一邊強化資訊監控;
政黨聲稱保持中立,卻又偏向特定陣營;
政客主張清廉乾淨,卻又從事黑箱操作;
企業以「永續發展」為目標,背後卻大肆掠奪自然資源……
今日社會充斥著各種類似的矛盾與謬論,完全對立的「事實」橫流四溢,「雙標」、「髮夾彎」、「打臉自己」成了日常語言,這些都是「雙重思想」下的產物,讓我們即使不受極權政權統治,每個人也都活成了《一九八四》裡「大洋國」的子民,逐漸將這些矛盾視為理所當然,在無意間成為這種邏輯矛盾的接受者與執行者。
歐威爾以「大洋國」的虛構世界,深刻描寫了「雙重思想」如何成為控制人民的工具。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到「無知即力量」,他揭示了語言與思想如何被扭曲,用以操控大眾。他的《一九八四》不僅是對極權社會的批判,更是一面照見我們當代社會危機的鏡子。
閱讀《一九八四》不只是一場文學體驗,更是一種思想上的挑戰,提醒我們要警惕看似合理的謬論,鍛鍊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習如何在迷霧中守護真相。
作者簡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
本名艾瑞克・亞瑟・布雷爾(Eric Arthur Blair),英國著名作家、記者暨社會評論家,以其對極權主義的深刻洞察與批判聞名於世。他的代表作《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和《動物農莊》(Animal Farm)為文學史上的經典,揭露了極權體制的荒謬與殘酷,對世界文學與社會思潮產生深遠的影響。
《1984》出版於1949年,以一個虛構的極權世界為背景,描述個人如何在全然監控和思想控制下喪失自由與尊嚴。他在本書中創造的「老大哥」(Big Brother)、「雙重思想」(Doublethink)、「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等詞彙,今日已成為描述專制統治的代名詞。歐威爾透過本書警示讀者極權體制對個人自由的威脅,並揭露真相被扭曲的危險。他以冷峻的筆調描繪了一個被監控和宣傳完全掌控的世界,對科技與政治聯手剝奪人性的潛在風險發出預言式警告。《1984》對未來主義和反烏托邦文學產生重要影響,啟發了包括瑪格麗特.愛特伍的《使女的故事》等在內的多部作品。
歐威爾的作品不僅揭示了權力如何運作,也探討了權力如何腐蝕道德和人性。《動物農莊》用寓言展現權力的逐步腐化,《一九八四》則揭示了極權體制對權力的極致追求。他認為權力的核心目的是控制,並強調「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此一觀點至今對文學、政治哲學和社會批評具有重要意義。
譯者簡介:
游騰緯
臺大翻譯碩士學程筆譯組畢。自由譯者、文字工作者,譯有《古典音樂之愛》(黑體文化)、《藝術家之死》(麥田出版)。譯稿賜教:tengwei930@gmail.com
章節試閱
溫斯頓展在開始一天的工作時,不自覺地深深嘆了口氣,即使他正距離電幕很近也無法遏止自己發出嘆息。他把說寫機拉向自己,吹掉收音口上的灰塵,然後戴上眼鏡。四份捲成圓筒狀的文件早已從辦公桌右側的氣送管落下。他攤開文件,並將它們夾在一起。
隔間的牆上有三個孔洞:說寫機的右側是書面文字訊息的小型氣送管,左側較粗的氣送管用於傳送報紙;在溫斯頓伸手可及的側壁上,是一個圍著金屬格柵的大橢圓形投入口,用來處理廢紙。這整棟建築有成千上萬個投入口,不只每個房間都有,每條走廊上也相隔不遠就設置一個。不知為何,這些投入口被暱稱為「記憶洞」。當部裡的人得知任何文件需要銷毀,或甚至看到附近有一張廢紙,就會自動掀起身邊記憶洞的掀蓋口把它放進去,隨後紙張會被一股熱氣捲走,飄向隱藏在建築物深處的巨大熔爐。
溫斯頓檢視攤開來的四份文件,每一張紙只有一、兩行句子,由縮寫術語組成——雖不全然是新語,不過大多是由新語單字組成——這些內容用於內部溝通,內容如下:
泰晤士報 17.3.84 BB演講誤報非洲修正
泰晤士報 19.12.83 預測三年四季八三個誤印核實現刊
泰晤士報 14.2.84 裕部誤引巧克力修正
泰晤士報 3.12.83 報導BB日勳雙加不好涉及非人全改上呈待存
抱著一絲滿足感,溫斯頓把第四條訊息放到一邊。那是責任重大的複雜工作,最好留到最後處理。其他三項都是例行公事,不過第二項可能比較枯燥,必須核對一大堆數字。
溫斯頓在電幕上撥打「過刊」數字,調出這四個日期的《泰晤士報》。報紙幾分鐘後就從氣送管中滑出。訊息中提及的文章或新聞,因為某些理由有必要調整——官方用語是:修正。三月十七日《泰晤士報》報導,老大哥在前一天的演說中預測南印度戰線將維持和平,但歐亞國很快就會在北非發動攻勢。出乎意料的是,歐亞國最高司令部襲擊的是印度南部,不是北非。因此,老大哥演說中的一段必須重寫,好讓他的預測與實際發生的事相符。十二月十九日《泰晤士報》公布一九八三年第四季,也就是第九期三年計畫第六季,各類消費品產量的官方預測。這天的報紙刊載了實際產量,可以看出與預測的數字相去甚遠。溫斯頓的作就是要修正原始數據,以吻合後來的新數據。至於第三個訊息,只是非常簡單的錯誤,幾分鐘內便可以修正。不久前的二月,裕民部承諾(官方用語是「絕對保證」)一九八四年全年不會減少巧克力配給量,而事實上,就如溫斯頓所知,這個週末巧克力的配給量將從三十克減少到二十克。他只需要拿掉原先的承諾,改為提醒大家四月某個時間點可能有必要減少配給量。
溫斯頓處理完每一則新聞,立即將他用說寫機修正好的版本以迴紋針別在該日的《泰晤士報》上,然後推入氣送管,接著他近乎無意識地將收到的訊息字條與他為此做的筆記揉成一團,扔進記憶洞裡任由火焰吞噬。
氣送管通往的那個看不見的迷宮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他不太清楚細節,只知道個大概。特定日期《泰晤士報》需要修正的部分只要集結完成,該號將重新印行,並且銷毀原始副本,用更正版歸檔。這種持續修改的程序不僅限於報紙,也運用在書籍、期刊、小冊子、海報、傳單、影片、聲軌、漫畫、照片——所有可能包含任何政治意涵或意識形態的各種文學作品與文獻。日復一日,幾乎每一分鐘都有過往被更新。如此一來,黨的每一個預測都有修正過的文獻佐證。任何與時下需求相牴觸的新聞或言論都不許留存紀錄。所有歷史都像是被刮去原文、重複利用的羊皮紙,只要有必要就會刮除乾淨並重新書寫。一旦修正完成,就完全不可能證明這些檔案經過任何偽造。檔案司的最大單位比溫斯頓工作的單位大得多,所有職員都負責追查已經被修正之書籍、報紙及其他文件的初始版本,這些都要全數銷毀。一些《泰晤士報》的報導因為政治立場或結盟關係的改變,或因為老大哥的錯誤預言而被改寫了十幾次,但它們仍然存在檔案庫裡,登載著原始日期,而且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內容與之矛盾的版本。書籍也一樣,一次又一次被回收重寫,但再版時永遠不會承認內容經過修改。那些下達給溫斯頓的書面指示從未表明或暗示要進行偽造,而且他處理完後一定立即銷毀——每次的原因都說是為求精確,必須修正疏漏、謬誤、誤印或誤引。
不過,溫斯頓重新調整裕民部的數字時,其實他認為這根本稱不上造假。這不過是用一段胡扯代替另一段胡扯而已。你處理的大部分資料與現實世界的一切沒有任何關聯,甚至連最顯而易見的謊言中通常隱含的一點點事實基礎也不存在。統計數字的原始版和修正版都同樣虛幻,常常需要自己憑空想像。例如,裕民部預測本季靴子產量為一億四千五百萬雙,實際產量為六千兩百萬雙,但是溫斯頓重寫的預測會將數字調降至五千七百萬雙,以便讓黨一如既往宣稱目標已超額完成。無論如何,六千兩百萬不比五千七百萬或一億四千五百萬更接近事實,很有可能根本連一雙靴子都沒有生產。更有可能的是,沒有人知道實際產量,也沒有人關心。大家只知道,每季靴子產量的天文數字是紙上談兵,而大洋國也許有一半的人口打赤腳。各種類別或大或小的數據紀錄都是如此。一切都消散在幻影世界之中,最後連年份日期也分不清了。
溫斯頓往大廳那邊掃了一眼。另一側相對的隔間裡,一個名叫提洛森的男人正專心努力工作。他個子不高,看起來相當拘謹,下巴留著黑色鬍子。他的膝蓋上放著一張對折的報紙,嘴巴緊靠說寫機的收音口,感覺想避免讓其他人聽見自己對電幕說的話。他抬起頭來,眼鏡朝溫斯頓投射出一道充滿敵意的閃光。溫斯頓跟提洛森不熟,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內容。檔案司的職員不太願意談論他們的工作。沒有窗戶的大廳有兩排小隔間,持續傳出紙張摩擦的沙沙聲和對著說寫機說話的喃喃低語。這裡面有十幾個人,溫斯頓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儘管他每天都看到他們在走廊上匆忙來回,或是在「兩分鐘仇恨」時用力揮舞雙手。他知道旁邊的隔間裡,那個淺沙色頭髮的矮小女人日復一日辛勤工作著,只為從出版物中找出已經被蒸發、被視為從未出現在這世上的人,刪除他們的名字。這項工作滿適合她,畢竟她的丈夫幾年前也被蒸發了。幾個隔間之外,有個溫和、無能、愛做白日夢的傢伙,名叫安普福斯。他的耳朵長滿了茸毛,在處理韻腳與格律上擁有驚人的天賦。詩集裡有些作品會帶有牴觸黨的意識型態,但因為某些原因被保留下來,而他正在重新撰寫這些詩的曲解版本——官方稱之為「權威文本」。這個大廳裡約有五十名職員,在巨大龐雜的檔案司中也不過是一個處室、一個細胞。遠處、樓上、樓下還有其他大量職員,從事各式各樣難以想像的工作。這裡有大型印刷廠,配置了助理編輯、排版專家,以及設備精良的照片偽造工作室;也有由工程師、製作人和演員團隊組成的電幕節目單位,這些演員經過精挑細選,善於模仿聲音;甚至還有人數眾多的資料處理人員,專門負責條列需要召回的書籍和期刊。這裡建有存放更新版文件的大型倉庫,也有用於銷毀原始文件的隱蔽熔爐。沒有人知道主腦團隊成員是誰或是在哪裡,但他們在暗地裡指揮協調運作、訂定政策路線,並且決定保留、重製或抹去哪一段歷史。
不過,檔案司還只是真理部的其中一個單位,該部主要的工作不是重建過去,而是提供大洋國國民報紙、電影、教科書、電幕節目、戲劇、小說——各種你想像得到的資訊、指導或娛樂,從雕像到口號,從抒情詩到生物學論文,從兒童拼寫課本到新語詞典。真理部不僅要滿足黨的各種需要,還要另外製作一套低階產品來造福無產階級,由一長串獨立部門負責製作供應給無產階級的文學、音樂、戲劇和娛樂,當中有幾乎滿是體育新聞、犯罪案件和星座運勢的品質低劣報紙、情節官能煽情的廉價小說、情欲橫流的桃色電影,還有各種靡靡之音,完全由被稱為「詞曲合成器」的機械拼湊生成。甚至,還有一個新語名為「色科」(Pornosec)的小部門,專門製作最低俗至極的色情作品。他們產出的所有成品皆密封寄出,除了工作人員之外,任何黨員都不許觀看。
溫斯頓處理工作時,氣送管又滑出三張紙捲,但都是簡單的交辦事項,在「兩分鐘仇恨」打斷他之前就處理掉了。仇恨結束後,他回到自己的隔間,從書架上拿起新語詞典,將說寫機推到一邊,再擦了擦眼鏡,開始著手今天上午最重要的任務。
溫斯頓生活中的最大樂趣就是他的工作,雖然大多是乏味的例行公事,但可能也有一些非常困難複雜的挑戰,可以讓人傾力投入,宛如絞盡腦汁解開一道數學難題:在毫無其他指示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對於英社原則的理解和對於黨期待聽到什麼的掌握,來打造精緻偽造的文字。溫斯頓擅長此道,有時甚至會被委派修正完全用新語寫成的《泰晤士報》社論。他攤開之前放在一旁的訊息,上面寫著:
泰晤士報 3.12.83 報導BB日勳雙加不好*涉及非人全改上呈待存
*歐威爾於《一九八四》中創造的新語詞彙,在ungood(不好)前又加上double(雙倍)與plus(更加),構成「雙加不好」(doubleplusungood)一詞。
用舊語(或標準英語)來解讀意思大概如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泰晤士報》「老大哥當日授勳」報導極為不當,提及不存在的人。全文重寫,歸檔前將文稿上呈請示。
溫斯頓從頭到尾讀過這篇問題報導。那天「老大哥當日授勳」似乎主要在讚揚「FFCC」的付出,該組織提供香菸與福利品給浮堡的水手。內文中特別提及一位知名核心黨員威瑟斯同志,獲頒二等功績勳章。
三個月後,FFCC 突然無緣無故解散,大概可以推測威瑟斯及其同夥失寵了,但報紙或電幕都沒有對此事進行報導。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政治犯鮮少受審,也不常遭到公開譴責。黨會公審叛徒與思想犯,要他們低頭認罪,隨後進行處決,但這種牽涉數千人的大清洗是幾年才一遇的特殊盛會。通常,那些引起黨不滿的人就直接消失了,自此音訊全無,大家完全不曉得他們的下場到底如何。某些情況下,也許有人還活著。溫斯頓認識的人當中,不包括他的父母,大概有三十個人先後消失。
溫斯頓用迴紋針輕敲著鼻頭。對面的隔間裡,提洛森同志仍神祕兮兮地伏在說寫機前。他抬頭片刻,鏡片又閃過一道敵意。溫斯頓懷疑提洛森同志的工作與自己的一模一樣。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此艱難的工作不會只委派一個人,但將它交給一整個委員會處理又等於公開承認進行捏造。很可能現在有多達十幾個人正在撰寫與老大哥實際所言相反的內容,隨後內黨主腦會從中選擇一個版本,重新編輯並進行必要的複雜交叉比對,最後被選中的謊言將永久保存並成為事實。
溫斯頓不知道威瑟斯為何失寵,也許是因為貪腐或無能,也許老大哥只不過是要斬除太受歡迎的下屬,也許威瑟斯或與他關係密切的人被懷疑抱持異端思想,又或許——這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只是因為清洗和蒸發是政府運作的必要機制。訊息中唯一的真正線索是「涉及非人」這幾個字,代表威瑟斯已經死了。不過,並非所有遭到逮捕的人都會被立即處死。有時他們會被暫時釋放,在行刑前享有長達一、兩年的自由時間。偶爾,有些你以為早已死去的人會像鬼魂般再次現身公審,他的供詞將牽連數百人,然後再次消失,而這次就一去不復返了。不過,威瑟斯已經是個非人了。他不存在——他從未存在過。溫斯頓認為,光是翻轉老大哥演講的說詞是不夠的,最好改成與原本主題完全無關的事情。
他大可把演說變成如往常一般對叛徒和思想犯的公開譴責,但就會有點太明顯了,而造假前線勝利或者第九期三年計畫超產,可能又會讓這份檔案變得過於複雜。這裡需要一個完全虛構的故事,而他的腦海裡這時突然浮現一個形象,彷彿他早已預先想好:一位不久前在戰役中犧牲的同志,名叫奧格維。老大哥有時會把他的當日授勳用來紀念身份卑微的基層黨員,把他們的人生奉為值得效仿的榜樣。這一天,他就該用來紀念奧格維同志。當然,奧格維同志並不存在,但幾行文字和幾張偽造的照片就可以讓他立刻真實存在於這個世上。
溫斯頓想了想,把說寫機拉近,開始以老大哥常見的語氣口述。這種風格富有軍事色彩又帶著老古板味,而且因為運用自問自答的提問技巧,所以很容易模仿,比方說:「同志們,我們學到了什麼教訓?我們學到的教訓,同時也是英社的基本原則,那就是……等等。」
奧格維同志三歲時,除了鼓、衝鋒槍和模型直升機之外,對其他玩具都不感興趣。六歲時因特例放寬標準,他提前一年加入少年間諜隊,三年後晉升隊長。十一歲時,他意外聽到一段透露著犯罪氣息的對話,向思想警察舉發了他的叔叔。十七歲,他成為青少年反性聯盟的區幹部。十九歲時,他設計的一種手榴彈被和平部採用,在首次武器試驗中一次就殺死三十一名歐亞國囚犯。奧格維同志在二十三歲時於一場行動中殉職。他攜帶重要文件飛越印度洋時遭敵機追擊,最後抱著機關槍增加自己的體重,跳下直升機沉入海底,連同文件和所有東西全部一起帶走——這種光榮結局,老大哥表示,著實令人欣羨。老大哥還補充了奧格維同志一生的純潔忠誠:奧格維同志從不吸菸喝酒,除了每天去健身房一小時,沒有任何娛樂活動。他甚至發誓終生獨身,認為婚姻生活、家庭責任與每天二十四小時盡忠職守無法兼顧。他談論的話題只有英社原則,而他的人生目標也只有擊敗歐亞國和追捕間諜、破壞分子、思想犯以及叛徒。
溫斯頓內心掙扎著是否要授予奧格維同志傑出功績勳章。最後,他決定不授予,因為這樣就無須進行不必要的交叉比對。
溫斯頓再次看了一眼對面隔間裡的對手,感覺有個聲音篤定地告訴他,提洛森正忙著和自己一樣的工作。他無法得知上級最後會選擇誰的作品,但他堅信會是自己的。一小時前,奧格維同志還不存在,現在已成事實。他覺得有趣的是,你可以假造死人,卻不能捏造活人。奧格維同志從未在當下存在,現在則存在於過去;而偽造行為一旦被遺忘,他在歷史上的真實性就會像查理大帝或凱撒大帝一樣確實有據。
溫斯頓展在開始一天的工作時,不自覺地深深嘆了口氣,即使他正距離電幕很近也無法遏止自己發出嘆息。他把說寫機拉向自己,吹掉收音口上的灰塵,然後戴上眼鏡。四份捲成圓筒狀的文件早已從辦公桌右側的氣送管落下。他攤開文件,並將它們夾在一起。
隔間的牆上有三個孔洞:說寫機的右側是書面文字訊息的小型氣送管,左側較粗的氣送管用於傳送報紙;在溫斯頓伸手可及的側壁上,是一個圍著金屬格柵的大橢圓形投入口,用來處理廢紙。這整棟建築有成千上萬個投入口,不只每個房間都有,每條走廊上也相隔不遠就設置一個。不知為何,這些投入口...
推薦序
譯後序
《衛報》過去曾調查英國人「假裝讀過的十大書籍」,或許容易想像《戰爭與和平》、《尤里西斯》等大部頭榜上有名,但出乎意料的是,結果竟由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奪冠。近年在國內外的社群媒體,仍可見討論。作為一本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在當代社會中的份量不言而喻。
《一九八四》是我的第一本經典文學翻譯作品,一開始不免有些惶恐。面對經典的高牆,我的起手式是備妥精良的「裝備」讓攀爬的過程更加順利,若讀者希望更深入了解歐威爾,以下這幾本著作也很值得參考。
李明哲教授的碩士論文《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詳述歐威爾的生平、創作歷程,羅列可供研究的譯本名單,讓人迅速掌握二〇一一年以前《一九八四》中譯本在台灣的概況,論文核心精彩的戒嚴時期譯本分析也不容錯過。《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是美國記者艾瑪.拉金(Emma Larkin,化名)追隨歐威爾的足跡深入緬甸,以優美的文字記述旅途見聞,並且搭配歐威爾的作品,試圖理解緬甸如何形塑他的寫作,而他的寫作又如何預示了緬甸艱辛的民主之路。D.J.泰勒(D. J. Taylor)的《特搜歐威爾《一九八四》》,標題開門見山,以成書前、中、後三大部,揭露歐威爾的寫作經驗、《一九八四》出版歷程以及作品對後世的影響。
稍加掌握作者與作品的背景知識後,我穿梭在眾多譯本之間,尋找屬於自己的施力點。我相信,經典新譯若要具有意義,就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且還得呈現出個人獨特的立姿。
縱覽近年臺灣譯本,語言似乎營造出相近的氛圍,我想劉紹銘的版本也許是理解這個現象的關鍵。李明哲的碩論指出,劉譯是臺灣第一本全譯本,「劉譯的特色之一是大量使用四字成語或自創的四字語,使得譯本讀起來簡潔明快,鏗鏘有力。」我想針對「簡潔明快」與「鏗鏘有力」再進一步談談。劉譯的文字確實如同上述二詞的形容,不過「簡潔」有時出自於刪節,而其他的策略有時則為《一九八四》譯本帶來相當激昂的氣氛。歐威爾在《一九八四》的敘述冷靜平實,恐怕是擔心讀來不夠引人入勝,劉譯添加了許多活潑的描述,也更常用上驚嘆號。據我觀察,二○○○年之後臺灣譯者所產出的優秀譯本其調性或受劉紹銘影響,亦多添加詮釋、增補形容。
對我來說,歐威爾的魅力不在於辭藻,而在於簡單文字所傳達出的人類社會的惡以及渺小個人無能為力的恐懼。《一九八四》讀來的感覺,更像是開頭與結尾的天氣——寒風刺骨、大地凍結,一種冷調黯淡的可怖,骨感文句像是樹葉落盡的枯枝。這是我更想達到的閱讀體驗。一九四六年,歐威爾寫了〈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批評「醜陋又不精確」的英文寫作,並且提出六大規則,其中第二、三點是我在翻譯時特別秉持的原則:「若有短詞可用,就不用長詞」、「詞句一律能刪則刪」,不做過多修飾。不過,原則當然需要隨原文適時調整,例如葛斯坦的《寡頭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模仿托洛斯基的寫作,如爬藤植物般攀附著核心概念,我亦隨之纏繞。
翻譯非鏡像,百分之百呈現原文的譯文並不存在;語言轉換重組時,總是有些零件怎麼樣就是無法嵌合,只能忍痛捨去。在《一九八四》的翻譯過程中,我最大的放棄是重現對話中的「考克尼腔」(Cockney accent)。例如,第一部第八章溫斯頓在路上閒晃時聽到的路人對話,以及酒吧偶遇的老人,便是用模仿這種腔調的聲音和語法所寫成。歐威爾將無產階級說話的方式設定為考克尼腔,屬於倫敦東區的一種口音,常見於工人階級。在臺灣,譯者若想在翻譯文學中呈現方言,常見的做法是直接用臺語,或者是所謂「臺灣國語」(受臺語發音影響的華語)。但是,外國文學中方言所代表的弱勢,與臺語、臺灣國語所承載的政治意涵通常不盡相同。為了避免彆扭的類比,我用描述性的方式加上「倫敦工人口音」補充發話者的腔調,以此稍作區隔。
當然,上述的原則與策略絕非唯一標準,只是個人的堅持,也需要在各位讀者的腦中發揮預期效果方能成立。譯者走入相同的原文寫生,用譯文描繪風景,每一位都有各自的視角與筆觸——這也正是我們為何需要新譯本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四》的新譯,或許更重要的是提醒讀者,未來預言已成為現在進行式,又或者說是歷史不斷重演,極權統治仍在你我身邊。在翻譯的過程、甚至撰寫譯後記的此刻,就如身處倫敦的溫斯頓聽見低悶的轟隆聲迴盪,遠方的某些角落砲彈也正在落下,而那些謊言、那些篡改的史實,我們可能看得也不比溫斯頓少。
人類期待走向什麼樣的未來?這本小說是來自一九四九年的警語,如果我們願意留心,也許就能避免走到被老大哥的目光追上的那一天。
譯後序
《衛報》過去曾調查英國人「假裝讀過的十大書籍」,或許容易想像《戰爭與和平》、《尤里西斯》等大部頭榜上有名,但出乎意料的是,結果竟由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奪冠。近年在國內外的社群媒體,仍可見討論。作為一本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在當代社會中的份量不言而喻。
《一九八四》是我的第一本經典文學翻譯作品,一開始不免有些惶恐。面對經典的高牆,我的起手式是備妥精良的「裝備」讓攀爬的過程更加順利,若讀者希望更深入了解歐威爾,以下這幾本著作也很值得參考。
李明哲教授的碩士論文《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
目錄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新語概說
譯後序
【一九八四-雙重思想:驚世語錄】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新語概說
譯後序
【一九八四-雙重思想:驚世語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