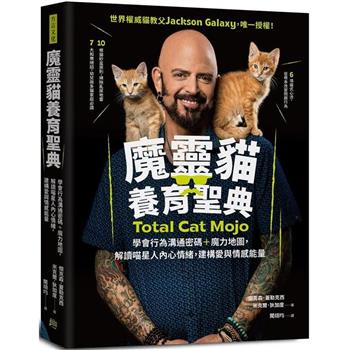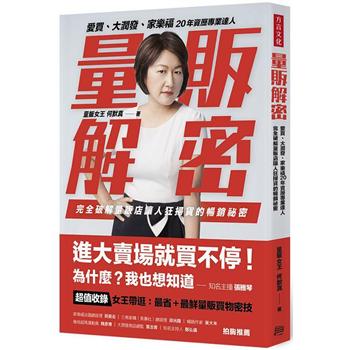連昊天是個成功的作家,也是個孤獨甚至是孤僻的作家,因為他認為,唯有遠離人群,才能讓自己那幾乎是強迫性的批判性格不致傷人。他的遊歷、見識和閱讀範疇不同於一般,這增加了他思考與批判的素材,卻也讓他難以找到能夠深刻談話的對象。
在一個駐地寫作的機會裡,已步入老境的連昊天不可自拔地愛上蔣依第。然而兩人各自有家庭的事實,讓天主教徒連昊天有著太多的掙扎,也深陷自我背叛的恐懼漩渦之中。
「不要讓我陷於誘惑,不要讓我陷於誘惑,不要讓我陷於誘惑……」
他恨透了這樣的誘惑,卻也因為依第的高雅誘惑而得到知心、知情、知意的滿足──直到依第意外懷孕。依第說,即使和丈夫離婚,同時斷絕與連昊天的關係,她也要保有肚裡的孩子。
依第主動邀連昊天面談。在一個強烈颱風來襲的日子裡,他滿懷煎熬地驅車赴約。
「狂風呼嘯,車子好像有些飄動。擋風玻璃前彷彿是一片厚厚的白簾子,幾乎什麼也看不見。突然似乎是紅色的什麼在眼前閃過,我的車子頓了一下,感覺上應該是稍微凸起路面的斑馬線區。」
狂暴的風雨中,連昊天祈求著天主的垂憐……
本書特色
老作家的自剖、自辯、自白,呈現基督宗教持續千年探討的「誘惑」、「罪」與「恐懼」;
當老作家的內心糾結以及對自我的煎熬交戰,翻躍成不得不迎面撞擊的外在現實,陰涼的悲雨終將籠罩他的前路……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誘惑 (電子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24 |
華文創作 |
$ 252 |
中文書 |
$ 253 |
現代小說 |
$ 288 |
中文現代文學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誘惑 (電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