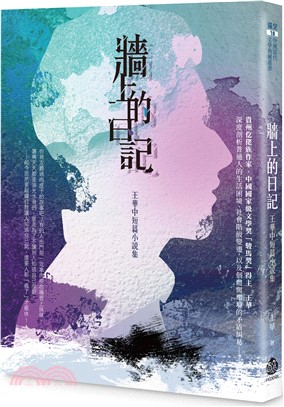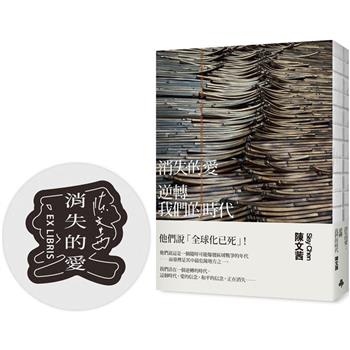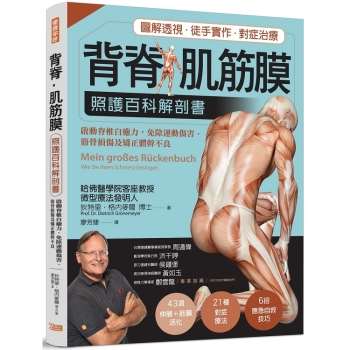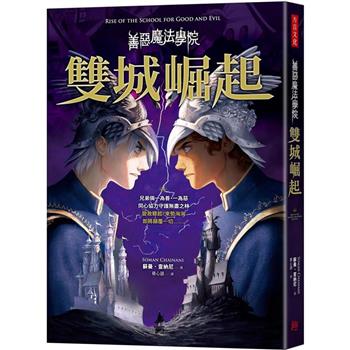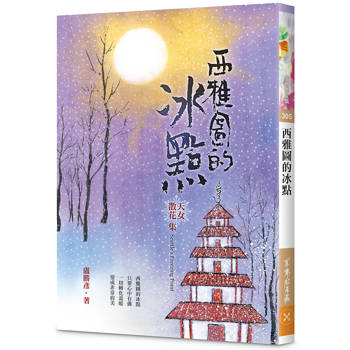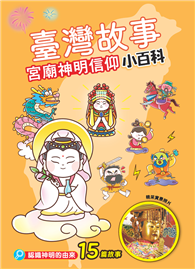接到拆遷辦的電話時,趙小蘭和李洪生都在榆林。一聽說他們的房子要拆遷,兩口子都有點懵。他們出來找兒子已經有三年時間了,這三年裡,除了跟派出所老王打個電話,打聽一下他們有沒有兒子的消息,再沒關心過別的事兒。
「啷辦?」大事小事,趙小蘭一貫都是這樣問李洪生。
「啷辦?回去啊!」李洪生也從來都是拿主張的那個人。但這一次李洪生表現得很焦躁,還很憤怒。他焦躁是因為兒子還沒找到房子又要拆遷了,憤怒是因為趙小蘭那副沒有主張的樣子。在他的印象裡,趙小蘭永遠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小事上,她從來都只說聽他的,大事上,她又從來都只會問「啷辦」。就連他們丟了兒子,她也只能問他:「啷辦?」
兒子是她弄丟的,完了她卻問他「啷辦」,你說他該啷辦呢?他恨不能揍死她解個氣,但臨了又沒有。他不是那種隨便就可以伸手打人的人,更何況還是趙小蘭這樣的人。
趙小蘭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出嫁前是父母的乖乖女,父母說什麼聽什麼。出嫁後呢,又是一位賢妻,丈夫說什麼聽什麼。你說菜淡了,她立馬去加鹽,你說菜鹹了,她立即去加湯,你叫她站著,她便不坐,你叫她坐著,她便不站。得到這樣一個人,一開始還當寶貝,時間一長,就會生膩,就會把這叫「無用」。尤其當面臨大事兒,你需要分擔壓力的時候,這樣的人,只會給你平添鬼火。
但是這一次趙小蘭居然問了一句:「那兒子呢?」這是她第一次對丈夫的主張提出質疑。
李洪生有點驚訝,因為在他的印象裡,她那腦子就是個擺設,可從這個跡象看,它其實也是可以轉起來的?好像是因為這個轉變,他的態度居然平和了些。
「兒子就暫時別找了,先回去處理房子的事兒。」他說。
「不找了?」趙小蘭問。
「不找了,我們都找了三年了,從南找到北,從西找到東,把全中國都找遍了,把積蓄也花完了。」李洪生語氣裡全是洩氣。
趙小蘭便沒再繼續提問,她那腦子好像轉到這裡,也就停下了。雖然回來的路上她沒少回頭,就像兒子可能就在他們身後那樣,但她最終還是跟李洪生一起回來了。
回到家,鄰居們個個都問:「不找了?」
李洪生便一個個回答:「不找了,先處理房子的事兒吧。」
她也一個個回答:「李洪生說,不找了,先處理房子的事兒。」
鄰居們都在忙搬家的事兒,就說:「也是,先把家搬了吧,要不然,過幾天挖掘機就開進來了。」
李洪生也這麼想,但趙小蘭卻不同意搬家。她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主張,就像那種從來開會都不吱聲的人,突然就表起了態。
她說:「這家不能搬。」
你問她為什麼,她就說:「這家要是搬了,兒子要是自己找著路回家來了,卻找不到家,啷辦?」
李小小丟的時候才三歲,大家都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李洪生也認為沒有這種可能。但她卻堅信,只要兒子有了回家的機會,他就一定會回家。三歲的時候可能不行,但現在他都已經六歲了,再往後,他還在長大,七歲、八歲、九歲……自從離開了爸爸媽媽,他就沒有停止過對他們的想念,只要一有機會,他還不第一時間就找路回家嗎?
所以,這個家,堅決不能搬。
這話的確是有道理的,所以李洪生也就有史以來第一次失去了主張,也是第一次和她發生了角色顛倒。
「那……啷辦呢?」他竟然也會這麼問。
李洪生從來都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你讓他做釘子戶,那是不可能的。這一次,是趙小蘭拿的主意:離婚。離了婚,李洪生搬自己的那一半家,她留下來。
李洪生質疑地問:「有這個必要嗎?」
趙小蘭說:「你不想做釘子戶,就只能這樣。兒子是我弄丟的,我留下來等。」李洪生聽她說這話的同時,還看到了她眼裡的意志。很顯然,趙小蘭的人生態度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她曾經的順服,服從父母,順從丈夫,服從於規矩,那都是因為,這是和平的基礎。但當這種和平遠遠偏離了她的意志,她就必須做出改變。
李洪生現在看到的,已經是一個比他更強大的趙小蘭。而他,反顯得那麼沒用,於是他問她:「那地呢?」
他們家是菜農,即便離了婚,他也可能要做菜農,所以地很重要。他們住的這地方,和離家近的兩塊地被徵了,但遠處還有兩塊菜地,是在紅線外的。
趙小蘭說:「地也一人一半吧。」
因為她跟他的打算一樣,今後也還是要做菜農的。
事情就這麼定了,他們辦了離婚手續,李洪生搬家,趙小蘭留下。
他們的家,是兩層樓的平房,結構很簡單,樓下兩大間,樓上兩大間,中間一道樓梯。這樣的房子分起來也很簡單,以樓梯為界,一人一半。原來,他們家是樓下廚房客廳,樓上住人。一分為二後,趙小蘭要了兒子原來的臥室,和正對那間臥室的廚房。
李洪生是不帶走房子的,他只帶走他那一半邊房子的拆遷補償費。所以他說:「其實我搬了以後,這房子就全都是你的了。」好像是因為這一點,他搬的時候,也就還是一副坦然的樣子。
但趙小蘭並不想要他的房子,他一走,她就將它們全鎖上了。她要那麼多屋子幹什麼,只要有兒子那間臥室就夠了。她將兒子的衣櫃歸整歸整,把自己的衣服也放進去,把兒子的枕頭往裡頭挪挪,自己的枕頭挨著放下,就把自己安頓好了。
一開始還是有些不適應,兒子丟了,丈夫也搬了,家很空,心也很空。因此頭一天,她整整一天都待在兒子的臥室裡。在這間屋子裡,她到處都能看見兒子的影子。睡到床上,甚至可以摸到,可以和他抱成一團嬉鬧。兒子喜歡在牆上亂塗亂畫,這裡一個太陽,那裡一朵花,都是幼兒園阿姨教的簡筆畫。床頭的地方,有一朵巨大的向日葵,算是他留下的最複雜的畫了。但很顯然,在用色問題上,兒子還沒出師,向日葵是紅色的。在向日葵的旁邊,是趙小蘭寫下的一句話: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半,兒子在幼兒園門口被人偷走。
那是丟了兒子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他們兩口子決定出門尋找兒子的那天晚上留下的。那天晚上她就睡在兒子的床上,臉朝著牆壁,朝著牆上的那朵向日葵。兒子的床頭正好放著他畫畫的彩筆,紅色,於是,她順手拿起那支彩筆,在牆上記下了那句話。
三年多時間過去了,趙小蘭已經沒了當初那麼多眼淚,但牆上那句話卻依然鮮豔奪目,跟那朵向日葵一樣鮮豔奪目。
這天,她一整天都睡在兒子的床上,還是當時的那個姿勢,臉朝牆,側臥。她的臉和那朵向日葵正對著,只隔三十釐米,就像兩張臉互相望著。但事實上她一整天都看著那句話,因為那句話緊挨著向日葵,她看它的時候,都不需要移動視線。
天黑下來,屋裡暗下來了。她起來開了燈,又拿起了兒子床頭上那個筆頭。好像是受到那句話的呼喚,她記憶裡那些沉睡著的日子,便都活躍起來,都爭著擠著,要到牆上去。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八號下午五點鐘,我們已經找遍了整個小河區,兒子還是沒有下落。有人說,肯定是被人販子偷走了。我們就報了案。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號上午九點過,派出所回答我們:他們已經立案,案子由老王負責,以後專門由他跟我們對接。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九號晚上,我們決定第二天出門找兒子。李洪生聽人說,最近幾年人販子都往河南河北去的多,我們得跟著這條路追。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號早上七點,我們上了貴陽去鄭州的火車。下午四點半,李洪生打電話到派出所問老王,有沒有兒子的消息,老王回答說沒有消息。
……
二○○○年三月五號中午,老王打電話說我兒子有消息了,說在陝西的吳僕(堡)縣發現了一個孩子,跟我兒子情況很像,他們正在趕過去核實。但第二天晚上八點老王又來電話說,那不是我兒子。那時候,我們正在前往吳僕(堡)縣的路上。接到老王的電話後,我們還是去了吳僕(堡),我們想見見那個孩子。
二○○○年三月十號,我們到了榆林……
三年,一千多個日子,九百多篇日記──它們擠擠挨挨占了兩面牆壁。一口氣寫完這些日記,趙小蘭感覺心裡好受了些。牆上有了她的那些日記和兒子的那些畫,這間屋子就不再那麼空寂,她也就不再那麼孤獨。更何況,她的內心還有一個等待兒子回來的希望。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牆上的日記:王華中短篇小說集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牆上的日記:王華中短篇小說集
★兩度獲得中國國家級文學獎「駿馬獎」、仡佬族作家王華,深度剖析普通人的生活困境、社會階級變遷,以及個體與環境的矛盾糾葛!
吳本末一家雖窮,生活卻未曾真正困頓過。直到他為了旁人眼中可有可無的自尊,拒絕被列為貧困戶而展開抗爭後,他們家竟越發地「窮」,而吳本末也越發地「瘋」;老年痴呆就像有一個陌生人拿著橡皮擦將趙大秀全部的記憶擦去了,擦去了她的過去、她的歲月,只留下一角關於女兒的殘片。於是,她開始反覆說起──自家姑娘被男人甩了;趙小蘭在牆上兒子塗鴉的向日葵旁寫下:「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半,兒子在幼兒園門口被人偷走」,那是牆上的日記伊始。三年,一千多個日子,寫就九百多篇日記,她仍擁有等待兒子回家的希望,先行到來的卻是房子拆遷通知……
生活悄然令他們成了群體中的異類,瘋了、病了、忘了、傻了──但他們原來並不是這樣的。
作者簡介:
王華
仡佬族作家。
著有長篇小說〈橋溪莊〉、《儺賜》、〈家園〉、〈花河〉、〈花村〉、〈花城〉,中篇小說〈旗〉、〈向日葵〉以及短篇小說〈香水〉、〈牆上的日記〉等。
曾兩次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作品被改編成電影,部分作品翻譯到海外。
章節試閱
接到拆遷辦的電話時,趙小蘭和李洪生都在榆林。一聽說他們的房子要拆遷,兩口子都有點懵。他們出來找兒子已經有三年時間了,這三年裡,除了跟派出所老王打個電話,打聽一下他們有沒有兒子的消息,再沒關心過別的事兒。
「啷辦?」大事小事,趙小蘭一貫都是這樣問李洪生。
「啷辦?回去啊!」李洪生也從來都是拿主張的那個人。但這一次李洪生表現得很焦躁,還很憤怒。他焦躁是因為兒子還沒找到房子又要拆遷了,憤怒是因為趙小蘭那副沒有主張的樣子。在他的印象裡,趙小蘭永遠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小事上,她從來都只說聽他的...
「啷辦?」大事小事,趙小蘭一貫都是這樣問李洪生。
「啷辦?回去啊!」李洪生也從來都是拿主張的那個人。但這一次李洪生表現得很焦躁,還很憤怒。他焦躁是因為兒子還沒找到房子又要拆遷了,憤怒是因為趙小蘭那副沒有主張的樣子。在他的印象裡,趙小蘭永遠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小事上,她從來都只說聽他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貓空─中國當代文學典藏叢書」出版緣起
向日葵
康復
情詩
牆上的日記
橡皮擦
向日葵
康復
情詩
牆上的日記
橡皮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