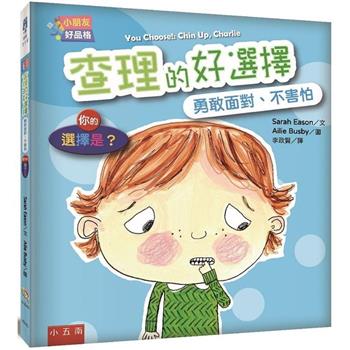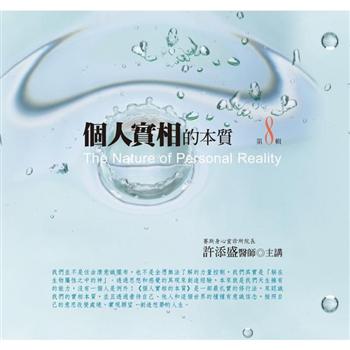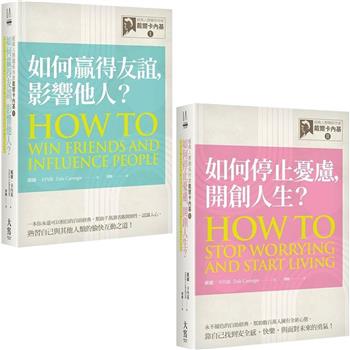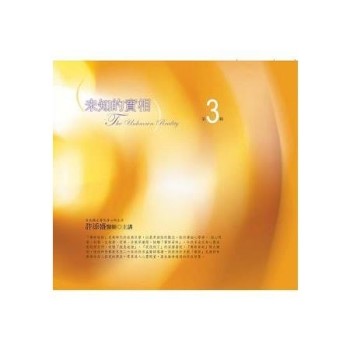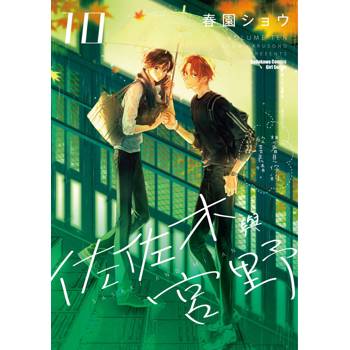名人推薦:
作家 林楷倫
作家 張維中
書評 喬齊安
────專文推薦
【讀者回饋】
當你厭倦了正向思考,不知道該往哪裡走的時候,這本書會讓你覺得,也許繼續保持現在的狀態也是可以的。我真的很喜歡這本書。(★★★★★)
鈴木涼美的著作數量多、語錄多。我經常發現自己在想,自從大學畢業以來的 15 年裡我一直在做什麼,這本書讓我想用它來重建和確認我的未來。我很喜歡鈴木涼美的書,因為讀完後我感覺充滿活力。(★★★★★)
鈴木涼美出道以來的作品我幾乎都看過,但對她的信仰不是特別認同(太固執己見,對愛情的看法也扭曲),覺得她總是說些奇怪的話。但她對文學的造詣很深,我真的認為她注定要成為一名作家!(★★★★)
關於閱讀體驗。鈴木涼美一定是在一個被書籍包圍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
一開始從《愛麗絲夢遊仙境》這本書開始討論是有道理的。當我看到書中,她在 19 或 20 歲左右時專心閱讀了這些書時,我也決定仔細閱讀這些書。其中最令人難忘的作品包括《你好,悲傷》、《靜子小姐》、《Le Grand Écart》。(★★★★★)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即使有時夜晚過於昏暗,沒有照耀文字的光
別把一切無謂之事,推諉給時代啊。
放棄只有些許光芒的尊嚴。
起碼自身的感受要靠自己守護,
愚蠢之人啊!
――――――摘自茨木德子《起碼自身的感受》
「妳覺得愛達從窗戶出去時,為什麼會回頭呢?」
這是我對於書本所能想起的最早記憶。
喜愛童書,從事相關工作的母親總是拿很多書給還不識字的我看,有時還會問我一些難以理解的問題。愛達是桑達克(Maurice Bernard Sendak,1928~2012年,著名的童書作家與插畫家)的繪本《在那遙遠的地方》(原書名Outside Over There)的主角。這一段是桑達克描繪尋找被哥布林擄走的妹妹,爬窗時往後看的愛達,結果功敗垂成的情景。
之所以往後看是怕忘了東西?這樣跳下去比較容易?還是她一直都是用這方式出去?年幼的我用有限的語言和想像力回應母親的提問。看她的表情就覺得我的回答只是讓大人覺得有趣,肯定不正確,只好再發揮拙劣想像力。結果持續一週,每晚都一邊瞅著同一本書的同一頁,和母親討論這、爭論那。這情形是從何時開始?又是過了多久而成了一種習慣?記不清楚了。不過,我還記得六歲那年全家搬到鎌倉之前的事,也記得搬家後的事,所以應該是從上小學前就開始持續好幾年吧。
每當我提出什麼看法時,母親就會故弄玄虛似地說:「也許吧。」要我繼續看下去,然後隔天又說:「搞不好發現自己忘了帶走什麼東西,不是嗎?」等待我的小腦袋瓜裡浮現其他可能性。這場問答遊戲反覆進行將近一週後,母親又拿出瑪麗.荷.艾斯(Marie Hall Ets,1895~1984,美國作家和插畫家)的《和我玩好嗎?》,母女倆一起閱讀。閱讀到動物們圍繞在女孩四周的最後一幕時,母親又問「仔細看這幅畫,前方好像有個像是壞掉柵欄似的鐵網,不是嗎?妳覺得這是什麼呢?」
這麼做能讓年幼的我的想像力變豐富嗎?我不知道。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為何愛達爬窗時往後看的行為是個大錯誤,也不清楚詭異的構圖到底哪裡詭異。十歲時的我厭煩這樣的閱讀方式,連帶地也討厭母親的藏書中,那些奇幻、少年少女的冒險故事,只想看漫畫和內容有點情色的茱蒂.布倫(Judy Blume,美國最受歡迎的青少年小說作家之一,大膽談論月經、性愛、宗教等議題)寫的小說等。
上國中後,周遭多了許多比漫畫和小說更有魅力的事物。好比看連續劇、歌唱節目,隔天和好友們聊著自己喜歡的歌手穿的禮服,不然就是放學後去速食店,點個小杯可樂待上三小時,再去KTV飆唱新歌、上個美美的妝,盡情消磨時間;一夥人也會開始聊些關於戀愛和性的話題,就算考前才花個三小時臨時抱佛腳都覺得浪費時間,青春就這樣逐漸染上繽紛色彩。
母親不再拿桑達克、艾斯的書給我看,只要求我睡前翻看幾頁書,什麼書都行,以及每個月至少閱讀一本英文書,還有要是和誰成為朋友,就算吵架、意見相左、沒了共通興趣,也別輕易和對方斷了聯繫,要我遵守這些事就行了的母親則是埋首於她的工作與興趣;不過,母親在我的房間擺了一個她的書櫃,擺些她國高中青春期讀的書。
有好長一段時間,從未想要翻閱這些書的我望著書櫃上成排的橋本治、金井美惠子、莎岡等人的詩集、小說、散文和遊記,心想母親只是把她書房裡塞不下的書放在這裡而已。
國一時,一直禁錮在小孩子框架中的我沉浸在變得廣闊的自我世界,無論是快樂的事、刺激的事、曇花一現的事,還對有點悖德感的事感興趣,因為到處都有比奇幻世界來得更生猛又直接的刺激。父親看我這樣子,遂從書庫拿了幾本書對我說:「要是覺得和媽媽一起看的書很無趣的話,這幾本應該比較有趣吧。」我依稀記得有村上龍的《寄物櫃的嬰孩》、狄克的《銀翼殺手》、克拉克的《童年末日》、村上春樹的《開往中國的慢船》、井上廈的《BUN與HUN》,以及杜斯妥也夫斯、遠藤周作的作品。我也是有一搭沒一搭地翻閱,赫然發現這些書堆積在房間的書櫃上有好長一段時間。
十四歲、十七歲,我的世界變得更扭曲。看在大人的眼裡,就是叛逆與特立獨行,缺乏知識又思慮不周,看什麼都不順眼,染上名為「年輕」的感冒吧。無法忍受稍微有點約束的規範與乍見並不合理的規則,無視這一切好快樂。根本不明白什麼是真正的自由,目光短淺、行事衝動、平庸、牢騷滿腹,討厭被約束,只想逃避,卻沒想到這麼做反而讓自己更不自由。
那時的我雖然成了叛逆少女,卻慢慢地拿起父親給我的書,還有母親放在我房間裡的書,大量閱讀。肯定是本能察覺自己根本沒什麼料,所以無法確切形容與表達自己的不滿與欲望。也想起母親和我透過書來對話的往事。我就像個口渴難耐,快要癱倒的拳擊手,拿起擺在書櫃上的書,探索家裡的書庫,還利用白天上學,夜晚出遊的空檔時間去趟書店。我討厭學校圖書館的陰森感,卻又喜歡窩在這地方,以往被動的閱讀模式完全幻化成主動追求。
就在我雜食性閱讀各類書籍時,逐漸明白自己的閱讀口味。有些人喜歡能讓腦中浮現情景的描寫,也有人樂在享受詭計與結局,或是愛上書中人物;對我來說,一味追逐印刷在紙上的大量文字,邂逅到怦然心動的文句就是閱讀的醍醐味。只要有一行讓人很有感的文字,即使不喜歡書中人物,就算故事發展不夠驚心動魄,結局一如預期,或是內容艱澀到看不太懂,我還是覺得這本書值得閱讀。我想,這一定是和我想加強詞彙表達力而閱讀一事有關。只要看到喜歡的文句就用便利貼標記,不然就是劃線、抄寫,這是我從高中就養成的習慣,迄今也還在追求令人怦然的文句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