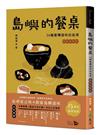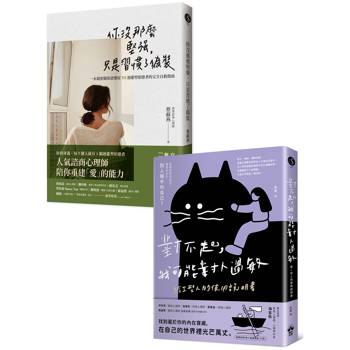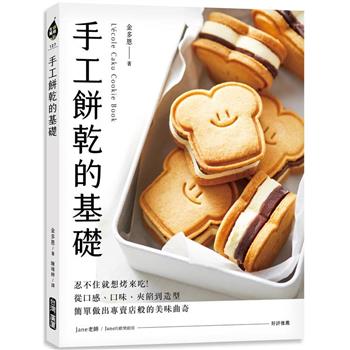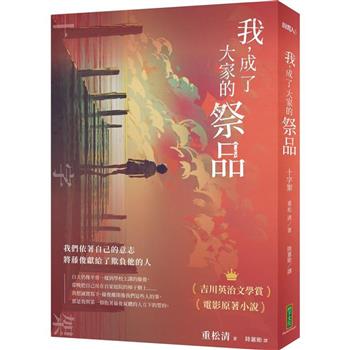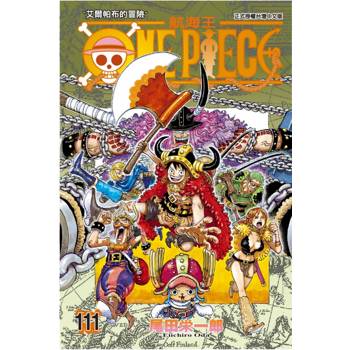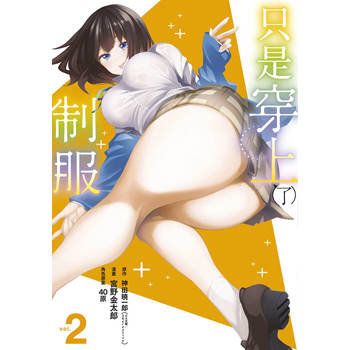序
我家的餐桌,我的田野
起初,我並不知這張小小的自家餐桌,有如此廣大無邊的田野。
長久以來,我一直以編輯採訪為業,誰知到了二○○七年夏天,改變的念頭不斷蠢動,卻又不知從何著手。日子一天天流逝,飯還是一餐餐吃著,即使身處這股中年失落的憂鬱裡,無論是母親煮的菜還是自己弄的飯,吃來都仍別有滋味,生命的熱情在餐桌上依舊澎湃著。是啊!在暫別探詢他人生活、編寫別人故事的想望中,就「姑且」依靠一下每天都要吃的飯菜吧!
秋天,部落格「我家的餐桌」架起來了,菜上了,起初只是隨意記錄,啊!這是從小吃到現在的菜,那是大學時才嚐到的滋味,還有這是進入職場以後才出現的嗎?穿梭在這些光陰釀造的菜盤裡,人雖住在板橋,天天活在北部味道裡,但心裡卻總想大學以前在彰化度過的歲月,那歲月裡有許許多多屬於童年,屬於青春期的美味,慢慢的跨越中部時代的滋味,更遙遠的臺南食物也進場了,那是父親出生地的特產,祖父母眷戀的家鄉味。
餐桌的尋味,就這樣從自身的回顧開始,依循父親的足跡,走著走著,卻驀然發現母親一直走在前頭。記得,前年冬至,我端出一碗母親煮的雞湯麵線,寫到因母親不肯放棄在彰化養成的習慣,我家除了立冬日,冬至這天也會進補。格友尤加莉看到了,在我視一年兩次進補為理所當然之事的敘述中,她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母親,一個「好有味道」的母親。尤加莉,以前的同事,從餐桌開張以來,一直支持我上菜的人,她的留言,讓我發現自己寫餐桌的菜,不知不覺勾勒了母親的身影。
是的,這桌菜的靈魂終究還是握在母親的手裡。從水餃開始,歷經獅子頭、牛肉麵、餛飩湯,一直到義大利麵。這一道道菜,貫穿半個多世紀以來劇烈的時代變動,被母親端了出來。母親,一個平凡的臺灣家庭主婦,八○年代初從中部小鎮來到北部都會,歷經一段江浙餐館的打工歲月,她勇於接受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菜色挑戰,甚至在九○年代全球化席捲的飲食浪潮裡,也沒有缺席的找到屬於自己的做菜姿勢。不過,她自始至終沒放棄自小在彰化農家養成的飲食信念。
這份堅持,過去我沒發現,即使餐桌開張了,尤加莉留言了,還是沒能掌握。直到那天,「鹹小管配清粥」上桌了,身為半個澎湖人的barachi來留言,他說他「和鹹小管也算時常見面,通常都是難以消受那劇烈的重鹹,看來下次也該依樣畫葫蘆地體會一下父輩熱愛此物的心情……」啊!有人要「依樣畫葫蘆」,這曾讓我難於舉箸的鹹小管,有著讓人想體會「父輩熱愛此物的心情」的衝動嗎?母親的鹹小管竟有這般魅力。那魅力裡有著令barachi的父輩和我的母親難捨的堅持嗎?
立夏,隨筆寫下蒲仔麵,自謙對節氣習俗只是考證派的Arkun看了,十分感動仍有人傳承這個習俗。我才恍然大悟,從彰化到板橋,母親努力記得要吃的蒲仔麵如此有分量,當然這也激勵了我的某種「本能」,過去在職場磨練出來的「本能」,面對田野裡的被採訪者(報導人)總想問想追究……
有時,我這個田野採集者也會扮演起報導人的角色,自己下廚,結果端上桌的不是帶著日本和風的洋味、就是濃濃的西方口味,母親的菜我總是煮不來,明明我是吃母親煮的菜長大呀!餐桌因此常出現一些遲疑,一些苦思而上不了菜。
進入盛夏前,身體出了狀況,動了小小手術。沒想到,母親的鱸魚湯,讓我迅速復原了,而一碗不起眼的蕹菜湯,竟讓我找回了平常心。這些菜看似平凡,但就是有力氣,而這種平凡的力氣就是母親飲食裡的堅持吧!
七夕,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回到常軌的餐桌端出了油飯與麻油雞,這兩樣母親視為理所當然、年年七夕都會煮的食物,竟為餐桌開啟了另一個視野。
多年來致力於母語保存的臺語創作歌手一蕊華(王昭華)聞香而來,她說好多年沒吃七夕的麻油雞與油飯了,還說她的家鄉屏東潮州這天還會吃芋頭湯,七夕吃芋頭湯,我首次聽到,不過,這也讓我想起以前在彰化時,七夕供桌上還有一種中間有凹洞的湯圓(糖粿)。沒想到一蕊華說那是要裝織女眼淚的湯圓!雖沒吃過更不曾見過,但國中時她在《千江有水千江月》書中讀到有關它的描述。一蕊華說,那時她才知有人在七夕吃湯圓。
原來兒時七夕吃的湯圓有如此美麗的典故,我竟不知,而對於家鄉為何七夕要吃芋頭湯,一蕊華也不確知,儘管如此,她的七夕芋頭湯與我的七夕湯圓,確實隨著餐桌上母親煮的油飯與麻油雞浮現了。其中也許有時空的脫落或隔絕,不過,同樣的臺語家庭,一在屏東,一在彰化,各自以不同的食物寄託對七夕的想像卻是真實存在著。如此一想,從我家的餐桌望去,我好像看得到一張地圖,有著不同地方不同人家餐桌的樣貌……
九月,想起端午節的粽子。雖搬到北部,但母親綁的一直是彰化時代的水煮粽,就是所謂南部粽。北部的熟米蒸粽,儘管見識過也吃過,但母親從不做。正當我從個人的記憶出發寫五月粽時,月桃葉縛粽從一蕊華的童年回憶出現,獨鍾南部粽的一蕊華說她長大以後才知道有人用竹葉縛粽。而我,如不是吃過臺南的花生菜粽,也不識月桃葉。這時曾以「飲饌紀行」做為自己部落格名稱的polanyi來了,家在北部,人在南部工作的polanyi說他比較喜歡一蕊華口中「竹葉包油飯」的北部粽,雖然他的阿母是臺南東山人,家裡的粽子是用「煠(水煮)」的。好奇妙的一刻,說自己喜歡那種食物,也要說說自己打哪來,父母又是哪裡人。食物好像會透露人的足跡。
我的「看家本領」一發難收。一碗有祕方的麵上場了,餐桌上的地圖越鋪越遠越廣。這碗母親煮的麵,我從小吃到大,家常又簡單,寫著寫著,寫到了兒時在臺南親戚家喜慶場合裡吃過的魯麵。這碗充滿臺南古都典雅風的魯麵,竟讓Arkun想到在中國華北吃到的打滷麵,而帶著中國北方味的打滷麵到了臺灣就成了polanyi在大學旁麵攤吃到的大滷麵。
這又是一次意外的餐桌地圖之旅,一蕊華的加入讓它更添時代味道。她說小時候沒聽過「魯麵」,倒是對「大滷麵」印象深刻。有次姐姐帶她到鎮公所對面的「江浙小吃部」說要吃傳說中好吃的大滷麵,麵店很吵雜,外省伯伯聽到兩個小學生要大滷麵,不可置信的高聲重複大喊:「兩位小姐要吃大滷麵!?……」大滷麵來了,竟大碗到超乎想像,感覺滿屋子的大人都在看她們,而那麵也不是原先想像的有如滷蛋、滷肉、滷海帶之類的滷醬,竟是酸辣湯加麵……
餐桌的菜繼續上著,旅程尚未結束。十月底,還來了一位高雄女孩花丸子。小時候吃辦桌最渴望吃到的雞捲,母親像變魔術般的讓它在年夜飯上現身,這回花丸子重新將它熱上桌,她說阿嬤捲的最上等,偏偏媽媽不會,媽媽雖是長媳,但阿嬤年紀大了等不及,已將做雞捲的手藝傳給了比媽媽早好幾年進門的嬸嬸,因此,每年的年夜飯,不會做雞捲的花媽總在嬸嬸的炫耀中吞下心酸淚。從花丸子傷心回憶裡的這段家族恩怨,我首次意識到我家餐桌上的雞捲,在臺灣家庭餐桌上的地位。
我家的餐桌,從母親做的菜開始,在我的回憶裡,在我的文獻梳爬裡,在這些料想不到的網路共鳴裡,母親對飲食的某種堅持逐漸被勾勒出來,一張屬於臺灣土地滋味的餐桌不知不覺浮了出來。
廚房的火依舊開著,飯繼續煮著,用蓬萊米炒出的飯,再平常不過的一碗炒飯,竟炒出臺灣島的光與熱。而翻開上個世紀歐美飲食名家的作品,在遙遠美國南方的老派食譜裡,竟有油粕仔的身影。這被許多人視為廢物的油粕仔,到了法國普羅旺斯的肉品店,還被做成地方引以為傲的肉泥醬。原來油粕仔有如此不凡的身價。母親,甚至所有臺灣母親做菜的身影,藉著油粕仔上桌,穿越時空,最後竟與世界另一端的母親、老祖母疊合在一起。
這真是一趟又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那些母親經年累月煮著的菜,我們吃來平淡無奇的菜,竟道道說得出故事,而自己偶爾下廚煮的菜,雖稚嫩而無名,但卻不知不覺融入自己成長的滋味,流轉其中的又是一個接一個時代的氣味。至此,故事的發展已不只侷限於我個人或者我家……
如今,餐桌的菜要匯集成書,首先感謝我的母親,再來就是常年在餐桌捧場的家人,特別是我最愛的姪子與姪女,以及幾位堅定的熱情「吃客」,還有慷慨將相機腳架借我大半年的友人。當然如果少了格友的激勵,這些菜終究只是被吃下肚,而無法用文字或影像再次烹成可以謹記在心的菜,而格友,除了以上那些不斷帶給我啟迪者,還有常與花丸子拼場的程、熱愛臺灣的bigburger,以及在太平洋彼岸的morning、新加坡Iris、法國Sophie Chiang和kimberly、小米媽、喜波桑等散居各地的格友,他們對生命的熱忱因而延伸出對食物的執著,或在異鄉想念家鄉或思念阿嬤煮的食物,都是我的動力。米果的不吝留言更是力量。而在playtime那裡玩樂,總會找回一些已逝的青春滋味也一直銘記在心。啊!記憶所及必有我所疏漏的知味格友和無法點名的潛水客,在此我一併致上由衷的感謝。最後,對於遠流的靜宜與詩薇催生了此書也有說不出的感激。
這回,我為書中每道菜做了更深刻的尋味,希望這種綿延不絕的歲月滋味,能激起更多人的共鳴與想像,在舌尖的想像中,想起自家的餐桌,想起每個人的媽媽、阿嬤,甚至所有生活中的甜美滋味……
初版推薦序
餐桌上的尋味之旅
王宣一(作家,《國宴與家宴》作者)
二○○七年的秋天,陳淑華在網路上擺起了她家的餐桌。她原本是在媒體工作的資深報導人,走遍中國大江南北、臺灣全島各地,寫過編過不少和土地、文化、生態、歷史相關的書籍和文章,但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某種因緣的促動,她開始了飲食寫作。
也許是因為過去訓練有素的田野調查背景,淑華的飲食書寫有她自成一格的文化脈絡,她不但認真追究她家餐桌上的菜餚,也很自然地開始追尋媽媽做菜的手路與滋味,當然更免不了的,廣閱文獻,開啟了飲食上的田野踏查旅行。
幸運的是回首兒時滋味,她的母親仍在身旁,母女每天輪流上菜,當她端出一道菜來,母親也還能端上三道菜,好學愛做的陳媽媽,即使自己不吃牛肉,但仍會為孩子們燉煮一碗牛肉麵,而這份手藝終於最後被淑華接手,她實驗了不同版本的牛肉麵的作法,也變化了一些日式或西式料理,並且帶領著姪輩們一同動手,而她勇於嘗試製作新式料理的母親,更是從她那裡學到了義大利麵的麥香彈牙風格,做出一盤一盤風味獨具的pasta,母女甚至一起參加義大利麵美食競賽,陳媽媽還得到了獎項呢。
雖然她的母親原本不過是一般的家庭主婦,端出的菜色大多是六○年代閩南家庭餐桌上常見的家常菜,蕹菜湯、菜頭粿、蒲仔麵、麻油雞、鹹小管、魯肉飯、炒豆芽,但是在八○年代之後,她家裡的餐桌偶爾也出現一些「淮陽名菜」,有時候端出大盆子的獅子頭或小碟子的腐皮捲,過年時還有一品鍋。原來她的母親曾在臺北著名的江浙菜餐廳「秀蘭小館」打過工,她的阿姨更是秀蘭開創時期的主廚。但不論做哪一種菜色,她的母親卻始終堅持遵循該有的步驟。
以往不起眼的古早味,在今天卻顯得異常珍貴。油粕仔(豬油渣)、扁魚肉羹、清明潤餅、尾牙的米糕糜,或是用水打出來的手工獅子頭等等,甚至當淑華再度回想或品嚐一些以往無法吸引她下箸的菜色,突然發現許許多多童年時未曾珍惜的平凡食材,有著不一樣的滋味。例如大年初一早上母親為他們準備的「春飯」,白米飯配上幾株長長帶紅根的菠菜、豆腐、荷蘭豆和幾粒花生米,味蕾在她成年之後重新在母親的餐桌上被啟動。她愈吃愈嚼愈有味道,逐漸體會出蘊含在食物裡的意義與其中深層的好滋味。
這本《島嶼的餐桌》,記錄的不止是作者家庭餐桌上的日常飲食,也敘說了臺灣六、七○年代典型的家庭餐桌上的故事,作者除附上簡單的食譜與製作的小撇步,還延伸出一篇篇旁徵博引的飲食典故,讓讀者更清楚的明暸這些食材或佳餚的孕育環境與來歷。
我自己極嗜吃臺菜,在雜誌上推薦的美食餐廳小店一半以上都是臺菜餐廳或小攤,因此當我捧著這本書稿閱讀或到淑華「我家的餐桌」部落格瀏覽時,常常讓我飢腸轆轆到極點,想立刻拋下書稿到廚房去複製陳媽媽的菜色,當然如果能有機會到她家的餐桌上吃碗鹹粥更好,還有不能錯過筍乾、雞捲、白菜滷……。若能撒點油粕仔一定更香!
新版推薦序
從家之味開啟臺味探索之路
陳靜宜 (作家,《喔!臺味原來如此》《我說福建麵,你說蝦麵》作者)
文學作品裡,不乏女性作者以家庭為出發點,透過飲食書寫,帶出家族情感、時代背景等。如辛永清的《府城的美味時光:台南安閑園的飯桌》、陳翠玲《我的東引,你的小島》部分篇章、王宣一《國宴與家宴》,以及陳淑華《島嶼的餐桌》等,各自在不同時代、不同家庭結構下訴說自己的故事。
《島嶼的餐桌》作者陳淑華生在閩南人家庭,原住彰化、後因故遷至板橋,書中收錄的三十六道菜橫跨約一九六○至二○一○年(自她幼年至該書初版出版為止),代表臺灣五十年來的縮影;而我也是閩南人家庭,也從臺南遷居臺北,曾經落腳土城,生活年代也大致重疊,因此特別有共鳴。
作者擅長細寫家常食,她並透過民間信仰、時令習俗溝通食物的意義,溫柔的筆觸讓人想到《京都家滋味:秋冬廚房歲時記》裡,婦人的娓娓細訴。她家餐桌上的菜,一受時代趨勢,二受家庭環境改變,包括:舉家北遷、母親出外求職、飲食西化等出現了明顯變化。
一開始是許多閩南系統家庭常見的鹹飯、肉豉仔、白菜滷等菜色。一九四九年後,大批閩南地區以外的中國大陸人(外省人)移居臺灣,本地人增加與外省人互動的經驗,她家的餐桌也受到外省鄰居影響,中國北方水餃、鍋貼也躍上餐桌。
接下來,陸續出現跟過去菜色大相逕庭的獅子頭、白濃雞湯、牛肉麵、腐皮捲(簡版兩筋一)等,源於母親成為職業婦女,並且還是在臺北知名江浙餐廳「秀蘭小館」工作,可說餐桌上最戲劇性的轉折,這代表了雙重變化:一是從家庭主婦轉型為職業婦女,也從素人廚娘踏上專業級廚師的階梯;二是從閩南菜跨足到不同系統的江浙菜。我們可以發現,她母親並未自我設限,反而透過新的學習,豐富了餐桌的風景也打開作者的飲食視野。
隨著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解嚴,報章媒體得大量傳播各類資訊,民以食為天,跟常民生活相近的飲食成為重點,她也受傳媒影響,做出跳脫家族脈絡、生命經驗的「十香如意菜」,像是天外飛來一筆,她大意上這樣說:「電視上的烹飪節目或報紙的美食專欄端出一道道年菜,我很想改造自家餐桌上數十年不變的年味,這道菜就成了我行動的起點。」接下來是加工食品、進口食品量產問世,容易購得起司、白酒、奶油、番茄罐頭,她也跟上時代脈動,義大利麵、可樂餅成為她餐桌上的常客。
《島嶼的餐桌》追尋家之味,是陳淑華飲食書寫的開端,溫柔樸實;第二本《彰化小食記》以探索家鄉小吃為核心,進而比較追究臺灣各地相關小吃,周詳細膩;第三本《灶邊煮語》則更大企圖地梳理比較閩客族群的飲食手路,我認為想要學好臺客菜,必須學會臺客語的烹飪用語,因為每字代表不同火侯與烹調技法,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也能從中理解臺菜的奧妙之處,此書為教科書等級的存在。讀者可透過作者島嶼飲食三部曲的演繹軌跡,開啟對臺味的探索與追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