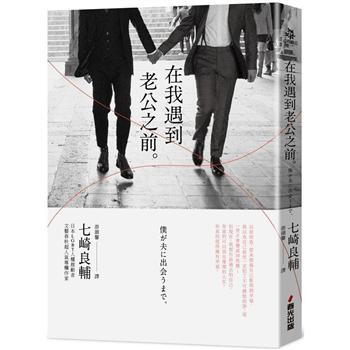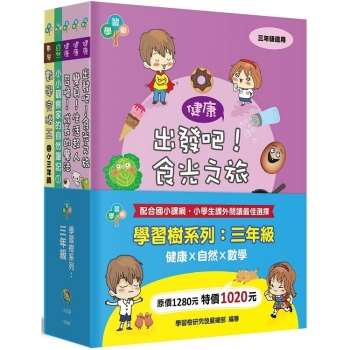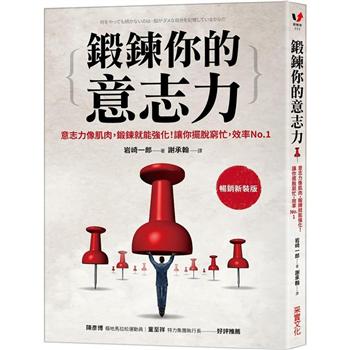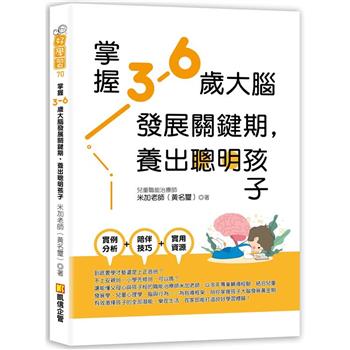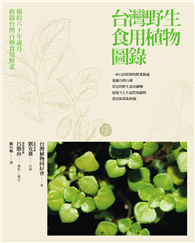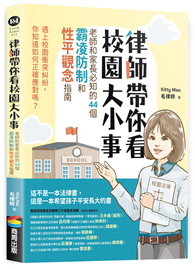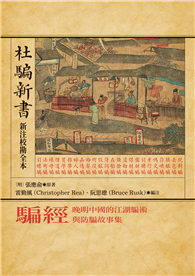◆牽動晚明江南社會秩序的鄉紳,他們的威信與勢力從何而來?
◆陽明學為何成為晚明江南地區民變事件的思想源頭?
◆晚明興盛的出版文化,在江南社會的群眾運動中扮演何種角色?
◆明清大變局中,江南社會的民眾如何自保以維持生計,又如何看待新政權?
明清史研究經典名著
《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為岸本美緒教授立基於「地域社會論」的集大成之作。書中以由下而上的視角,生動刻畫江南社會的動態、資訊傳播下的民眾集體行動,以及政權交替時期江南地域的官、紳、民的關係,探討在明末清初的動亂之中,地方社會的能量如何從危機轉向秩序的重建。
岸本美緒深入淺出地解讀地方史文獻,將目光聚焦於民眾面對變動局勢的回應方式。藉由明清之際江南社會發生的事件或民變,解析「當時的人們為何採取那樣的行動」、「怎樣的狀況使人們朝向這個方向運作」、「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等問題,並從中帶出社會流動與輿論擴散、社會不安與民眾運動、陽明學流行與民眾心態,以及國家權力與民眾對應等重要課題。
名家推薦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甘懷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誠摯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十七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的圖書 |
 |
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十七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 作者:岸本美緒 / 譯者:吳靜芳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3-2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64頁 / 14.8 x 21 x 2.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95 |
中國歷史 |
$ 521 |
明史 |
$ 521 |
中文書 |
$ 521 |
中國各朝歷史 |
$ 521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59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十七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岸本美緒
歷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助教授、教授,現為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日本學界中國史研究的代表學者之一,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經濟史。代表著作有《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明清史論集》(四冊)、《明末清初中国と東アジア近世》等。
譯者簡介
吳靜芳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專長為明清社會史、中國醫療史。
岸本美緒
歷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助教授、教授,現為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日本學界中國史研究的代表學者之一,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經濟史。代表著作有《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明清史論集》(四冊)、《明末清初中国と東アジア近世》等。
譯者簡介
吳靜芳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專長為明清社會史、中國醫療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