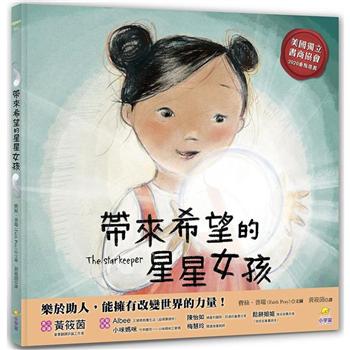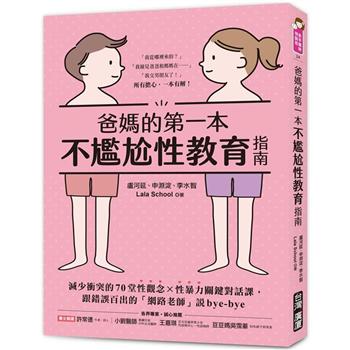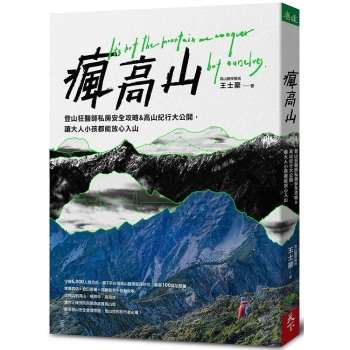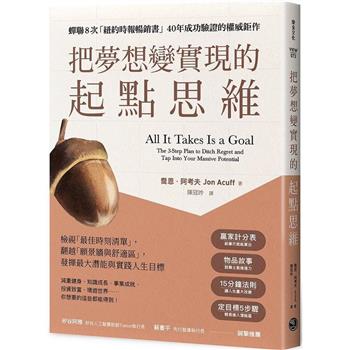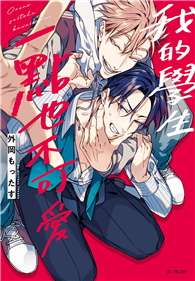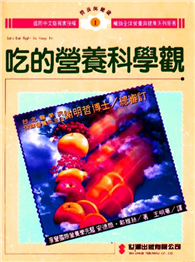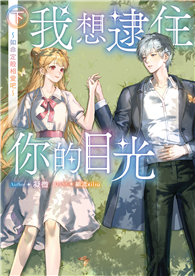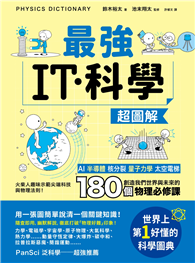本書揭露20世紀以來 11 場重大戰爭中的媒體操弄手法,包括了:
● 美國如何利用媒體發動戰爭
● 西方媒體如何塑造敵國形象
● 韓戰與媒體宣傳
● 波斯灣戰爭的輿論操作
● 新疆問題與國際輿論
● 利比亞戰爭背後的媒體戰
● 天安門事件的真相與爭議
● 北韓形象塑造的歷史演變
如果你對國際政治、戰爭史、媒體研究以及地緣政治等有興趣,絕對能在本書中,更深刻地了解假新聞(Fake News)、媒體操弄(Media Manipulation)、戰爭宣傳(War Propaganda)、輿論戰(Public Opinion Warfare)、捏造暴行(Fabricated Atrocities)、國際衝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s)、信息戰(Information Warfare)等各種戰略,是如何環環相扣,影響全球輿論與世界秩序。
本書列舉十一個近現代較知名的國際衝突及戰事案例,分析各案例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及案例中主要參與的國家、組織或個人,在主流媒體中的形象。而這些形象帶給國際社會的觀感,往往就是導致國際社會對於該場戰爭或衝突,給予支持或反對的主要依據。這些輿論形象的呈現,對歷史發展與往後國際政治環境的形塑,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同時,在十一個被捏造暴行國家的案例中,詳述捏造出來的暴行如何為實質的侵略行為鋪路,導致被誣陷國家的人民在遭遇戰爭和軍事介入時,面臨到的真正暴行;而這些真實暴行的罪惡程度,往往遠超出當初西方勢力透過媒體所捏造出來的虛假暴行。
第一章 冷戰初期的古巴與越南
分別描述了美國如何在侵略古巴及出兵越南之前,創造了適合美軍發起軍事行動或合理化其戰爭行為的輿論環境。而在兩場軍事行動失利後,美國又是如何透過西方媒體引導國際輿論走向,合理化其發動軍事行動的正當性。
第二章 韓戰
釐清在韓戰期間,西方盟軍事實上也曾進行過不人道的戰爭行為,或曾發起過不符合交戰規範的屠殺行為,然而西方世界最後都將這些罪行推到了敵軍身上,規避原有責任。另外,關於韓戰期間美軍及西方國家戰俘宣稱曾遭受過的虐待,作者也嘗試以各方資料查證是否屬實。
第三章 1989年的北京和天安門廣場
從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並開始與西方民主資本陣營開始對峙講起,指出目前西方主流媒體對於六四天安門期間,中共政權曾發動過大規模血腥鎮壓的描述或許存在誇大嫌疑,並以蒐集到的資料,試圖還原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始末與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章節最後分析中國與西方世界在天安門事件後的關係演變。
第四章 波斯灣戰爭
伊拉克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的舉動與之後的壯大,讓西方世界開始對伊拉克產生戒心。指責伊拉克在入侵科威特期間曾犯下非人道暴行的「奈伊拉證詞」,更促成了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波斯灣戰爭。然而事後各方對奈伊拉身份及其證詞真實性的質疑,連帶也讓外界開始懷疑美軍以此發動對伊拉克軍事行動的合理性。此次波斯灣軍事行動帶來的數百萬人傷亡和流離失所,更證明了捏造暴行將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第五章 南斯拉夫內戰
簡介蘇聯解體後的南斯拉夫局勢、西方國家與前南斯拉夫成員國家之間的利益糾葛、南斯拉夫走向解體並爆發內戰的背景,最後說明北約和外國勢力介入南斯拉夫內戰所帶來的影響。
第六章 伊拉克戰爭
九一一事件爆發後,美國積極將蓋達組織與伊拉克掛勾,最終以藏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和海珊政權的所謂暴行為由,出兵伊拉克。作者在本章針對美軍當時的出兵理由提出多項質疑,同時也提出多項證據認為美國針對伊拉克政權的暴行指控存在漏洞,而以美軍為首出於「人道主義」的外國勢力介入,也對伊拉克當地人民往後的命運,產生深遠影響。
第七章 美國與北韓之間的衝突
當愈來愈多的「脫北者」在西方媒體鏡頭前亮相,北韓共產、獨裁、落後的形象透過這些脫北者的描述深植國際社會。然而當脫北者的描述被發現疑似造假、西方媒體掌握或傳播的許多北韓資料來源似乎也有問題,究竟國際社會對於北韓的認知是否足夠客觀?在南韓天安艦沉沒事件、金正恩哥哥金正男於馬來西亞機場遭到暗殺、美國學生在北韓旅遊遭拘捕,以及北韓駭進索尼影業的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似乎有必要重新調整對北韓的認知。
第八章 北約與利比亞的戰爭
北約介入利比亞的戰爭究竟是出於真正的人道主義,抑或是出於想像中的伸張正義?作者在本章點出西方世界合理化出兵利比亞的背景,以及西方世界號稱主持公道的軍事行動,對當地居民帶來怎樣的衝擊。作者最後認為,西方世界介入利比亞的模式,或許也會是未來西方世界國家想要軍事介入他國事務的公式樣板。
第九章 敘利亞叛亂
章節開頭先描述敘利亞的政治及歷史背景,以及敘利亞與西方世界之間的矛盾。當獲得西方支持的叛軍在敘利亞起義,而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也發動武裝鎮壓,西方世界只能加強介入力道,並對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實施更緊迫的打壓,致使敘利亞的內戰至今尚未結束。
第十章 新疆與中美矛盾
新疆問題是近年國際社會用以抨擊中共政權的一大焦點。西方世界也不斷透過各種媒體管道、流亡新疆人組織等,對中共政權發起輿論譴責或抵制,並逐漸提升對新疆的聲援力度,試圖對中共政權施壓。不過這背後或許並不是單純的新疆問題,還與更廣大的中美對立,以及目前以歐美為主的西方世界霸權欲維護既有國際秩序,想要以此制衡中共政權的勢力發展有關。
名人推薦語
「亞波汗.艾布斯透過本作提供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將有關所謂暴行的『假新聞』,從它主要被討論的事務場域中抽離出來,將其放入一個更廣泛、更深刻,事實上甚至更令人不安的脈絡下進行討論。他洞見觀瞻地追溯了捏造暴行敘事被使用的方式及過程演變,從西方戰爭和殖民擴張之初一直到近期,舉出十一件個案研究。令人不寒而慄的是,他記錄下西方列強如何透過暴行敘事來主導資訊領域,從而導致衝突造成的結果,遠比原先所指控的暴行後果更糟糕。學者、記者和其他對了解國際事務抱有濃厚興趣的人都會發現,本作中發人深省、石破天驚的分析,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彼得.福特(前英國駐敘利亞大使)
「亞波汗.艾布斯以外科手術式的精準筆觸,震撼揭露了干預主義集團武器化人權議題,意圖造成敵國動盪並荼毒該國人民的行徑。」──馬克斯.布魯門塔爾(記者、《灰色地帶》編輯、著有「紐時」暢銷書《共和黨的娥摩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