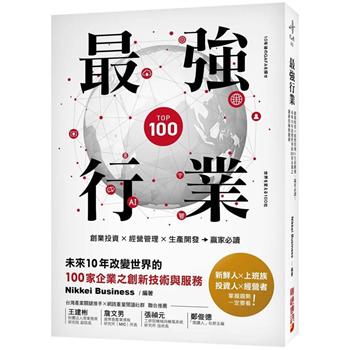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文藝腔低、敘事平順,卻常常在某些暫停的段落,發出令人沉思的喟嘆。」
──吳明益
吳明益/作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柴柏松/詩人
專文推薦
小令/詩人
白樵/作家
何致和/作家
房慧真/作家
敷米漿/作家
驚豔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每當他望著無盡的街道盡頭,
那輪在模糊地平線上的圓月時,
他就會想起身後的街道盡頭
同樣也有一輪一模一樣的圓月。
用沙築起的壇城,幽魂遊走其間,前世的情結勾連離世的悵惘。當風吹起時,有沒有虛無之外的歸向?
《沙壇城》由七篇短篇小說構成,既有馬來西亞的風土質地,也有夢境般的閾限空間,有命運的膠著,也有機遇的玄奇。那些遭受屈辱、排斥、孤立的人物,從縫隙透出的氣息與光線得到一瞬解脫。
來自檳城的新銳小說家林俊龍,在精簡篇幅中描畫出鮮活的形象,帶出奇異的轉折,傳達耐人尋味的意蘊,以輕巧的筆觸將故事帶往迷宮的出口。
〈雨樹之下〉(東華奇萊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
身世不明的母女成了村民仇日的替罪羊,但有個男孩透過風與鳥鳴認識到那個女孩的真實。
〈第二片屋瓦〉(西子灣文學獎小說組首獎)
經商失敗的老李與妻子女兒搬到雨鎮,發現了當地的賭雨風俗,賭徒的本性又被喚起。
〈到遠方〉
被寄養的男孩和身上有赤紅條紋的女孩相遇,現實對他們並不友善,山野成了他們暫時的樂土。
〈Chelsea Blue〉(花蹤文學獎馬華小說首獎)
父親臨終前說出一個藍色的謎,謎中有復活的死嬰、神出鬼沒的黑貓和夢想破滅的運動選手。
〈老奧爾洛夫〉
一匹賽馬逃出馬場,在奔向自由的路上浮想聯翩。
〈一顆完美的蛋到底要煮多久〉
在kopitiam駐唱的女歌手,遭到男人始亂終棄,成為母親的她等待著能夠告訴孩子真相的那一天。
〈沙壇城〉
一個遺忘生前記憶的男子試圖恢復記憶,穿梭在以性愛麻痺自我的鬼魂中。
作者簡介:
林俊龍
1993年生的INFJ,馬來西亞檳城人,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文學組、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碩士班創作組。小說作品曾獲奇萊文學獎、西子灣(全國大專院校)文學獎,及花蹤文學獎。花蹤文學獎得獎作品〈Chelsea Blue〉同時也被翻譯為馬來文,與其他六名馬華作家一同選入《Tasik Itu Bagai Cermin: Antologi Cerpen Sastera Mahua》(《馬華小說選:湖面如鏡》)。
章節試閱
第二片屋瓦
老李最近搬到了鎮上。鎮上總是落雨,外地的人都叫它作「雨鎮」。雨鎮的人們喜歡給對方起外號,像最近新到的老李,大家都管他叫「闊嘴李」。並不是因為他的嘴巴比別人闊,而是老李的鼻子小,顯得嘴巴特別大,不僅如此,他的食量也是全鎮人所佩服的。
雨鎮附近有條小河,從拉律山上流經雨鎮的東邊,新來鎮上的老李帶著他的一對妻女安住在河岸邊上。老李家板屋前門是條大馬路,後門出去是河岸,河岸邊有一棵大葉欖仁樹,它長得茂密高大,板根高過一個成年人的膝蓋,往後還有一小片的香蕉林。老李的八歲女兒小花,多半一天的時間都花在那裡的河岸。她不只戲水,還會抓那種小小且色彩繽紛的打架魚。老李一家本來是製造水粉的,老李嗜賭,把在北部好好的工廠都賠了,欠了一屁股債就逃來這小鎮。
老李的妻子勸他在鎮上重操水粉生意,可老李身上沒有大筆錢,不能買米做水粉。自從新到雨鎮後,他因為錢的事情總是鬱悶不樂,臉都皺得像一塊乾掉的柑皮一樣。有一次,老李的妻子臨睡前終於忍不住勸他:「多在鎮裡找找工作,吃些苦當一個搬運工,賺點小錢,能積多少就多少,這樣才能繼續做水粉啊。」老李沒回應,只把雙眼一閉,弓著小腿就陷入睡眠深處。很多時候,妻子只要一提起找工作的事,他不只轉移話題,還會刻意迴避,搞得後來妻子也不再和他說話了。
老李總是一大早出門,傍晚的時候才回家,但他不是為了找工作,而是去鎮上巴剎附近的一間茶室,那間茶室叫「大千茶室」,那裡晨早時會聚著一群中年人談論每日的「氣象」。老李初時坐在角落旁喝著海南kopi靜靜觀察他們,後來大家熟絡了,「闊嘴」、「闊嘴」的叫著後,連他也插了一腳進去和他們聊了起來,但大多數聊起的都是老李過去作為老闆經營水粉行業的成功事蹟。他喜歡談論自己輝煌的一刻,這很令他自傲,所以後來鎮上的人又叫他「闊嘴頭家」,說他嘴巴大,可以吃四方,以後又會變老闆。每當老李聽到有人這樣稱呼他,嘴巴都笑成了路邊晨早盛開的喇叭花那樣大。
老李一大早出門去大千茶室是有原因的,在大千茶室裡他總是聽著那群中年人談論著雨鎮的每日「氣象」,他覺得這樣的日子聽著他們聊就會變得特別有意思,而且大千茶室的kopi O很合老李的口味。後來,在雨鎮的巴剎另一頭,出了一名「雨王」。雨鎮的人們在巷子倒垃圾時談論他,煮菜時也談論他,臨睡前也談論他,就連晨早與鄰居碰面打招呼時也會談論起他,老李心裡不是滋味,大家都鮮少叫起「闊嘴頭家」這個名號了,何時何處都以這位雨鎮裡的人物作為話題。他很想知道這名人物到底怎麼發跡成雨鎮的焦點。那天一早他又出門,往著一條與大千茶室相反方向的路走去,他拐了彎,走過大馬路,直走到巴剎的另一頭,那裡有一座鐘塔,是以前英國殖民時建的。鐘塔對街有座封閉式巴剎,連著巴剎有一間小茶室,茶室是巴剎的入口,鎮裡的華人都把那裡叫「萬山頭」;馬來人則叫「SiangMalam」,意指白天與黑夜。萬山頭茶室的外觀有兩層屋頂,最低那層離地面其實只有兩米高,抬頭便可見到波紋瓦的坡屋頂;最高那層則具有平式頂蓋外,還有伊斯蘭鏤空木板的簷飾設計。那裡和大千茶室一樣,聚著一群中年人,還有一些年紀更老的。老李走了進去,點了一杯愛喝的無糖kopi O,找了個好位子坐下,他的眼睛和耳朵變得像獵豹一樣關注著「雨王」的出現。他等了一天,沉浸在吵雜的人語中,「雨王」始終沒出現,kopi O只點了一杯,也沒喝完。那時,外頭響起淺淺的雷鳴,所有中年以上的男人都跑到街道上去,不約而同地抬頭望天。老李也走了出去,他們望著的不只是天,還看著延伸出茶室外的坡屋頂討論起來。
有個年紀看起來比較大的,身體十分矮小的老男人,對著一個肚子像懷胎九月的中年男人笑得咧開嘴說,「你看吧!這一定下的啦!你輸的了。」
「都還沒下雨。」大肚子的中年男人身子後仰攤開雙手地說,像是對那矮小的老人表示不要太過囂張。
老李則站在街上和大家一起望著天。天空烏雲密佈,流出一點顫顫雷聲。街上站著的人不時轉身看他們的身後,老李也跟著他們做了同樣的動作。他抬頭一看背後,原來是那座鐘塔,上頭指著三點五十六分。身材矮小的老人叫一個年輕小伙子幫他看一下鐘塔的時間,小伙子看完後轉頭告訴他。老人的眼神比剛才少了得意之外,還多了幾分焦慮,中年男人比起老人則冷靜許多。大家除了看屋瓦和天空外,還不時看著鐘塔上挪動的指針,分針走到了五十八分,雲依舊陰著臉俯瞰雨鎮的人們。那時,老人和中年男人的眼神都變得異常堅毅,彷如變成了傳道者,已聞得真理信仰一般。那一刻,他們的信念堅定,眼神互不相讓,可知他們理念不同,並且對立,就像街上站立的人們,一半看前方的屋瓦,一半看背後的時鐘。在深邃陰暗的天空裡,顫顫的雷鳴突然轟大起來,嚇著了分針,讓它向前傾至下一分鐘。而在這一刻的雨鎮上空,一滴雨飛落在萬山頭前排的波紋形屋瓦上。那些擠滿一大團的烏雲最終瀉下水來,街上有一半的人叫出淋漓暢快的歡呼聲。矮小的老人走回茶室裡,邊走還與著剛才的年輕小伙子用吹噓的語氣,說他問過神,不可能會輸!同時,那個中年男子低下頭,雙手交叉在大腹之上也往著茶室內裡走去,他的步伐看起來踉蹌,可能因體重,也可能因某些事落敗了。
大雨落下,雷聲在雨鎮的上方呼嘯而過,老李坐在靠咖啡攤的位置聞到了土臭味,他又點了一杯kopi O。他看著剛才聚在街上看天的人們又圍聚在茶室裡的一張大理石圓桌旁,許多人掏錢給那個矮小的老人,矮老頭落下拖鞋坐在大理石的圓桌上,他黝黑的一腳曲放到桌上,幾根手指在趾縫間摳個不停,又邊數著一小疊紙鈔咧開嘴笑,但沒笑出聲音。
那時kopi O遞到老李桌上,他付了錢給泡咖啡水的老闆。老闆下巴偏左的地方有顆黑痣,還是長出一小撮毛的那種,鎮裡的人都說他那顆長毛痣像極了芽菜的彎曲弧度,正巧他也姓蔡,紛紛都叫他「豆芽蔡」。老李叫住他,向他詢問了剛才發生的事情。芽蔡用了寥寥數語向老李解釋,他說,「那是雨鎮裡獨特的賭博方式啦,主要是透過猜中下雨或不下雨的限定時間內取決輸贏。像剛才的賭局,莊家賭下午四點前下雨,超過四點○一秒不下雨即算輸啦,當然也是有賭四點前不下雨的人啦。」他指了那個背對著老李的大腹中年男人。
「這款賭雨方式賭法有很多種,像剛才的除了賭不下雨外,」他用手指指向外頭凸出的坡屋頂,繼續說,「還有賭這範圍內滴下的第一滴雨落在厝頂的哪一排。」
然後又說,「這裡賭雨的人都把下雨叫作『要雨』。雨季時,賭局會追加條件。我給你舉例子比較簡單啦!」
老李睜大的眼睛裡像發出了亮光,他即刻對著芽蔡點頭張大耳朵聽他說接下來的例子。
「像你賭下午三點前要雨(或無雨)嘛,我或莊家就可以推遲或提早十五分鐘到三點十五分或兩點四十五分前要雨(或無雨);又或者你可以推遲或提早半小時到三點三十分或兩點三十分前要雨(或無雨),以此類推啦。每人可以改動的時間不能少過十五分鐘就對了。」
「那麼說,像莊家如果賭早上十一點前要雨,我就可以推前到十點四十五或者是十點的意思嗎?相反地推遲也是這樣子嗎?」老李聽他說得挺仔細,興趣的勢頭也被他帶起,他想確認自己是否聽懂了規則,所以他又問了一次。
芽蔡沒開口,只對著老李叉腰點點頭。
「那會不會有兩個人都賭同一時間要雨或無雨的狀況?」老李問。
「那就要看誰能讓步嘍,誰都不讓步的話,雨就賭不成了!而且這種事還滿常遇見的。」他下巴的「芽菜」晃動著,嘴裡呼出口氣後回應了老李的問題。
老李一邊聽他說,一邊勾起杯耳淺嚐了一口kopi O又置回杯盤上,他露出了嫌惡的表情,接著和芽蔡談剛才的話題,「你剛才說的是雨季的賭法嘛,那麼旱季咧?」
「旱季就沒什麼人要賭啦,要賭也是『打折賭』。像莊家打五折,莊家賭贏了有五十塊,對方贏了就有一百。」他說完,又靠向老李的位子指著那個坐在大理石桌上的矮老頭說,「他是作莊的,這裡的人都叫他『老莊腳』,要賭可以去找他。」
「所以他是『雨王』?」老李問。
芽蔡聽完後大笑起來,手裡自然地撚起他下巴邊上烏溜溜的「豆芽菜」。他說,「哪裡可能啦,雨王比較厲害。前些日子他可是逢賭必勝,現在他贏了一筆錢就走人嘍。而且聽說是去北部做什麼生意之類的。」
那時外頭的雨越下越大,對街的雜貨店像隔了層迷濛的紗簾。
「這場雨大概會下到晚上去嘍。」芽蔡望著雨中的街景說。
那滂沱雨聲像瀑布掩蓋過巴剎的喧鬧,老李壓根沒聽清芽蔡最後說的話,只看著那杯喝了一口的kopi O深思起來。他站起身探頭看了雨勢,就跑過對街的五腳基去避雨,他沿著五腳基繼續走,路過沒有遮蔽物的地方,就大步跨過去,直直跑到大千茶室,和那裡泡咖啡水的頭手說,請求收他為徒。
自那時起,老李開始學習泡好喝的海南kopi。閒空的時候,就和大千茶室裡的那群中年常客坐在一起聊雨鎮的每日氣象,學學看雲、看雨。不多久,他便開始賭起雨來。起初,因為旱季,多半是打折賭,老李小贏了幾次。而雨季來時,短時間內必須預測出什麼時候下雨,還得賭第一滴雨落在厝頂哪排。老李就開始一直逢賭必輸,搞得後來存了幾個月泡kopi的薪資,都投進「雨」裡去了。
老李四處欠了幾筆債,連開水粉工廠的目標也破滅了。鎮上的人們暗地裡都這樣說老李:「闊嘴吃不起四方,還得把以前吃進的全吐出來。」家裡沒人願意一直承受這樣的苦日子,只有小花每日還開心地帶著那副瘦骨嶙峋的身體,看著玻璃罐子裡黑黃色斑點鱗片的打架魚。他妻子瞭解賭徒的本性,即便逃到何處也不會有重新開始的一天。每日早晨起床她就喝斥老李達到鞭策,久後也挺有見效的,老李那半年多裡再也沒去賭。然而,他每日清晨會坐在門外的矮凳上,研究雨鎮的氣象,只要一有閒暇,就會抬頭望天,身上還帶著一本小簿仔做起筆記來,像個專業學者的模樣做著研究。
上癮的賭徒怎會甘心一直平靜度過沒有輸贏的日子?
老李用他這半年多的氣象觀測經驗再次下了賭注,但他賭雨鎮今日下午五點前「無雨」。那時還是雨季,雨鎮已經有三天沒下雨,按理說第四天下雨的機率可能性很大,萬山頭茶室裡的人都因為賭「無雨」的老李而掀起一陣熱議。
老莊腳把五張一百的紙鈔放在大理石圓桌上,單手一拍大聲笑道,「闊嘴又來輸錢了!」
老李沒理會,走到芽蔡的咖啡攤,一如往常地點了一杯無糖kopi O,就從早上坐到下午等「天意」,那杯kopi他依然還是只喝了一口。時間差不多在四點五十九分,狂風吹開了魚鱗天,來到雨鎮的街道上,吹亂印度女子的頭紗,吹落了行道樹上的葉子,也把鐘塔上的指針吹成五點鐘。茶室裡的人都震驚了,「闊嘴李贏了!」而且還贏了不少,場上賭「無雨」的只有老李一人,全部人都賠本了。還有人說「闊嘴一張口,就把雨鎮吃空了!」老李依舊沒理會,拿了錢就走進茶室深處的巴剎。他去買雞肉、咖哩粉、椰漿和各種香料,他要給家裡的妻女加菜,他喜歡吃妻子煮的咖哩雞肉,他很久沒吃了。想著,這下還可以還掉一些債後,留下一些錢,便拿去買一些瓶口用琉璃焊接的無色玻璃瓶子給小花。小花拿著那些瓶子裝打架魚,一瓶一隻,整齊地羅列在欖仁樹的板根旁,還用一片長型的木板,蓋上所有瓶口。她每天會在河岸邊的土壤或水裡挖絲蚯蚓餵食打架魚,搞得臉上和衣服總是髒兮兮。每當她母親說她是個男人婆時,她卻笑得瞇起雙眼露出牙。
第二片屋瓦
老李最近搬到了鎮上。鎮上總是落雨,外地的人都叫它作「雨鎮」。雨鎮的人們喜歡給對方起外號,像最近新到的老李,大家都管他叫「闊嘴李」。並不是因為他的嘴巴比別人闊,而是老李的鼻子小,顯得嘴巴特別大,不僅如此,他的食量也是全鎮人所佩服的。
雨鎮附近有條小河,從拉律山上流經雨鎮的東邊,新來鎮上的老李帶著他的一對妻女安住在河岸邊上。老李家板屋前門是條大馬路,後門出去是河岸,河岸邊有一棵大葉欖仁樹,它長得茂密高大,板根高過一個成年人的膝蓋,往後還有一小片的香蕉林。老李的八歲女兒小花,多半一天的時...
作者序
自序
創作並非一條路可走
十四年前,第一次開啟小說之路時,那時寫完的文稿多數是收藏給自己看,感覺就像是躲在自娛自樂的白日夢裡,更沒想過自己寫的故事有天終於要出版了。
曾幾何時我認為自己沒有出色的寫作能力,作為中文系的學生,卻無法在文章中大量運用和展現自己的華麗辭藻,這讓我感到困惑。尤其,每當讀到現當代文學後,乃至於讀到參賽評審遴選出來的得獎作品時,我都有深深的疑惑。難道文學是非得先學會艱澀難懂和華麗用詞才能踏入的領域嗎?就像人們總是調侃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是因為它抽象看不懂。抱持這種想法,一直到了文大時,選修了何致和老師的小說創作課後,一切想法才開始有所轉變,第一次接觸到海明威〈像白象的山丘〉時的「原來對話還可以這樣寫」的豁然開朗,以及契訶夫〈捉弄〉主角對於感情中留下的遺憾。碩班時,上了明益老師的小說課後,更是閱讀了一系列老師開出的書單。永遠記得第一次讀完艾加.凱磊〈故事形狀的思想〉結尾時的那種震撼:
「就在那個牢房裡面,他形塑了最後一個思想,把絕望做成繩索的形狀,打個圈,吊死了自己。這個把絕望做成絞索的主意在月球上引起了騷動,大家趨之若鶩,紛紛將自己的絕望想法做成繩索,套在脖子上。月球上的人類就這樣滅絕了,只留下寂寞做成的單人牢房,歷經數百年太空風暴,那牢房也塌了。
第一艘太空船抵達月球時,太空人沒找到人,只找到上百萬個坑。起初,太空人以為那些坑是古代月球人的墳墓;湊近了看,才發現全都是空洞的思想。」
八個段落,簡單的文字為單純的故事而服務,沒有太多玄之又玄的情節和炫技,我想我找到了我要的答案:作品要寫得讓人讀得懂,而不能只寫給懂它的人看。一直以來,我只是沒遇到能夠與之共鳴的作品罷了。感歎之餘,我開始摸索自己的創作風格,最喜愛保羅.奧斯特、卡森.麥卡勒斯、喬治.桑德斯、瑪麗.奧斯汀、迪諾.布扎蒂、羅貝托.博拉紐、加西亞.馬奎斯.艾加.凱磊、阿爾多.李奧帕德、契訶夫、村上龍、村上春樹、石黑一雄、小川洋子等。在這些大師的作品基礎上盡可能地吸納他們的優點,再把我對人性思辨的想法融入進我的作品當中,往後也將如是。
談及寫作的根本原因和動機,一開始抱著的就是書寫治療來治癒自己過去不幸的經歷。這本即將出版的《沙壇城》大部分也是如此,是各種痛苦與掙扎,我確信這些捋不清的複雜情感就是創作者該有的本色,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存在的意義就在那裡。而每當我完成一篇小說後,雖然感到疲勞,但心情卻無比舒暢,仿佛心裡某塊缺失已久的拼圖被填補上了,我想這就像村上春樹說的:「小說家在創作小說的同時,自己的某部分,也被小說創作了」。
這本書,我在二○一七年初時開始起筆,直到文稿最後階段定名為《沙壇城》時,已經是二○二一年末。距離完成到即將面世,中間過去了三個年頭。自回到馬來西亞後,從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一切都沒有想像中順利,內心充滿撕裂與痛苦,乃至於完成這本書後,這三年間專注力的消磨(儘管期間不停蒐集素材和記錄冒出的想法),讓我遲遲無法開展新一輪的創作。對我來說,每一次的動筆都是一場專注力集中的冥想。創作不僅需要空間,更需要親近之人的支持與諒解,沒有這些將難以維持寫作的狀態。工作結束後,所剩不多的時間又被生活瑣碎之事瓜分而去,僅剩下的就只有睡前的一個小時,這種時候腦袋多數開始不靈光,能夠作用的就只能拿來思考未來人生要何去何從的事情了。每每想起村上春樹《身為職業小說家》中的內容時,總是避免不了心生艷羨,從而感歎道:「真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作家呢。」已故的曾珍珍老師曾在我的夢裡說過:「創作不一定只有這條路可走」,不必拘泥於創作的任何形式,所做的任何事,諸如:交談、調酒、掃地、游泳、購物……體驗生活甘苦皆屬於創作的一部分。由於這本書的出版,最近我開始覺察到體內熟悉的某種東西又再次蠢蠢欲動,腦海不停飄出新一本小說後續的部分情節。我想,事不過三說的就是現在,三年的蟄伏還不算浪費,今年該是時候了。
自序
創作並非一條路可走
十四年前,第一次開啟小說之路時,那時寫完的文稿多數是收藏給自己看,感覺就像是躲在自娛自樂的白日夢裡,更沒想過自己寫的故事有天終於要出版了。
曾幾何時我認為自己沒有出色的寫作能力,作為中文系的學生,卻無法在文章中大量運用和展現自己的華麗辭藻,這讓我感到困惑。尤其,每當讀到現當代文學後,乃至於讀到參賽評審遴選出來的得獎作品時,我都有深深的疑惑。難道文學是非得先學會艱澀難懂和華麗用詞才能踏入的領域嗎?就像人們總是調侃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是因為它抽象看不懂。抱持這種想法,一直到...
目錄
「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高嘉謙
推薦序 活著的鶴會飛走──吳明益
推薦序 前方是令人心情舒坦的陽光──柴柏松
自序 創作並非一條路可走
雨樹之下
第二片屋瓦
到遠方
Chelsea Blue
老奧爾洛夫
一顆完美的蛋到底要煮多久
沙壇城
後記 湮滅之後又為誕生
作者簡介
「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高嘉謙
推薦序 活著的鶴會飛走──吳明益
推薦序 前方是令人心情舒坦的陽光──柴柏松
自序 創作並非一條路可走
雨樹之下
第二片屋瓦
到遠方
Chelsea Blue
老奧爾洛夫
一顆完美的蛋到底要煮多久
沙壇城
後記 湮滅之後又為誕生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