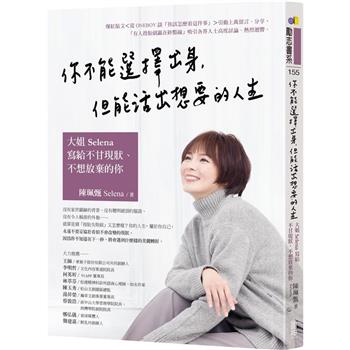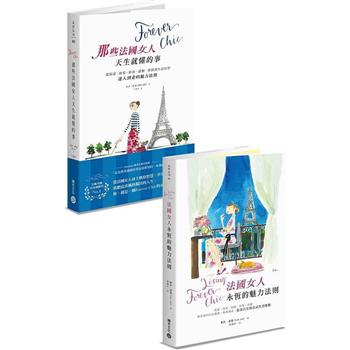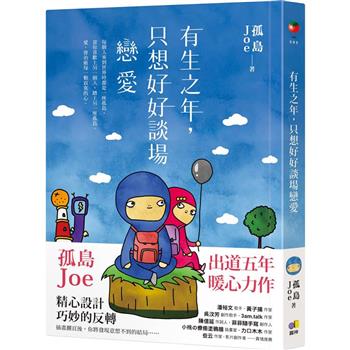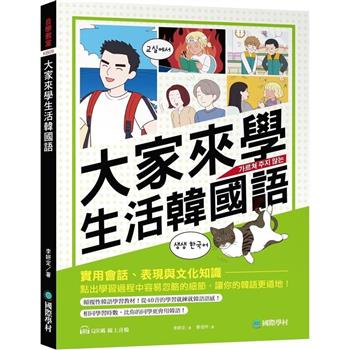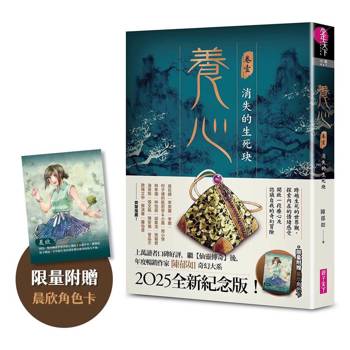六十餘年的文學奧德賽之旅
文學是一片廣袤的沃土,我有幸在這片沃土上萌茁,成長,乃至於垂老。
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
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他來自馬來半島北部一個偏遠的小漁村,經過在臺灣求學、扎根,現在是著作豐碩、育才無數的權威學者。從一個在檳城泡圖書館的文藝少年,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學長者,超過六十年的文學奧德賽之旅,李有成人生的重要篇章與際遇,在在是一個時代的文人精神的見證。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敘述李有成在馬來西亞時期的文學經驗,包含他初識文學及閱讀興趣的養成,還有他在指標性的《蕉風》月刊擔任編務的歷程,其中述及白垚與陳瑞獻這兩位文藝先鋒。
第二部分追憶李達三、齊邦媛、朱炎、王文興、陳祖文、李永平、陳鵬翔等幾位師長與老友,記述跟隨詹明信學習理論的過程,以及回顧七○年代的文學生活。李有成與這些人物的交錯匯聚,呈現出橫跨中西、代代相承的人文薪傳。一篇篇情真意摯的散文,流露出文學家、教育家、小說家等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神采。
蘇珊.桑塔格曾說:「詩人的散文是感情熾熱的自傳。」恰恰呼應了這本散文集的特性。她還說:「在喚起實際生活中與文學中決定性的邂逅時,作者無異於闡明了用來評斷其自我的標準。」正因此,在李有成所召喚的那些文學魂躍動的時空中,浮現一位詩人學者虔誠於寫作與學問的生命情調。
同舟推薦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宇文正/詩人、作家
封德屏/《文訊》雜誌社社長
孫梓評/《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張貴興/作家
張錦忠/中山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兼約聘研究員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盧美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老師有如荷馬筆下的奧德修斯,行行重行行,他的求學歷程、文學之旅、家國記憶,反映了馬華人在臺灣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的歷史變遷。──胡金倫〈總編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