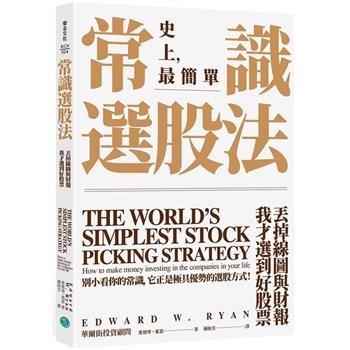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就在這裡,那比任何賭博都要激盪人心的二十四小時開始了,
並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擾亂我命運的方向--」
你的一生中有多少個24小時?
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茨威格三大小說名作,經久不衰的人性經典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作品暢銷百萬冊,是全球傳播最廣、譯文語種最多的德語作家之一,他的小說對人性描寫深刻入微,尤其善於刻畫女性心理,堪稱是最瞭解女人的男作家。
茨威格擅長以受限的視角來展開故事,他筆下的主角往往會只因為一個瞥見或一個執念,就把自己推向無盡深淵:在〈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裡,心如止水的英國貴婦,只因瞥了一眼某個年輕賭徒的手,就被其深深吸引,決心拋家棄子,不惜一切留在他身邊;在〈祕密燎人〉中,十二歲的男孩艾德加執拗地想要找出能夠變成大人的「祕密」;而〈恐懼〉的主角與其說是發生婚外情的伊蕾娜夫人,倒不如說是縈繞在其內心的恐懼。
本書精選茨威格三大小說名作,翻開任何一篇,都會觸動心靈,引人深思。
------------------------------------------------------------------
你們之所以……拒絕認為一個女人在她一生中的某些時刻會臣服於意志和認知無法掌控的神祕力量,那是因為你們自己也在害怕。
--摘自〈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他有種直覺,這個祕密就是童年的門鎖,只要打開它,就能進入成年人的世界。
--摘自〈祕密燎人〉
恐懼比懲罰更折磨人。
--摘自〈恐懼〉
作者簡介:
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
享有世界級聲譽的小說大師、傳記作家。
出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父母都是猶太人。十九歲時進入維也納大學讀哲學,二十歲時出版詩集,次年轉到柏林大學,將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文學創作,並且從事了一些翻譯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等人的影響下,從事反戰活動,為和平而奔走。二戰陰雲遍布歐洲後,猶太人遭納粹屠殺,茨威格流落異國他鄉,一度移居英國,加入英國國籍,後轉道美國,定居巴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因對歐洲的淪陷感到絕望,茨威格和妻子輕生離世。消息傳開,引起世人無限哀痛,巴西為他們夫妻舉辦了隆重的國葬。
茨威格的小說作品對人性描寫入木三分,尤其擅長刻畫女性心理;傳記作品兼具了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魅力,具有無與倫比的感人力量。
代表作:小說《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焦灼之心》,人物傳記《人類群星閃耀時》,自傳《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譯者簡介:
楊植鈞
德語譯者、教師。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文學博士,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聯合培養博士生。現任教於浙江科技學院中德學院。
長期從事德語教學及翻譯工作,在奧地利現當代文學領域研究成果頗豐。
譯作有:
二○一九《奇夢人生》
二○二三《象棋的故事:茨威格中短篇小說精選》(作家榜經典名著)
二○二三《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中短篇小說精選》(作家榜經典名著)(臺版譯名:《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茨威格中短篇小說精選》
二○二三《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茨威格中短篇小說精選》(作家榜經典名著)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受限,卻無限
一百多年前,一本名為《馬來狂人:關於激情的故事集》的中短篇小說集在萊比錫的島嶼出版社問世。該書的作者,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在致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這部小說集的寫作已經停滯了六個月……原以為還得花費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可是,有一天,它突然就在那兒了……這是我的第二部小說集,我對它的即將出版愉快得無以名狀……」
事實證明,這部作品對於一直以來從事傳記寫作和報刊編輯工作的茨威格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義。在不到八年的時間內,它在德國售出了十五萬冊,裡面最著名的篇目〈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和〈馬來狂人〉被改編成電影和舞臺劇,它們連同早期的中篇〈祕密燎人〉一道,成為茨威格早期小說的代表作。在納粹因其猶太身分而焚毀他的所有作品之前,他的小說、傳記、詩歌和戲劇銷量已經突破了百萬冊,他本人也成了當時乃至今日作品全球傳播最廣、譯文語種最多的德語作家之一。二○二一年是茨威格誕生一百四十周年,德奧等地除了舉辦各種展覽紀念這位具有深厚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以外,還推出了根據其生前最後一部小說〈西洋棋的故事〉改編的電影。電影保留了小說中敘述者所說的一句話:「一個人越是受限,他在另一方面就越是接近無限。這些人貌似避世,實際上正像白蟻一樣用自己特有的材料構建著一個獨一無二、非同凡響的微型世界。」
受限,卻無限—或許,這句話不僅適用於〈西洋棋的故事〉裡那位高超的西洋棋奇才,也適用於茨威格其他小說的主人公。他們的思緒、情感和精神都受制於某個特定情境,他們的行動是他們內心激情的俘虜,他們的結局或是被命運和偶然的鏈條所牽制,或是被歷史和政治的暴虐所改寫,或是被自我和本能的烈焰所吞噬。在〈祕密燎人〉中,小艾德加初次察覺到成人和兒童的界限,不自覺地被那個「偉大的祕密」所吸引,人格發生了自己都無法理解的嬗變;在〈馬來狂人〉中,殖民地醫生出於高傲和欲望把一個女人推向死亡,為此負疚終生,只能像馬來狂患者一樣手持尖刀向前奔跑,沒有目標和記憶,直至倒地身死;〈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裡嫻雅的英國貴婦,只瞥了一眼某個賭徒的手,就被其深深吸引,毅然放棄家庭和子女,準備隨他而去;〈重負〉裡的主人公、逃兵費迪南,儘管熱愛和平,拒絕成為殺人機器,卻因為一張紙條而喪失了自我,無意識地對戰爭俯首稱臣;〈看不見的珍藏〉裡的收藏家一輩子都活在不存在的收藏品中間;〈日內瓦湖畔插曲〉裡的逃兵跳進水裡游向根本不在此地的故鄉;〈西洋棋的故事〉裡的B博士瘋魔一般下著腦海中的棋局;〈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裡的陌生女子為一個稍縱即逝的身影獻出了自己的愛情與生命……
在茨威格所有的小說作品中,無論裡頭講述的是個體的命數還是歷史的浩瀚,都存在一個刺針一樣的、微小又神祕的「束縛」,它可能只是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執念、一道稍縱即逝的思緒、一片曾經見過的風景、一場腦海中幻想過的會面,卻足以在主人公的生命中掀起風暴,把他們推向激情的淵藪。不是所有主角都能把自己內心的衝動轉變成非同凡響的微型宇宙,可是他們都在凝視內心深淵的過程中,感知到了一個更為宏大的維度的存在。一種不可觸摸的信號,猶如天啟,在身體的內部敞開,像是燒淨一切的烈焰,又似萌芽於隕滅的種子:「他感到,這陌生的、未知的力量先用銳器,再用鈍器把他肉體裡的什麼東西挖了出來,有什麼東西正在一點一點地鬆開,一根線一根線地從他密閉的身體裡解脫出來。瘋狂的撕裂停止了,他幾乎不再疼痛。然而,在體內的什麼地方,有東西在燜燒,在腐爛,在走向毀滅。他走過的人生和愛過的人,都在這緩慢燃燒的烈焰中消逝、焚燒、焦化,最終碎成黑色的炭灰,落在一團冷漠的泥潭之中。」(〈心之淪亡〉)可以說,茨威格的小說是一個龐大的、關於束縛的寓言,它不僅僅關注著人的內心,也質問著那種對內心施加束縛和限制的力量。
……
楊植鈞
於德國布蘭肯費爾德-馬婁
二○二一年十二月
名人推薦:受限,卻無限
一百多年前,一本名為《馬來狂人:關於激情的故事集》的中短篇小說集在萊比錫的島嶼出版社問世。該書的作者,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在致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這部小說集的寫作已經停滯了六個月……原以為還得花費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可是,有一天,它突然就在那兒了……這是我的第二部小說集,我對它的即將出版愉快得無以名狀……」
事實證明,這部作品對於一直以來從事傳記寫作和報刊編輯工作的茨威格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義。在不到八年的時間內,它在德國售出了十五萬冊,裡面最著名的篇...
章節試閱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戰前十年,在我當時下榻的一所位於里維拉海濱的旅館餐廳裡,曾爆發過一次激烈的爭論。出人意料的是,爭論很快就演變成狂暴的唇槍舌劍,險些以憎恨和辱罵收尾。世上的人,大多麻木不仁,缺乏想像力。無關痛癢的事,他們不會煽風點火;但如果眼下的事觸犯到他們哪怕一絲半點個人情感,他們就會怒不可遏、順勢澆油。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一掃平日裡事不關己的態度,代之以誇張又不合時宜的暴虐。
我們這個餐廳裡坐在同桌的中產階級小圈子,恰恰就陷入過一次這樣的爭吵。平日裡,我們總是友善地寒暄,或是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吃完飯後就各奔東西,那對德國夫婦去踏青和拍照,那個肥胖的丹麥人百無聊賴地去釣魚,那位英國貴婦去看她的書,那對義大利夫婦去蒙地卡羅玩。而我呢,則坐在花園裡無所事事,又或者去工作一會兒。不過,在爆發爭吵的那天,我們所有人都針鋒相對,你不讓我我不讓你;要是有誰突然從桌邊站起身來,那可不是像平日那樣要彬彬有禮地告辭,而是要把怒火噴向在座的其他人,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那樣,準備激烈地為自己爭辯。
打破我們小圈子一貫平和的事件,本身就已經夠離奇。我們七人住的那家膳宿旅館,表面上是一幢與世隔絕的別墅。啊,從旅館房間的窗戶看出去,能見到美不勝收、礁石嶙峋的海濱!不過,它其實是那家金碧輝煌的宮廷飯店的一棟比較廉價的附屬建築而已,而且和那個飯店透過一個共有的花園連接起來,所以我們和宮廷飯店的那些住客平日裡一直都有來往。就在前一天,這家飯店傳出了一樁不折不扣的醜聞。
當天十二點二十分的時候(我不能不告知各位讀者這個精確的時間,因為它無論對這個插曲還是對我們後來爭吵的主題來說,都至關重要),一位年輕的法國男子乘著正午列車到來,並在飯店裡一個朝向海濱、可以遠眺大海的房間裡住下了,這件事本身就意味著他大有來頭。不過,不論是其無可挑剔的優雅氣質,還是他那不同凡響、讓人心生好感的英俊外表,都讓這位年輕人處處受人矚目、惹人憐愛。宛如少女的細長臉龐,感性溫熱的雙唇和上方的絲綢般泛金的髭鬚,白皙的額頭上那輕軟微鬈的棕色劉海,還有能用目光愛撫別人的溫柔雙瞳-他臉上的一切都那麼柔美、撩人、可愛,帶著只屬於他自己的氣質,又毫無造作雕飾的痕跡。
從遠處看,他給人的第一眼總讓人想起大型服裝店櫥窗裡的那種肉色蠟像,它們握著手杖,非常高雅,用來展示理想中的男性美,然而只要湊近了看,那種紈絝子弟特有的印象又會消失無蹤,因為在他身上-非常罕見-沒有任何雕琢整飭的人工感,只有與生俱來、純屬天然的可愛與迷人。他向每個遇到的人致意,既謙虛又真誠;他身上的優雅總在每一個小動作裡舒展流淌,讓人賞心悅目。每當有位女士往衣帽間走去,他總是搶在前頭,幫她把大衣取下來,而對每個小孩子,他總是和顏悅色,有時會說上一兩句逗趣的話,給人熱情開朗又禮貌得體的印象。總而言之,他看起來就屬於那種幸運兒,相信自己能用明媚的臉龐與青春活力取悅身邊的人,並在反覆試驗之後,把這種確信轉變成駕輕就熟的優雅。對大多數年老體弱的房客來說,他的存在就好比天賜之恩;他青春貌美,昂首闊步,盡情展示輕盈清新的風度,和身邊的人共用自己的優雅,因此不可避免地奪取了所有人的心。剛到飯店不過兩小時,他就已經和那個來自里昂的胖工廠老闆的兩位千金打起了網球,她們是十二歲的安妮特和十三歲的布朗琪,而她們的母親、溫柔高雅又格外靦腆的亨莉埃特夫人,則在一旁微笑地看著她兩個年輕的女兒和這位來路不明的年輕人打情罵俏,彷彿出自本能那樣自然。
當晚,他湊到我們的牌桌邊來,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小時各種有意思的軼事,然後又和亨莉埃特夫人到露臺上散步去了,這位夫人拋下了她的丈夫,他還像往常一樣和一位生意上有來往的朋友玩多米諾;稍晚點的時候,我還看到他和飯店的女祕書在昏暗的辦公室裡可疑地談著什麼。
翌日早上,他陪我那位丹麥朋友去釣魚,在這方面展示了驚人的學識,之後還久久地和里昂的工廠老闆聊政治,從胖工廠老闆那蓋過海浪的笑聲來看,這位年輕人顯然不乏風趣幽默。飯後-我把每時每刻發生的事件交代得這麼清楚,因為它們對理解整個故事至關重要-他又和亨莉埃特夫人坐在花園裡喝了一小時黑咖啡,然後去和她的兩個女兒打球,還和那對德國夫婦在大廳裡閒話了一下家常。晚上六點的時候,我正要去寄一封信,卻在火車站附近遇見了他。他匆匆忙忙地向我解釋說他要失陪一陣子,因為突然接到了離開此地去辦事的通知,兩天後會回來,說罷便繼續趕路了。當晚吃飯的時候,他人雖然不在,卻依然是眾人聊天的唯一話題,沒人不對他那溫文得體、活潑爽朗的風度讚不絕口。
夜裡,大概十一點的時候,我正在房間裡想把一本書讀完,卻突然聽見窗外傳來叫喊聲,對面飯店裡顯然發生了騷動。更多是因為好奇而非忐忑,我走了五十步來到對面,只見人頭攢動,房客和服務生都局促不安、亂作一團。亨莉埃特夫人原本像往常一樣,在她丈夫和來自那慕爾的朋友玩多米諾的時候沿著海邊露臺散步,可是今晚她卻沒有回來,恐怕是出了什麼意外。肥胖的工廠老闆像頭牛一樣往海邊衝去,邊跑邊大喊著:「亨莉埃特!亨莉埃特!」」聲音都因為不安而扭曲了。在夜晚的海邊,這叫聲聽起來異常驚悚,彷彿來自遠古世界的一頭瀕死巨獸。飯店侍者焦慮地跑上跑下,叫醒所有客人,還報了警。在此期間,那個肥胖的男人還在踉踉蹌蹌地跑著,衣冠不整,上氣不接下氣,無望地對著黑夜叫喚:「亨莉埃特!亨莉埃特!」他的兩個孩子也醒了,穿著睡衣,對著窗外大聲叫著母親的名字,於是父親只好又跑上樓去安撫她們。
接下來發生的事是那麼駭人聽聞,要複述一遍幾乎不可能,因為在情感限度無法承受的瞬間,狂風驟雨般的事件刻在人類腦海的只有一個極其悲愴的印象,以至於沒有任何圖像或者文字能用同等的閃電般速度將其再現。那個肥碩無比的男人突然臉色大變,疲憊又陰沉地從咿呀作響的樓梯上走下來。他手中拿著一封信。「您把所有人都叫回來!」他用剛好能聽清楚的聲音對飯店主管說,「請您叫各位回來,不用再找了。我的妻子拋棄了我。」
這是一個瀕死男人的鎮定,一種超越凡人的自制,在他面前是一群先前好奇地望向他,現在卻突然驚恐、羞恥、迷惑地從他身上移開目光的人。他竭盡最後的一點點氣力,步履不穩地從我們身邊走過,沒有看身邊的人一眼,直接走到書房裡把燈擰滅;然後我們聽到他那沉重的身軀倒在扶手椅裡的聲音,聽到一種野性的猛獸般啜泣—只有從未哭過的男人才會這樣哭泣。
他那刻骨的痛楚馬上攫住了在場每個人,狂暴得令人眩暈,哪怕最與之無關的人也不得不為之震動。沒有一個侍者,沒有一個因為好奇心而溜過來的客人此刻敢微微一笑或者說出一個表示遺憾的詞。默然無聲,因為見證了這讓人粉身碎骨的情感爆發而羞恥不已,我們一個接一個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裡,留下那個被不幸擊倒的男人躲在漆黑的房間角落裡,孤苦伶仃,獨自啜泣。包裹著他的是這幢竊竊私語的房子,它低聲細語,呢喃不止,緩緩地走向瓦解。
可以理解,這樣一樁突如其來、直擊人心的事件為什麼會惹惱那些平日裡無所事事的人。我們桌邊的爭論總是突然爆發,然後把所有人逼到要動武的邊緣,雖然這些爭吵的起點是那樁駭人的事件,不過後來證明,它本質上更像是各種不同的人生觀之間的角力,也是一場對生活態度的基本探討。一個女傭偷看了那封信—當時,精神崩潰的丈夫把讀完的信揉成一團,隨手扔到了地上—然後不慎說漏嘴,將信的內容傳得人盡皆知。亨莉埃特夫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和那個法國年輕人一起私奔了(在座大多數人對他的好感立馬被敗得一乾二淨)。第一眼看來,這位小包法利夫人會拋棄她那個肥頭大耳、土裡土氣的丈夫而投入一個英俊小生的懷抱,也是可以理解之事。不過讓人震驚的是,這位道德上無可挑剔的三十三歲貴婦,和一個剛認識的年輕男子只是晚飯後在露臺上聊了兩小時天,在花園裡喝了一小時咖啡,就對其投懷送抱,甚至拋夫棄女,把命運隨便交給這個花花公子。這恐怕不僅僅是工廠老闆和他的女兒,甚至連亨莉埃特夫人自己也無法想像的風流韻事吧。
一番討論之後,眾人一致認為,所謂「相識不久」只是一對小情人用來騙人的幌子罷了:亨莉埃特夫人和那個年輕人肯定老早就認識了,那個誘惑者這次到她下榻的飯店來是為了商討私奔的最後細節,否則—他們的結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貴婦在兩小時之後就被一個剛認識的陌生人騙走了,這怎麼可能呢?此刻,我卻執意提出不同的看法,彷彿能從中得到樂趣一樣:一個女人,長年累月和自己不愛的男人捆綁在一起,過著無聊又令人沮喪的婚後生活,其實心裡可能早就做好了隨他人而去的準備。因為我提出的異議,在座的人馬上就把這件事套用到自己身上,尤其是那對德國夫婦和那對義大利夫婦,他們都覺得所謂的一見鍾情極其愚蠢,只是某些下三爛小說裡的幻想罷了;他們對我很是蔑視,幾乎用侮辱的口氣否定了我提出的可能性。
當然,對於在上湯和甜點之間爆發的這場激烈爭論,沒有必要抓住各種細節不放。只有那些慣吃定餐的高雅之士才會說出值得一提的妙語,我們這些人情急之下所能找到的都是些老生常談的論據,畢竟在一次偶然爆發的爭吵之中,大家總會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我們的爭論這麼快就落到要互相羞辱的地步。
導火線應該是,那兩個丈夫不由自主地想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也會陷入和亨莉埃特夫人相同的危險處境裡;可惜兩位夫人找不到更好的回答,只能一味和我針鋒相對,對我說,我對女性心理的評判太過膚淺,和那些在調情中偶然得手的單身漢毫無二致。這話已經讓我有幾分火了,這時那位德國夫人還好為人師,火上澆油。她說,世界上啊,有兩種女人,一種是真實的女人,另一種則是「天生的娼妓」,亨莉埃特夫人毫無疑問屬於第二種。這話一出,我再也受不了了,於是變得咄咄逼人起來。我說,你們之所以拒絕接受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拒絕認為一個女人在她一生中的某些時刻會臣服於意志和認知無法掌控的神祕力量,那是因為你們自己也在害怕,你們害怕自己的本能,害怕會在某一天臣服於自己內心的惡魔;有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覺得自己不會輕易受誘,覺得自己更強大、更正派、更純潔,這樣想會讓他們內心好受一點。我本人卻認為,一個順從自己的本能和激情的女人,比那些和丈夫同床異夢、滿口謊言的女人要真實多了。
我大致上就說了這樣的話,在爭吵白熱化之時,他們越是全力詆毀可憐的亨莉埃特夫人,我就越努力去維護她(事實上這遠遠超出了我自己內心的本意)。正如大學生常說的那樣,我的激動對那兩對夫婦來說可謂「下了戰書」,他們此時齊齊唱起雙簧來,齊心協力對我發起進攻,以至於那個一直滿臉平和、像拿著碼錶的足球裁判一樣端坐在那裡的丹麥老先生也看不下去了,於是他時不時地用指節敲敲飯桌:「好了好了,各位先生。」不過這只是將戰火暫息了幾秒鐘。一位先生三番五次氣急敗壞地從桌旁站起來想動手,又被他的夫人勸住了—總而言之,哪怕再持續幾分鐘,我們就要大動干戈,這時,就像一滴潤滑油一樣,C夫人突然插話,平息了我們的怒火。
C夫人,一位白髮蒼蒼、高雅非凡的英國老貴婦,儼然我們這一桌的榮譽主席。她筆直地坐在她的位置上,面帶平和不變的友善,不發一語,但又總是興致勃勃地聆聽,光是她的存在就已經給人賞心悅目的印象:完美的鎮定、貴族的舉止,還有其散發的沉靜之光。儘管與每個人都保持著一定距離,她卻懂得怎麼藉由一顰一笑來傳達一種特別的善意,大多時候她都坐在花園裡看書,有時彈彈鋼琴,很少有人為伴,也不曾加入什麼熱烈的談話。她幾乎是無聲無息地存在著,卻又使所有人臣服於她特有的權力之下。所以,當她頭一回介入到談話中來,我們都覺得很難為情,因為我們方才實在是聒噪不止,有失體統。
在那個德國人憤怒地從桌邊跳起,然後又回到座位上的空檔裡,C夫人出人意料地抬起她那雙清澈的灰色眼睛,猶豫地看了我一眼,然後客觀明瞭地接過話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您是說,亨莉埃特夫人是完全無辜地被牽涉到一樁冒險之中?您的意思是,一個像亨莉埃特那樣的女人,可能在一個小時前還覺得出軌就像天方夜譚,與己無關?」
「是的,我正是此意,尊敬的夫人。」
「按您的說法,任何道德評判都是無效的了,任何傷風敗俗的行為都可以得到辯解。如果您真的認為,那些激情犯罪者,正如法國人常說的那樣,算不上真正的罪犯,那我們要國家的司法體制又有何用?的確,司法是鐵面無私的—您則有副慈悲心腸,」她微笑著補充道,「您會願意在每一樁罪行裡面尋找激情,然後為其開脫。」
她述說的口吻明白無誤,但又帶著一種近乎快活的語氣,這使我大為感動,於是我也不自覺地模仿起她的口吻來,半是嚴肅半是揶揄:「國家的司法體制對這些事的評判當然比我嚴格得多;畢竟它要鐵面無私地維護普遍的道德秩序和行為規範,它的任務在於審判,而非辯解。不過,作為一個普通人,我不覺得我有必要站在國家司法機關的制高點審判別人,我更願意當一名辯護者。理解他人,而非審判他人,這對我來說更有樂趣。」
好一會兒,C夫人都用她那雙明亮的灰色眼睛上下打量我,想開口說話但又猶豫不決。我擔心她沒有聽懂我的回答,於是準備用英語複述一遍。這時,她突然又提出了新問題,帶著一種不同尋常的嚴肅,彷彿是在監考:「一個女人,拋棄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就為了和一個她根本不知道值不值得愛的男人在一起,您難道不覺得這種行為無恥嗎?畢竟,她也不是什麼正值豆蔻年華的少女,而是兩個女兒的母親,應該為了孩子學會自尊自愛,您真的能為這樣一個女人草草犯下的失格行為辯解嗎?」
「我向您重複一遍,尊敬的夫人,」我固執己見地說,「我拒絕在這種情況下擔任審判者的角色。在您面前,我可以坦白地承認,我剛剛的說法是有點言過其實—這位可憐的亨莉埃特夫人當然不是什麼英雄,甚至算不上是為了愛情敢於冒險的人,當然更稱不上什麼情種。根據我往日對她的印象,亨莉埃特夫人其實是一名平庸又懦弱的女子,她現在敢於順從自己的內心,這固然讓我心懷敬意,不過我對她更多的是遺憾和同情,因為她明早一覺醒來,甚至可能此時此刻就已經發現自己身處極度的不幸之中。她的行為固然魯莽,甚至愚蠢,可是絕非低賤下作,我始終覺得,無人有權去蔑視一個可憐的不幸女人。」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戰前十年,在我當時下榻的一所位於里維拉海濱的旅館餐廳裡,曾爆發過一次激烈的爭論。出人意料的是,爭論很快就演變成狂暴的唇槍舌劍,險些以憎恨和辱罵收尾。世上的人,大多麻木不仁,缺乏想像力。無關痛癢的事,他們不會煽風點火;但如果眼下的事觸犯到他們哪怕一絲半點個人情感,他們就會怒不可遏、順勢澆油。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一掃平日裡事不關己的態度,代之以誇張又不合時宜的暴虐。
我們這個餐廳裡坐在同桌的中產階級小圈子,恰恰就陷入過一次這樣的爭吵。平日裡,我們總是友善地寒暄,或是開些...
目錄
導讀 茨威格:洞燭人性幽微的世界主義者 楊植鈞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祕密燎人
恐懼
史蒂芬•茨威格年表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導讀 茨威格:洞燭人性幽微的世界主義者 楊植鈞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祕密燎人
恐懼
史蒂芬•茨威格年表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