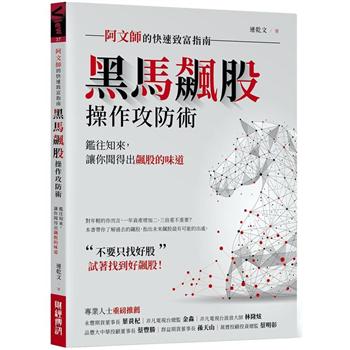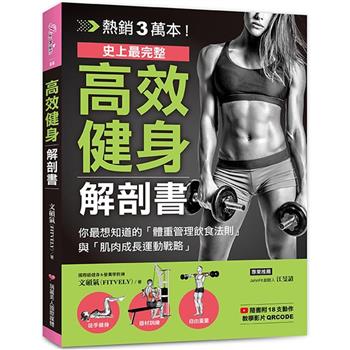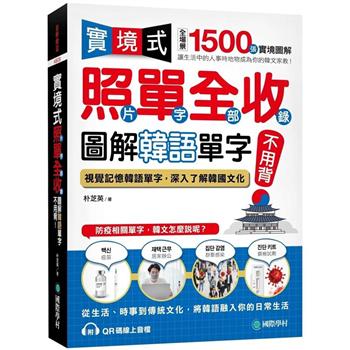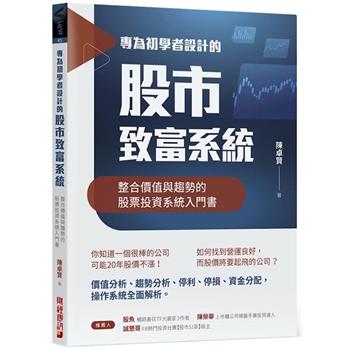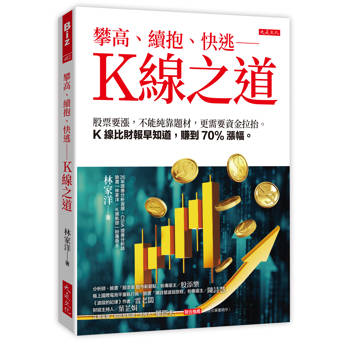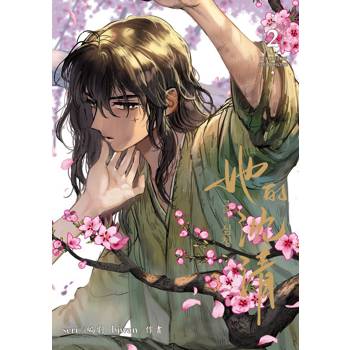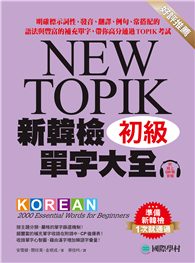自序
本人於1981年前往日本東京學習,因此開啟「日帝殖民下臺灣美術教科書歷史之研究」的契機。
在日帝殖民末期,臺灣處於日帝軍國主義的高壓統治,正值步入皇民化階段,當時臺灣民生物資缺乏,日軍在臺實施配給制度,將大部分的資源奉獻給天皇與皇軍,據統計,臺灣所生產的米糧約70%須運往日本本土及戰場前線。另一方面實施種族階級制度,要求臺灣人民改名換姓加入皇民,以換取較優渥的薪水以及糧食的配給。當時的臺灣陷入貧窮與物資短缺的困境,再加上遭受日本人種族的歧視與各種不平等的待遇,造成部分臺灣人民被迫加入了皇民家庭,希冀藉此改善家庭生活,少數既得利益者於此同時,早已臣服於日帝的太陽旗下,改名換姓融入軍國體制效忠日皇,甚至參與對中華民國作戰,隨著日帝戰敗這些人為躲避刑責選擇歸化日本籍。
慶幸的是本家並沒有在日帝利誘與強迫下加入皇民的家庭,雖然如此,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我的母親跟祖父母的對話皆使用日語,而父母之間的生活閒聊亦用日語,當時的我年幼無知,誤認日語是我們的母語之一,因此對日語產生了好奇,但隨著年齡漸長,這段成長經歷讓我深陷迷惘與文化認同的矛盾中。
1982年進入大阪藝術大學攝影科學習,在共同課程時因故與日本同學發生肢體衝突,事後,學科長岩宮武二,下令同學以後稱呼本人,以羅馬拼音YANG稱呼(ヤン君)而不是日語發音的(ヨウ君),此舉顯示種族差異造成的隔閡。畢業後拿到學科長獎,順利考上國立東京學藝大學造形藝術學美術教育學科大學院,在恩師赤沢英二教授指導下,我全心投入殖民地教育和臺灣美術研究的領域,並於1986年以《臺灣近代美術之研究》為碩士論文,確立了未來研究臺灣美術教育的方向。2003年再次遠赴日本留學,進入國立山囗大學東亞比較研究所,在指導教授纐纈厚先生許可下,每週搭乘班機往返桃園與福岡,三天在日本上博士班課程,四天在臺灣南部私立大學教學,多年後完成學業。
留日期間最大的興趣,是穿梭在神田區東京中古書店,找尋早期臺灣相關的教科書、寫真帖、東亞各殖民地文獻史料等,我對於日本戰後留下的龐大文化資產與古書文物深感佩服。這些文物深深吸引著我,從此投入大量的金錢、時間和精力,走遍東京、大阪、九州、北海道舊書店,瘋狂蒐集和臺灣相關的各類書籍。歷經二十多年,我共蒐集了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美術教科書兩百餘本,以及日帝東亞影像原版照片五百餘張,戰爭寫真帖、畫冊近百本,1894甲午戰爭手繪本一套,以及畫家古城江觀旅臺寫生作品數十件。
在孜孜矻矻不斷的努力研究下,前後出版《臺灣歷史影像》、《大侵略時代》、《太陽旗下美術課》、《有一天我會回家》紀錄片及同名專書,這些作品大多取材自我多年來蒐集的史料。期間,我曾成功申請了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日治時代臺灣小公學校美術教課書數位典藏收集計畫,預計將費心蒐集,堪稱臺灣獨一無二的日帝殖民美術教科書收藏,公開給予臺灣學界研究,無奈遇到人生道路上最大的「學敵」(學術敵人)!前中央研究院某研究員,不明事理的阻擋了我第三年的國科會研究計畫,諷刺的是,本人的計畫曾獲得國科會公開的讚賞以及在臺史館展覽的肯定,官方的國立臺灣圖書館也曾多次與本人接觸,邀約合作出版相關研究,無奈因第三年計畫受到學敵不理性的批判而胎死腹中,雖然本人向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提出抗議,對方卻以「國家型計畫不得申覆」為由回絕,嗚呼哀哉。
本人研究臺灣美術教育發展過程,從日帝學校制度變革著手,探討殖民地學制的比較與公學校的沿革,深入分析日帝美術教育發展歷程,以及殖民地臺灣美術發展的脈絡,我並非僅關注畫家的個人特色,而是著重於殖民教育制度對臺灣美術的整體影響。
日帝無心插柳卻促成了臺灣美術的萌芽。透過對每一頁美術教科書內容的比較,可以看出臺灣人在崎嶇不平的殖民地教育體制下奮力求生的歷史。不公平的學制、充滿歧視的公學校教育、種族分離政策,以及對臺灣原住民的排斥,與享有優越待遇的大和民族形成了鮮明對比。「臺灣人是天皇的赤子(兒女)」這種說法,無疑是一片謊言!
日帝時期臺灣美術教育在文化啟蒙與殖民統治間的矛盾,反映出殖民教育的本質並非單純促進藝術發展,而是服務於軍國主義和同化政策。臺灣人在殖民教育體制下的奮鬥,既揭示了壓迫,也展現了求生存的韌性。
日帝時期的美術教科書雖然設計精美、包裝華麗,看似充滿啟蒙意圖,但仔細推敲殖民地的教育過程與學制,不難看出其潛藏的殖民心機與剝削本質。這段歷史,也揭示了臺灣美術教育史背後深刻的悲戚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