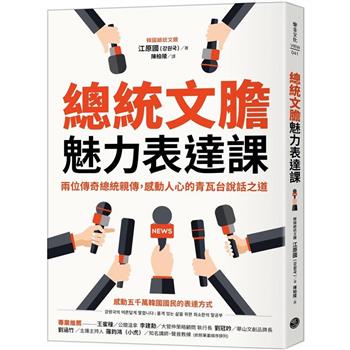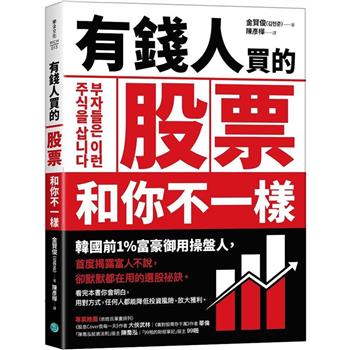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祕密,
只是她的祕密始終比別人多。
一部獻給受傷靈魂的激勵之作
卡內基兒童文學大獎提名作家
英國水石書店讀者五星評論
大英帝國軍官勳章作者賈桂琳‧威爾森讚譽作家
只是她的祕密始終比別人多。
一部獻給受傷靈魂的激勵之作
卡內基兒童文學大獎提名作家
英國水石書店讀者五星評論
大英帝國軍官勳章作者賈桂琳‧威爾森讚譽作家
「本書的故事令人心痛,而且毫不費力的擊中現實的問題。」
「我邊讀邊哭、大笑、愛得要命,而且同感悲傷。閱讀本書如同坐雲霄飛車,讓人捨不得放下。」
「我邊讀邊哭、大笑、愛得要命,而且同感悲傷。閱讀本書如同坐雲霄飛車,讓人捨不得放下。」
==內容簡介==
失去母親是她的第一個罪名,
第二個遺憾是失去了父親,
當好心的大人來到身邊,
她能勇於伸出手求救、不再害怕嗎?
凡是黛西所在的地方,好像總有意外發生。她努力想弄清楚自己的人生,也明白「別老是責備自己」。只是,自從那次意外,身上的傷疤只是確認了她必須為一切負責。她是帶來不幸的人。
當過往的痛苦把黛西壓得喘不過氣,似乎能釋放一切負擔的人出現了:妳就在今晚的月光下......一首她聽過最動人的歌聲傳來,黛西願意接受溫暖的擁抱撫慰自己日趨絕望的心,堅強的與世界抗爭嗎?
一部獻給受傷靈魂的激勵之作,找出繼續前進下一站的暖心之書。
==本書特色==
★邱慕泥(戀風草青少年書房店長)專文推薦導讀:這是一部難能可貴的故事。一方面為讀者揭露了小孩也會胡思亂想的陰暗面,另一方面,又為我們開啟專業社工、專業助人的這扇窗,讓人看到了光明面,相信擁抱的溫度。
★入選台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家讀、陳安儀老師寒假推薦書單、文化部第三十八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的《泡泡紙男孩》作者新書
★從《泡泡紙男孩》的親子關係,到《等星星發亮的男孩》重擊人們的心靈吶喊,本部作品再度啟迪讀者對於修復關係、自我成長最溫暖的勇氣。
==媒體與讀者佳評==
★《月光下的擁抱》讚譽)
本書非常有情緒感染力,滿滿的都是真實世界的議題。菲力‧厄爾已是青少年小說的一線作家。讀完了本書之後,菲力‧厄爾成為了我最喜歡的作者之一。——Anthony McGowan(衛報兒童文學專欄)
菲力.厄爾不是一位會後退的作家。本書的故事令人心痛,而且毫不費力的擊中現實的問題。——Serendipity Reviews
隨著主角的遭遇,無法停止且令人激賞的閱讀經驗。——The Overflowing Library
我邊讀邊哭、大笑、愛得要命,而且同感悲傷。閱讀本書如同坐雲霄飛車,讓人捨不得放下。——The Book Addicted Girl
給予滿分,而且期待作者的下一本書。——Nayu’s Reading Corner
我必須說,主角黛西是一個很好的敘事者,富有同情心、描述得很好,周圍的角色也是強而有力。對話是特別優秀的,每個角色都擁有很強烈的聲音。厄爾的寫作風格是不犧牲一分一毫地寫實,且不過血淋淋,但是他處理一些議題時讀起來極為強烈,經常會讀得很不舒服,部分是因為厄爾創造的角色和情境都很寫實,但同時也很抓住人心。——TheBookBag
我是老師,我認為這本跟 《等星星發亮的男孩》一樣,我大力推薦給年輕朋友閱讀,因為很讓人投入,也寫得很誠實。也希望未來能讀到更多菲力‧厄爾的作品。——讀者
我買了這個作者的兩本書,本書和《等星星發亮的男孩》。它們都很有趣,也給你一些關於出身於非原生家庭的孩童一些概念,讓你了解到他們的感受和情緒。——讀者
★《等星星發亮的男孩》讚譽
肯定生命的價值,內容充滿救贖,實實在在是本好書。──《衛報》
菲力‧厄爾以嚴厲的筆法描寫劣勢孩童的境遇,處理方式敏感細膩。這部精采引人入勝的小說讓我感動落淚。──英國書獎年度童書獎得主、大英帝國軍官勳章作者賈桂琳‧威爾森
《等星星發亮的男孩》令人愛不釋手──內容真實赤裸。比利是個毫無畏懼的孩子……頑強、勇敢又富有同情心。──《16歲的最後心願》作者珍妮‧唐涵
動人且充滿震撼力。我超愛這本小說。──《我想,我可能是瑪莎》作者蘇菲‧麥肯吉